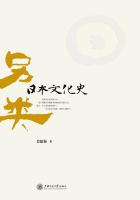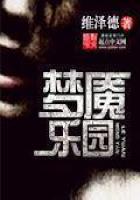我始终认为,兰州是一座神奇的、尚未被国人和世界充分理解的城市。它的神奇何在?首先,从地理位置看,兰州不偏不倚,恰好居于中国版图的中心点。第二,进入兰州盆地就会发现,环绕兰州的群山逶迤如一条巨龙,皋兰山若是龙头,九州台便是龙尾。经科学测量,九州台是黄土高原土层最厚的地方之一,故兰州又有“黄土高原之宗”的称呼。第三点尤为难得,黄河从巴颜喀喇山奔流而下,东流到海不复回,所经城池不少,但是,黄河穿城而过的,惟兰州而已。仅此三点,足可见其造化之巧,难道这还不算神奇吗?兰州的神奇何止这些?兰州的历史甚为悠久。秦置陇西郡、榆中县,汉置金城郡,十六国时期为西秦国都,隋置兰州,清康熙五年(1666年)陕甘分治,兰州遂成省会,自此成了甘肃省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兰州是各种文化相互激荡的最好见证地。兰州得名于皋兰山。匈奴称天为皋兰,皋兰山也确有直薄云汉的突兀感。兰州又名金城,据说依《墨子》“金城汤池”说法得之,因其地形险要,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要冲。在历史上,它是胡汉之间的著名驿站。汉代以来,汉民族的中央集权与西北各少数民族之间的杀伐征战多从这里引发。经过漫长历史的磨合,兰州是一个多民族的聚集地,虽以汉族为最多,但也有回、藏、蒙、满、土、东乡、维吾尔等民族往来其间,不同信仰的人在这里同生,佛教、道教、******教、基督教、天主教在这里并存,于是多民族、多宗教的交融互渗,兼容并包,成为兰州文化与众不同的突出特质。
我认为,古兰州或古金城郡,其实又是一个文化圈的别称,这个文化圈的圆周还应包括河州、湟州、临洮、循化、榆中、皋兰等青海与甘肃接壤的地带。这是因为,与仰韶文化同期的无比绚丽的马家窑文化诞生于斯。若加细分,又可分为马家窑文化、半山文化、马厂文化、齐家文化、辛店文化、寺洼文化等等,兰州花寨子、牟家坪、沙井驿等地就有丰富精美的陶器出土。它们证明,在新石器时代的中晚期,这里曾创造过辉煌的彩陶文化,它在人类文明史上的价值举世共认。瑞典大科学家安特生在其《甘肃考古记》等著述中叙之甚详。
到了近现代,兰州作为西北政治重镇和交通枢纽的地位更加显要:陇海、兰新、兰青、兰包诸线,均奔凑兰州而来,交会之后又各奔西东。川陕及沿海各地的货物要进入青海、新疆、西藏,或者,青海、新疆、西藏的物产要运到内地,大都必须经过兰州这个“瓶颈”地带。
我曾在一篇散文中这样描绘过兰州的城市性格:
兰州城的性格,就像它那典型的大陆性气候一样,晨与昏,夜与昼,骄阳与大雪,旋风与暴雨,反差十分强烈;又像皋兰山与黄河的对峙一样,干旱与滋润,安静与狂躁,父亲与母亲,对比极其分明。这里既有最坚韧、最具叛逆性、最撼天动地的精神,这里也有最保守、最愚昧、最狡诈、最麻木、最凶残的表现。后者如马步芳集团的所作所为。兰州是封闭的、沉滞的,但又是雄浑的、放肆的。不信,你往黄河老铁桥上一站,南望皋兰山,北望白塔山,下望黄河那并不张扬却又深不可测的浑浊漩流,会感到一种山与河暗中较劲的张力,或蒙克绘画中才有的紧张感……我不知道我的描述是否触摸到了兰州城独特的个性和深层的气质,但是可以肯定,兰州具有一种内在的复杂的文化底蕴。
现代以至当代,兰州作为一个移民城市的特点愈益突出了。仅在现当代,兰州就有过几次大的移民潮:抗战时期的大后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支边,六十年代的三线建设,九十年代的西部大开发,使得兰州城市的面孔、色调、时尚乃至服饰、语言,总是那样丰富多彩。某些被“兰州愚昧落后论”蒙蔽的内地人士,到兰州一看,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只能慨叹,没想到兰州这么“洋气”,饮食文化如此发达,兰州人如此善于享受人生。现在,生活在兰州的土著居民并不很多,“兰州话”也只能作为土著们的精神家园残留着。兰州大多是从各地涌来的大学生、工人、干部、打工者和来开发西部的东南部的商家。尽管“新西兰”的谑称,“孔雀东南飞”的人才外流现象,一度成为兰州人心中的痛,但是必须看到,建国以来至今,兰州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和西部开发上所做出了卓越贡献,所创造的奇迹,足可光耀史册。
今天的兰州是美丽的,洋溢着活力,用“日新月异”不足以形容其变化之巨大。我要在这里强调的是,兰州物质上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精神上丰富的人文资源,都留出了可持续发展和进一步大开发的巨大空间。
愿黄河明珠兰州更加灿烂,祝高原古城前程更加远大!
2007年7月写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