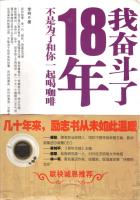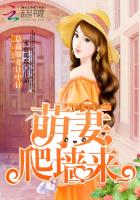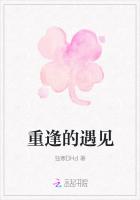中国新诗(自由诗)本来就是为反叛旧诗,冲破传统诗词的格律禁锢而引进而创造的,其自由散漫,无格律规范的形式特征与生俱来,原是“五四”那一代新诗人追求的目标。胡适提出:“文当废骈,诗当废律。”郭沫若就说,“诗的本职专在抒情。抒情的文字便不采诗形,也不失其为诗。”“自由诗、散文诗的建设也正是近代诗人不愿受一切的束缚,破除一切已成的形式,而专挹诗的神髓以便于其自然流露的一种表示。”
新诗的生存权
但在守旧的人们眼里,这横空出世的新诗无疑是一个异类,一个怪胎,他们从来就不承认新诗存在的合法性,恨不能将其扼杀于摇篮之中。继而,新诗阵营内部也开始有人反省新诗的前途和命运。鉴于新诗一直未能像古典诗歌那样广泛赢得读者,成为中国人精神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至今还有人怀疑,新诗这一形式的创立,是不是从根本上就错了?一个世纪几代诗人披荆斩棘的探索前行,是不是从一开始就误入了歧途?1997年元月号《星星诗刊》转发的引起争鸣的周涛那篇《新诗十三问》,其中首要的就是这一诘问。
然而,从根本上否定新诗,这在逻辑上就是说不通的。诗的发展,实际上只有格律化、自由化、散文化这三个方向,三条道路。如果说新诗的探索前行是一个方向性的错误,那么,请问正确的方向是什么?是坚持传统格律诗即所谓“古典加民歌”的方向吗?是转而奉散文诗为正宗吗?如前所述,在格律诗与散文诗之间,自由诗缺席已久,她的问世,有着天然的合理性,是诗史发展的必然。让我们设想一下:如果“五四”时代的人们没有创造出自由诗,还像明清两代那样沿袭汉唐诗风,一味模拟复古,或者止步于黄遵宪式的旧瓶装新酒,20世纪的中国诗坛又会有怎样的收获呢?可能避免明诗清诗式的低迷沉闷吗?
20世纪中国诗歌的主要成就,无疑是新诗的成就。尽管走过了曲折坎坷的道路,尽管良莠不齐,新诗的成就仍然是不可低估的。如果时至今日,仍然无视新诗的成就,坚持认为新诗“迄无成功”,那是说不过去的。事实胜于雄辩。唐代诗人白居易16岁写下“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从此不愁长安米贵,成为那个时代的骄傲;当代16岁女中学生也写出了《南方唱给北方的情歌》这样瑰丽的篇章,两相比较,后者的艺术质地是没有任何逊色的:
你满腮胡须的北方
冰雪地上迅疾掠过的驭者和烈马
当鹰影晃过你古铜的胸廓
我柔美地站在你粗犷的视野里
脉脉地望你
喜欢你把我看成操着吴腔越语的女子
总是缠绵绵在三月的经纬上相思、流泪
把三月的雨丝梳成好看的发式挂在背后
把三月的花枝插得满身都是
然后一点船篙高绾裤腿躲进杨柳岸这边
然后滑出多燕子的小巷
溜得远远地望你让你垂涎
我双眼皮的湖泊
波动着一页一页如岁月摇动的桨声
一阙一阙婉婉约约地折叠起来
折叠起一部重感情的地方志
第一页是西施们楚楚动人的捣衣声
第二页是琵琶女浔阳江头的琵琶韵
第三页是白娘子多愁伤感的儿化音
那些水墨画风格的水乡棹歌
年年月月在飘在唱呵
飘在穿绿裙的芦荡汊
唱在古装在矮檐下
望你
仰望你的风景线退进悲怆的凉州词
看冰雪搁浅在你毛发扬起的林涛
伸出女性的柔臂搭二十四桥
望你
戴清蓝风味的斗笠
依七十二长亭望你
等所有的纸鸢都成了北上的鸿雁
等所有的柳絮都成了痴情嘱托
我还会舞一条欢乐的林溪望你
并且扎遍野等待的草人……
南国是女性的,北国是男性的,这喻象的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且留给文化学者去阐发,诗人只以生花妙笔,抒写一支南国少女唱给北国男子汉的缠绵而炽烈的情歌。获得一个好的构思需要的是灵感,完成这一构思则需要艺术功力。当我们见到年青的诗人得心应手地运用拟人手法,极富想象力地将南国山水风情人格化,且调度那么多的历史典故和地方色彩以作渲染,突现一个极具挑逗性地“望你,让你垂涎”的现代女性形象,同时以简练的相应几笔,即勾画出阳刚、粗犷加上几分古拙的北方形象,当我们领略了诗行间透出的那别样动人的情致、意蕴和审美理想,是不能不为之叹服的。
读罢这样的诗篇,还有人坚持认为,今天的新诗面对古典诗歌,只有自惭形秽、无地自容的份儿,只配自杀或他杀,一死了之吗?如果先行者的“白话诗”可以被说成“只有白话没有诗”,那么对今天的新诗还能这样横加贬斥吗?
否定新诗可以有许多理由,譬如,新诗是从外国引进的,不符合中国人的审美心理,不能得到中国读者大众的认同;新诗没有形式规范,不便于传习,也不利于艺术经验的积累。这些理由却不免似是而非。与新诗相比,旧体诗以其简洁和精致,更适合于记忆和背诵,可是,与旧体诗相比,新诗以其语言表达的清晰和明快,更适合于朗诵和表演,更富于现场感染力。新诗的朗诵(尤其是配乐朗诵)让听众同步共鸣、即时感动的艺术效果,是旧体诗所远远不及的。
你到哪里去了呢?我的苏菲!
去年今日,
你还在台上唱“打走日本出口气”!
今年今日啊,
你的坟上已是绿草萋迷!
孩子啊!你使我在贫穷的日子里,
快乐了七年,我感谢你。
但你给我的悲痛
是绵绵无绝期的呀,
我又该向你说什么呢?
一年了!
春草黄了秋风起,
雪花落了燕子又飞去;
我却没有勇气
走向你的墓地!
我怕你听到我悲哀的哭声,
使你的小灵魂得不到安息!
……
这是高兰(1909~1987)《哭亡女苏菲》的开头三节。“九一八”事变后,正在燕京大学读书的高兰即参加卧轨南下的学生请愿,投身抗日救亡活动。1941年,女儿苏菲因患疟疾无钱医治而夭亡,葬于重庆歌乐山下。一年后,高兰写下了这首给女儿的悼亡诗。在痛失爱女的一字一泪的诉说中,交织着对日寇侵略者的控诉,和对那个黑暗不公的社会的诅咒。在当年大后方各地的诗歌朗诵会上,此诗的朗诵,总能让全场上下为之失声恸哭。其现场效果和感人程度,旧体诗岂能望其项背?
说到传习和艺术经验的积累,旧体诗的记忆和背诵是一种传习,新诗的朗诵和表演何尝不也是一种传习?而读者的审美心理是可以培养的,新诗的朗诵让听众为之共鸣和感动,就是新诗得到认同的表现。写过旧体诗和大鼓词却没写过新诗的作家老舍,在听过诗歌朗诵之后说:“这两个诗歌朗诵会给我一个印象:文句有长有短,合乎口语的条件的,都能念得好。因此我对自由诗的前途,颇抱信心。……太整齐的句子,念起来别扭。”经过近一个世纪的探索实践,新诗也积累了相当丰富的艺术经验。不利于传习和艺术经验的积累的因素当然也是有的,但那首先是诗外因素,譬如中学语文教材所选新诗篇目的陈旧和僵化,对新诗信誉造成的损害,对新诗与读者关系造成的疏离。
新诗格律化质疑
鉴于新诗因随心所欲而造成的形质松散之弊,一种建设性的主张,就是试图限制其自由,约束其散漫,就是倡导新诗格律化。从20年代初到世纪末,这种倡导代不乏人。例如,闻一多就提出了“三美论”:“新诗的实力不独包括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辞藻),并且还有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何其芳相信,“一个国家,如果没有适合它的现代语言的规律的格律诗……是一种不健全的现象,偏枯的现象。”吕进认为,“严格地说,自由诗只能充当一种变体,成熟的格律诗才是诗坛的主要诗体。”
如果新诗是一片自由生长的冬青树,格律化并不是要将它连根铲除,而是想按自己理想的尺寸和式样,对它进行大规模的修剪;如果新诗是一位“裸体美人”,格律化不是要处死她、监禁她,而是要给她穿上规范的制服。格律化不是要剥夺新诗的生存权,而是要限制新诗的发展权。
格律化的倡导者们所设计的“现代格律诗”是什么样子呢?分行,已是共识,押韵,除了“素体诗”的嗜好者,也没有问题,自由诗大多已是这样。现代格律诗的特征主要体现在行与节的建构上,一般认为,行要均齐,节要匀称。
行的建构,有两种基本意见。闻一多的格律理想是“建筑美”,强调视觉效果,兼顾听觉效果。其建行要领是“字”的整齐,兼顾音节调和。例如,其《死水》每一行都是九个字、四个“音尺”,每个音尺为两个字或三个字: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
不如‖多丢些‖破铜‖烂铁,
爽性‖泼你的‖剩菜‖残羹。
……
何其芳的格律理想是节奏感,强调听觉效果,其建行着眼于“顿”的统一。每行须有一定的顿数,可分三顿、四顿、五顿几种不同的句式。在长诗中,如有必要,顿数可以变化。例如,其《听歌》每一行都是四顿,字数有参差,每一顿的字数也从一字到三字不等:
我‖听见了‖迷人的‖歌声,
它那样‖快活,‖那样‖年轻,
就像‖我们‖年轻的‖共和国
在歌唱‖它的‖不朽的‖青春;
……
节的构成,可能是受民歌和古诗绝句的影响,无须更多的提倡,不少人已倾向于四行一节,也有实验两行、三行、六行、八行等一节的。至于一首诗应该有多少节构成,则没有一定之规。外来的十四行诗(商籁体)的四四四二、四四三三等分节方式,也不时地被一些诗人采用着。
每一行多少顿?每一节多少行?每一首多少节?以及押韵方式,这是现代格律诗的格律要素。可是,要形成诗人和读者公认的格律谈何容易!新诗格律化宽也不是,严也不是,格式多也是不是,少也不是,处处都是悖论。
闻一多主张“新诗的格式是相体裁衣”,即“根据内容的精神”,“由我们自己的意匠来随时构造”,因而“新诗的格式是层出不穷的”。可是,这样“相体裁衣”,即一人一款,一诗一式,层出不穷的格式,或“诗体的无限多样性”(吕进语),实际上就是否定了格律诗,认同了自由诗。有无限多的款式,就等于没有款式,有无限多的格律,就等于没有格律。试想,唐人的近体诗如果不是只有五七言律诗、绝句有限的几种格式,而有着无限多样的格式,那诗歌早就自由化了,还用得着几千年以后再来破旧立新吗?
作为新诗格律化成就的一次检阅,邹绛(1921~1996)编《中国现代格律诗选》即体现着“多样性”精神。这本诗选分为五辑:第一、二辑所收作品的格律已不甚严谨,何其芳的《花环》诗句参差不齐,即在其中;第三辑,只要是两节形式相同就算作格律诗;第四、五辑更为宽泛,艾青的《盼望》也被选入,可能是因为这首诗中有两节的形式相同,即算作一种随机创造的格律吧:
一个海员说,
他最喜欢的是起锚所激起的
那一片洁白的浪花……
一个海员说,
最使他高兴的是抛锚所发出的
那一阵铁链的喧哗……
一个盼望出发
一个盼望到达
如果“裸体美人”是自由诗,美人着装便是格律诗,那么,着装渐次减少,减少到泳装,减少到三点式比基尼,还算是格律诗吗?这个世纪,人们倡议和实验过的“现代格律诗”式样繁多,难以计数,但着装严整的少,“短、透、露”的多,这各式各样的“现代格律诗”,与其说是格律诗,不如说是半格律半自由诗,其中相当多的干脆就是自由诗,是自由诗的各种形式。
何其芳想必是看到了相体裁衣、一人一款的不大可行,他的《话说新诗》期待着:“将来也许会发展到有几种主要的形式,也可能发展到有一种支配的形式。”可是,要诗的内容和形式脱节,情感律动与格律脱节,不管身高、三围、雅俗、文野,要给天下所有的美人都穿上一套或几套统一的制服,这行吗?“五四”先驱们正是想要解放格律对思想情感的束缚,才毅然弃旧图新——抛弃旧的格律诗,创造新的自由诗的呀!
人们看到了,新诗格律化处于两难境地,“过于严密,容易限制流动的诗思诗情,过于宽泛,纵然建立一大堆诗体也失去意义。”
时至今日,新诗格律化应者寥寥,成绩远不乐观,闻一多式的“相体裁衣”的结果是新诗的继续自由化,何其芳期待的一种或几种主导的新诗格律并未兴起。倡导者自己拿出的现代格律诗的样板作品,如闻一多的得意之作《死水》和何其芳精心打造的《听歌》,也都缺少垂范的魅力。
九言诗在现代格律诗的倡导者那里曾经备受青睐。《死水》就是一首九言诗,尽管闻一多自我感觉良好,它在形式上却未免失之于“死”。林庚这位九言诗的热心倡导者认为,中国诗的句式,从四言到五言到七言,再到九言,是合乎逻辑的发展。他甚至设计了九言诗的“五四体”,把一个九言的诗句分为上五下四,如“未来在等待‖谁的记载”,认为这样最符合民族传统和口语特点。但九言诗的设计仿佛也是曲高和寡,与各种式样的“现代格律诗”的实验一样成绩欠佳。偶尔发现,邵燕祥1957年夏天到武汉长江大桥工地采访,还写过一首九言的《箫》:
你可能吹响这管洞箫,
就让箫声在江上缭绕:
吹得远天拍打着江水,
吹得沙岸上江水来潮,
吹得那云龙嘘气挂脚,
漫漫长江被烟雨笼罩,
吹出了虹霓天上的桥,
又把它吹落江水滔滔……
九孔洞箫是我们所造——
万里长江上第一座桥。
尽管诗人说,“当时坐在武汉蛇山顶上一个小石凳上,望着刚刚合龙的桥身,云天辽阔,江水浩荡,俯仰今古,遥想未来,很有些自得。这也是我第一次认真地作诗体试验。”作为读者,我还是更喜欢他的自由诗,如《普希金逝世一百五十周年祭——在枙世界文学枛、外国文学出版社的纪念会上朗诵》:
是谁杀死了
亚历山大·普希金?
是你吗,丹特士?
是你吗,第三厅长官?
还是你,沙皇
尼古拉一世
一颗黑色的子弹
射中俄罗斯的良心
俄罗斯的良心在淌血
俄罗斯的大地
在颤抖啊!
谁是杀害自由、光荣与天才的刽子手?
你们
双手沾满鲜血的一群
你们杀害了普希金
你们的罪恶得逞了
你们以为
决斗
就此结束了吗?
亚历山大·普希金
倒在枪声血泊里
而历史
把挑战的手套
抛向冬宫!
一九八七年二月五日
慷慨陈词,大义凛然。诗的力量源于一种信念,即民族良心不可侮,胆敢将罪恶的子弹射向民族良心者,必将得到历史的无情报应!而“你们以为/决斗/就此结束了吗?”“历史/把挑战的手套/抛向冬宫!”这样练达的诗句,如何能够格律化,如何裁为九言呢?
九言诗并非20世纪的新生事物,宋、元、明代就不断有人实验,九言诗却始终走不出实验室。元代天目山僧人明本的《梅花诗》就是九言诗实验室里的一个标本:
昨夜东风吹折中林梢
渡口小艇滚入沙滩坳
野树古梅独卧寒屋角
疏影横斜暗上书窗敲
半枯半活几个恹蓓蕾
欲开未开数点含香苞
纵使画工善画也缩手
我爱新诗故把新诗嘲
车前子(1963~)的《红烛——读闻一多诗后》也是这么一个标本(其韵式亦为“抱韵”)。其最后一行不知是故意还是不得已留下的破绽,仿佛寓示着诗人对这种格律追求的放弃:
远古时代有一位匠人
一生制了无数支蜡烛
有次手指被生活割破
那天就是红烛的诞辰
黑暗糊起茅屋的苦涩
红烛宛如竖着的手指
血滴在敲打他的桌子
匠人死了,还没燃尽夜色
严谨的格律论证和完美的格律设计,还不如几首典范之作更有号召力。缺少垂范之作,再好的论证和设计都是劳而无功的。
格律化的尴尬,使人们不禁要怀疑,新诗的出路真的在于背离自由化的初衷,对自由的语言形式重新加以约束,建立新的格律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