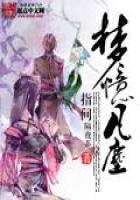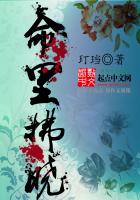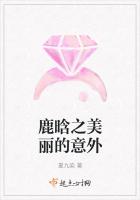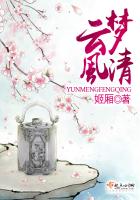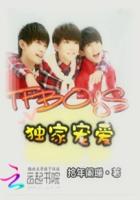用编年方式检点各种各样的文化记忆,为人类保存和反思自己的历史提供了许多方便和可能,也增加了人们对时间的期待与憧憬。然而,第一,时间是否就是刷新历史的油漆,翻开新的纪年、新的年份是否就是全新的事物?第二,即使时间刷新了我们的许多记忆,但它能否马上改变诗歌的象征体系和想象方式?
也许我们不应该期待在新的世纪、新的年份一觉醒来就成了新人,就读到全新的、“断代”的诗歌。因为21世纪初的诗歌,无论从何种意义上,都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诗歌探索的延续:仍然在城市化、世俗化的语境中走向边缘化;仍然是一种转型的、反省的、过渡性的写作,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仍然具有疏离“重大题材”与公共主题的倾向,以个人意识、感受力的解放和趣味的丰富性见长,而不以思想的广阔、境界的深远引人注目。这是一个有好诗人、好作品却缺少大诗人和伟大作品的年头。
这是一个平凡的年头,虽然我们生活中也出现了“非典”这样相当不平凡的事件。但短暂的骚动混乱过后,市场依然繁荣,普通人的生活仍然在延续,诗人也仍然像以往一样在边缘处境中挣扎。21世纪初的中国诗坛没有20世纪初的中国诗坛热闹,百年前的诗坛弥漫着“诗界革命”的火药味,而诗歌进入21世纪,则是运动式诗潮的隐退,沙龙式探讨对流派式集团风格的替代,个人写作对集体写作的疏离。20世纪末的“民间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的争战并没有得到持续,“下半身写作”的道德反叛也没有吊起多少人的胃口。诗坛似乎从来没有像近年这样风平浪静。
无须讳言,近年的诗坛远没有20世纪八九十年代热闹,平庸的诗人和作品也大量存在。但平静能否等同于沉寂?平凡是否就是平庸?也许探索并没有中断,可圈可点之作也不见得会比别的年头更少。伟大的时代照亮诗人的激情与灵感,诗人分享了时代的光芒,因而许多诗也是时代的反光;在平凡的岁月,诗则必须自己发光,以自身的价值求得人们的认同,凝聚自身的光芒照耀时代。因为时代平凡,因为被放逐到边缘的边缘,所以这是一个“非诗”的年代,但是上帝与魔鬼都不管诗歌,它不再成为各种势力争夺的中心,诗人也就有可能反省和回到自己的位置,追求自己的理想,因此可以说非诗的年代也正是一个从事诗歌的时代。问题是,诗歌是否出自我们内心的需要?我们的情怀、境界、眼力、才华,以及训练和技巧,是否经得起诗歌要求的考验?
进入21世纪,一些老诗人的创作已经过了鼎盛时期,他们的产量已经不如青壮年时代。但读公刘《不是没有我不愿坐的火车》、《天堂心》等遗作,你肯定会同意这都是生命之诗,体现诗人全人格的诗。而彭燕郊的《消失》与《叫喊》,则把个人发声当成了抵抗消失的唯一方式。应该说,这些作品也有很强的时代感,正如邵燕祥的《美丽城》、《网络》、《后祥林嫂时代》,无论题材还是意象都有很强的现实感,与他的杂文所体现的感时忧国精神一脉相承一样。然而,人们还是能明显感受到视角的调整变化。大致说来,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大多数诗中的说话者,往往是直接面向时代的,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说话者则更注意感受人在时代的命运,以个人记忆、感受与想象同时代对话。这时候的时代,不再单纯是一个人人追逐的太阳,而同时也是一个体验与反思的对象;它也不再是被文件、报纸的观念所规范的时代了,而是像朱朱《车灯》所书写的景物,是具体的、片断的、分散的,需要“重新丈量”的。“生活”太大,“时代”光暗明灭,不仅所见有限,无法“测知一堵墙的厚度”,而且“不完美的大脑”总被搅晕,因此,他们放弃了“宏大叙事”的野心,宁愿做不成一个“时代的诗人”,也要忠实于自己感觉与记忆,“以笨拙面对真实”。
表面上看,中国诗人变得不那么自信,不那么高瞻远瞩,不那么具有时代的洞察力和预见性了。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或许他们也正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时代性”的见证,即开放的、多元的过渡时代的见证。当然,诗歌见证这个多元共生的时代,与“生活”见证这个时代是不一样的,生活是GDP变化、制度调整、风俗变化和时尚迁移;而诗,则要通过语言捕捉与想象这种种变化在人心中留下烙印。这是否就是近些年来相当多的诗歌重视感觉、记忆与现实的关系,而不像20世纪初的诗歌更关心现实与未来的关系的原因?我相信,在这本《2002-2003中国诗歌年选》中,最有味道的诗,大都是处理个人感觉、记忆与现实的关系的诗。像朱朱的《皮箱》、庞培的《少女像》、黄灿然的《祖母的墓志铭》和王小妮的许多诗作,读他们的诗,你也许会认同张曙光《一个诗人的漫游》里那个被中年危机与生活困惑所夹击的说话者的判断:“回忆正逐步取代希望,它安抚着我们的生命。”但是,回忆正逐步取代希望是实,却不见得能安抚内心。因为这些大多不是怀旧的诗,怀旧的情怀能够带领人们“回家”,就像中国许多传统的古典诗词,总是把人们带到遥远的过去一样。然而,中国那些传统的田园世界,那些唐诗宋词中的美好记忆,似乎都变成了天边正在消失的晚霞。我们甚至无法像闻一多那样读出菊花丰富的颜色和意蕴,无法像戴望舒那样从记忆中找到村姑的神情了。一个叫做“现代”的东西早把我们拽下牛车马背,装进了火车、飞机。时间已经在网络高速公路上飞奔,而空间正在分崩离析,建筑物拆了又建,建了又拆,我们的感官每天都在承受爆破、打钻、搅拌的轰鸣,现代人哪里有心情怀旧,21世纪以来又有多少旧可怀?
因为不再轻易地相信未来,而传统文化又遥远得不可追回,所以许多诗人只能以个人经验、记忆去辨认破碎、暧昧的当下生存。你不妨认真读读辰水发表在2002年《天涯》上的《在乡下》(外六首),看看像刺一样揿入灵魂的乡村记忆:
在乡下我常常为了割到更多的草
会尾随着那些茂盛的草来到河边
河的众多分岔向四下里流去
通常我会知道它们流向哪儿
或者是在哪儿因干枯而死掉
在这些河滩上还有那么多坟墓
我至今都没有弄清楚哪些是属于我们这个
家族的
平时我为了尽快地赶回家去
就会抄近道穿过这大片的坟墓
这时我会比平常走得更快些
我相信这组诗是近年来乡村题材诗作中最出色的作品之一。不仅仅由于它呈现出记忆中的乡村世界的“真实”,也由于它不动声色的表现力。什么叫做“沉哀”,什么叫做“悲凉”?可不是直着脖子喊叫出来的。这是一个少年经常经历的情境,再熟悉不过的景象,也完全以乡下少年的抒情观点写成。因为年少,因为熟悉,诗中的说话者似乎没有新鲜的东西要告诉我们,似乎既不感到高兴也没有悲哀,即使穿过有许多坟墓的河滩,也不过“这时我会比平常走得更快些”。然而,在阅读者的感受中,这个由青草、河流、坟墓构成的“乡下”世界,青草的荣枯与草民的生存,流动的河流与时间的变化,弄不清的坟墓(连碑都没有)与无声无息的生死,不是没有关联的,而“这时我会比平常走得更快些”,也不通向“为了尽快地赶回家去”的因果逻辑,而是呈现出某种下意识中的害怕。这样的诗歌世界不是文人想象中的田园牧歌世界,“乡下”不是为了对比城市才得到表现的。许多年以来,多少人自以为代表沉默的人民说话,但很少看到这样摇撼心灵、没有矫情的诗作。不是因为他们不同情农民,甚至也不全然因为不了解乡村的生活,而是由于戴着别样的眼镜,因此被小康生活遗忘的农村社会,似乎是理所当然地在文学中被扭曲和遗忘。是的,乡村也在变化,现代化的声浪也席卷、摇撼着沉默的土地,但有多少人能感同身受地理解中国农民在城市化进程中所付出的代价和牺牲?有谁像辰水这样通过熟悉的情境传达转型时代的戏剧性?辰水不止一首诗写到那些在春夏之交去城里打工的农民,他写那些走在去北京路上的民工,衣着如何不合时宜,女人如何默默低着头跟在男人后面,“只有那些孩子们是快乐的/他们高兴地追着火车/他们幸福地敲打着铁轨/仿佛这列火车是他们的/仿佛他们要坐着火车去北京”;他写民工们如何被那帮油腻腻的家伙装上马车,他们不知道马车会把他们拉到哪儿,只有拉车的马在耳鬓厮磨、相互缠绕,“它们愉快地拉着我们,它们真像一对热恋中的情人”。这些诗作都聚焦于某个具体情景的组织,用的是“叙述”而尽量避免抒情和议论,似乎接近20世纪90年代末一部分诗人热衷谈论的“叙事性”,又可以印证另一部分诗人对“拒绝隐喻”的倡导,但它的朴素、凝练、简洁和有力,它的戏剧性情境所产生的艺术张力,却也对诗歌的叙事和表达的直接性,提供了新的启示。
中国诗歌抒情视野最重要的调整,是它已经不再简单通过空想未来、承诺未来去批判现实,也不通过“忆苦思甜”来论证“现实”了。它对诗歌写作最重要的意义,是在认识论的根源上偏正了长期占主流地位的所谓“现实主义诗歌”对主体与世界、语言与现实关系的误解,从而打开了从个人的感觉、意识接近和想象世界的道路,让语言与现实能够在磋商对话、互相吸收中呈现出独立的个人品格和艺术趣味。关于这一点,黄灿然在《删改》一诗做过非常有趣的探讨:朱伯添曾是忠实于“原文”的新闻翻译员,但是随着经验的累积、知识的增长和了解世界的深入,他发现,他要忠实的“真实”实际上已经被“删改”过了,因此一直恪守的准确度和清晰度发生了动摇,不得不对有些报道再度删改。他开始意识到,翻译的“忠实性”,其实有一个忠实于被镜头选择过的“原文”,还是忠实于知觉、情感的“真实性”问题。对于一个翻译来说,“当那恐怖的画面/掠过他的脑际/忠实性无非是镜头中/巴格达夜空里烟花似的炮火/而真实性是白天里/赤裸裸的废墟”。
在某种意义上,诗也是一种翻译,把未被言说、无可言说的东西变成一种可意识、可言说的东西。但在我们这个利益争夺、市场称雄、传媒掌控的后现代社会,人实际上生活在符号世界而不是生活在真实的感性世界中,连文化生产也变成了一种产业,文化产品在复制、借贷、挪用、流通中已经变得面目全非。现代诗人所遇到的问题,也正是《删改》中的译员所遇到的问题,不是命名的困难,不是忠实不忠实“原文”的问题,而是在你未说话之前,事情往往被“镜头”框限过,被人们说过、写过,“真实”已经被遮蔽了,只有经过“删改”才能让它重见天日。
如何在层层着色、层层改写、层层覆盖,充满了暧昧性的“现实”中“忠实于真实性”?一部分诗人主张放弃对世界的虚假承诺,面向真实平凡的个人内心经验。王小妮甚至在诗中宣称:“到今天还不认识的人/就远远地敬着他/三十年中/我的朋友和敌人都足够了/……我要留出我的今后/以我的方式/专心去爱他们”(《不认识的人,就不想再认识了》)。表面上看,这是一首拒绝世界,坚持个人经验、记忆与处世方式的诗。然而,文本中的说话者,并不是真的要延续旧人旧事的记忆,坚持过去的生活方式,而是在反省和清理自己的记忆和经验,面对世界与自我的真实。王小妮的诗,就题材而言,似乎都是琐琐碎碎的日常小事,平平凡凡的人间感情;就表达方式而言,也不执意追求现代主义的陌生化和技巧的繁复性。然而,她从日常中道出了人们生存的真相,从朴素中获得了表达的直接性。你读读《西瓜的悲哀》,相信你不由得要惊叹作者从一件日常小事抵达普遍境况的能力。然而,解读那种事因人生、人为事累的“无缘无故”的人生呈现在水火中煎熬的生命状态,诗人并不简单导向社会批判的主题,而是进行自我与世界的双重探索。因此,《我就在水火之间》中的“水深火热”,既是生存的体验,也是自我的读解;既有含蓄的讽刺和指责,也有热爱、同情与自嘲。
读王小妮这些从个人经验、感觉省察生命与世界的诗,人们会明显感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诗歌承担世界方式的变化。我曾把这种变化概括为诗歌英雄主义的隐退,直接参与生活的抒情方式的调整和语言意识的觉醒。我认为这种变化具有解放感觉、意识和想象力的意义。事实上,如果说王小妮那样的诗,是对个人经验的解放,通过个人经验的矛盾、丰富和复杂性的品味去触摸世界,那么,像陈东东、臧棣的诗,则体现了个人意识的敏感、自由和流动,充分展示了意识与现实、意识与经验、意识与语言的互动。有趣的是,不同于王小妮从日常感受、日常细节去探索意识与情感的转变,臧棣更擅长以多样的、不断繁衍生长和转变的意识去吸纳日常细节,形成充满妙趣的对话空间。像《宇宙是扁的》处理的是一个荒诞的题材,却通向日常经验里平凡与神奇交织现象的揭示:明明知道是光天化日里的谎言,是闭着眼睛说瞎话,但为什么还是被牵引,不仅喜欢,而且在短时间内让荒谬主宰了一切?又如具有寓言色彩的《反诗歌》,反讽一种“反诗歌”的阅读方法,却借助羊的现象讨论美和想象力是否可以作经验的还原问题,触及诗歌阅读的诸多偏见。臧棣的这些诗歌,以意识与语言的互动打破了传统诗歌写作的情景关系,冲破了生活决定论的经验主义美学,为现代汉语诗歌的写作展示了一种新的可能性。这是一种追求意识和语言的开放性和生长性,胜过追求文本经典性的写作。
从具体的个人经验出发探索意识的转变与从意识的生长变化去讨论经验,可能是近年诗歌最值得注意的景观。它标示了20世纪90年代“个人化写作”的延续和深化,进一步昭示诗歌必须自己发光的时代写作的可能和考验:“个人化写作”既是个人言说权的争取,对历史“宏大叙述”与时尚的化约性的反抗,经验、意识和想象力的自我解释,又是对个人言说境界、能力的一种更高的考验。
(《2002-2003中国诗歌年选》,王光明编选,花城出版社,2004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