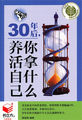雨还是不停地下着,那些细小的白花还在地上,被水浸泡得都不成样子了,有的被践踏得发了黑,落到地里的,早已成了泥了。我也没想什么,径直出了新村,朝着一辆开来的公交车飞奔过去。
还是夜里回来。这雨为什么还在下呢?非要把人的心境往灰蒙蒙的色彩里拖。我的心里竟记挂起那些零落的小白花来了。可是进了新村,再也看不到那一长条一感伤是不是一种奢侈长条的白色物了。再走几步,到有路灯的地方去看,还是如此。那些细小的白花其实并非不在,而是都化作一摊摊污物了。弥散在空气中的暗香也被抽走了,一种植物在水中浸泡久了散发出来的水臭味,湿漉漉、沉甸甸地往肺里摆,让人陡然就感伤起来。这就是这些小白花的命运啊,不久前还在树上快快乐乐地进行着的花期,突然就被一场淫雨取消了。这些微小的生命,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微小而羞涩,它们没有保留地奉献着自己的芳香,现在,不但过早地消逝了生命,就连芳香,也被一股水臭味取代,零落成泥也成了一种奢侈。
很快,我又为自己的感伤而感伤。
很久以来,以为是生活加快了节奏的缘故,觉得自己除了快乐、烦躁、恼怒、担忧之外,再也没有了一些复杂的情感,比如忧愁、感伤、温润、长久的感动等等。忙碌的生活使人的情感变得简单,谁还有闲暇来仔细照顾自己的内心呢?内心被几种简单的情感瓜分,此起彼伏,错落无致。这是另一种荒芜啊!
现在,感伤毕竟来了。我在“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年岁,看到落花就会有所触动。后来的岁月,我对落花已麻木,可是看到那么多正在开着的花被摧落,被践踏,内心会有所波动。但如今,感伤一直要穿过重重麻木,一直到落花成泥无着,花的香气被水的臭味羞辱,才来到一个人的心田。
这究竟是不是一种奢侈?
城市夏天
在城市的夏天我就像一条鳗鱼,身子总是湿漉漉、滑腻腻的,让人有一种厌烦的感觉。随你怎么洗澡,就是洗不尽。汗水似乎带着油,冒出毛孔。谁能把毛孔堵住啊!
在一个空调时代,人居然还有这种感觉,真是太奇怪了。问题是,我是一个极不喜欢空调的人,我觉得那造出来的冷风太鬼,老往人的骨头里钻,有一种彻骨的冷。现在的情况越来越糟糕,电风扇也让我感冒了,不想它对着我吹,特别是在我睡着的时候,时间一长,电风扇会吹得我浑身乏力。我最讨厌这种状态,脑子不知道在想些什么,想干什么又没力气去干。
我从乡下进城已有八年,在这一点上老是进化不了,想想真是气馁。二十岁以前,我在浙南乡下生活、读书,不知空调为何物,家中唯一的一个电风扇,跟宝贝似的,记忆中没用过几次。可我那座在海边的村庄,本身就是一个天然的空调器,夏日里感受从南边吹来的凉风,让人有说不出的满足。我在地里干活,我在海里捕蟹,太阳毒时,就到树下一躺,整个人的重量就像被提走了似的。我深信这些午睡是我这辈子最绵长最无忧城市夏天的午睡,就像蓝色沉入海底,而大海平静得像永失风暴,涛声把睡神迷醉。
照理说,我是个坐办公室的人,上海这座城市再怎么热,跟我似乎关系不大,可因为我跟空调过不去,又总不是它的对手,就一直生着闷气。一个人在家的时候,我可以自主了,拒绝空调,也不开电风扇。虽然太多的建筑物把风挡住了,我的身子总是湿漉漉、滑腻腻的,但我宁愿一遍遍洗澡,也不到有空调的房间去。我有这样的感受:在烈日下奔走,大汗淋漓,一到有空调的大厦,汗水突然被夺走,就有一种力量被突然夺走的感觉。这种感觉,比我大汗淋漓的时候难受多了。
何时能在城市的夏日躺在一棵树下乘凉,睡很长的午觉,并且听到大海的涛声?我不指望了。我的希望是,在搬进新居的时候,有一个房间不装空调,可供我藏身,与城市的夏天作无奈的抵抗。
内心的恐惧
我的左膝韧带撕裂了。毫无疑问,为了我年轻的躯体能够继续行走,我被送上了手术台。在我25岁的生命中,从来没有生过像样的病,突如其来的灾难让我毫无准备,如果说我的悲观和忧悒还只是天空中的一片乌云,我内心的恐惧则像傍晚时分苍茫四合的暮霭。
从我七点钟进手术室至医生们到来,这种恐惧在加剧。在开着空调的温室内,我的身体颤抖得越来越厉害。陪伴着我的一个护士小姐显得心不在焉,她东张西望,中间还出了两趟门。她似乎要下班了。我的这个想法马上被证实了,她甚至都没有跟我道一声再见,一到时间就转身走了,留下我一个人在空荡荡、明晃晃的房间里。
来了一个老阿姨,来了两个老阿姨,来了三个老阿姨。她们都是慈祥的护士,她们毫不犹豫地把我的裤子扒了下来,把我的手脚捆住,一边挂吊瓶,一边量血压。她们跟我说着话,以一个母亲对孩子的口吻。我当然也不闲着,一会儿要求她们给我的手臂垫上毛毯,一会儿要求她们再往我的身上盖床被子。这样,内心的恐惧才猫着步,放慢了摇动我身体的速度。
麻药上去了。她们拿着一根针,刺我的腹部、屁股和大腿。还疼吗?她们问。还疼。我说。她们还是拿着那根针,刺我的大腿,问我,还疼吗?我说,不疼了。
她们又刺我的腹部和屁股,问我,还疼吗?不疼了,我说。下半身已毫无知觉,我伸手去摸了摸,皮肤很粗糙。小时候我在乡村放牛,摸在牛背上的感觉就是这样。我一遍遍地伸手摸着“牛背上的皮肤”,回忆起在乡村度过的美好童年……
等我醒来的时候,医生们都在无影灯下埋头干活。
我的面前挡着一块白布,我不知道医生们在忙什么。过了一会儿,电钻钻墙面的声音地响,好像隔壁在装修房子。我不相信这是医生们在钻我的腿骨,好在上面安下一个螺丝,固定住我的随时会缩回去的韧带。我固执地想,如果真是在装修大腿,那也是别人的腿骨——没有任何感觉显示,这是我的腿骨。真的,我才25岁,从小梦想有朝一日能走遍中国。
他们开始在我的肌肉上穿针引线,熟悉程度就像我的母亲在缝我的一条裤子。但他们花的时间太多了,让我怀疑,这条裤子已经从裤腰裂到裤脚。我厌恶这样的裤子,虽然我母亲在世时一直跟我说:缝一缝,又是一条新裤子。想到这里,我内心的悲伤就像月圆之夜的潮汐,满了上来。
夜鸟
邻居家养着几只鸟,是鹦鹉、相思鸟还是别的什么,就不得而知了。因为是放在铁门与房门中间的一条小小的过道里,铁门上还挂着长长的布,见不着它们。
而我白天睡觉,夜里上班,与邻家人都不曾打过照面,更别说他们家的鸟了。
我与这些鸟儿发生关系,完全是因为厕所的一扇窗户。我租住的是老式公房,厕所不通风,唯一的窗户朝向邻家的过道,很不合理,却存在着。夜里两三点回来,上厕所、洗澡,要开灯,就弄醒了这些鸟。先前几次,它们小心叫着,声音很低;时间久了,它们似乎就习惯性地醒来。灯亮了,它们以为黎明到来了,就齐声歌唱起来,分贝很是不低。
对这样的声音,我并不反感,也许是我内心有一种复杂的情感吧。这些鸟儿,何曾见过多少次黎明?至多也只剩一些残存的记忆吧。在这过道之中,夜里是黑,白天仍是黑。我曾在午后观察过几回,即使发出再大的声响,也不见它们有多少回应,哪像夜里我亮灯时叫得欢!这么说,我内心之中多少还是有些故意为之,开着灯,把光亮透给这些夜鸟们了。至于终究是好是坏,却夜鸟是未及细想的。
有一天夜里,两三点,我回来时照旧是进厕所,打开灯,逐一洗漱。夜鸟又叫开了,我已经习惯了。但这次有些不一样,邻居开了房门出来,在过道立了会儿,似乎想跟我说话,终究又什么也没说,只是把鸟笼提进去了。我怔了怔,觉得这夜鸟的叫声是大了点,把他们吵醒了,心中有歉意。
第二天,我还在睡着,邻居过来敲门,跟我说,夜里上厕所可否轻一点,因为这些鸟醒来后,总是吵得他们睡不好。我跟他道明了我上夜班的实情,并且说,不是声音轻重的问题,而是灯光。邻居没再说什么,走了,大概是不好意思叫我夜里上厕所不开灯,更不好意思叫我不上厕所吧。他很重地关上了铁门,从此再也没有来找过我。
夜里回来,还是开灯。没有办法,夜鸟们又叫开了,分贝很是不低。邻居出来了,把鸟笼提了进去。
此后夜里回来,还是开灯,但再也没有听到夜鸟们发出声音。它们肯定已经不在那儿了。
它们会在哪儿?阳台,客厅,或者已被送了人?我甚至可怕地想到:它们已被处死!
这样一想,让我的内心感到发颤,继而想到:也许开灯和鸣叫,我和夜鸟,都是无奈的,何必道什么“给予了黎明”和“发出了欢叫”呢!
后窗
高架桥。上坡。一个人的出租车上,看到了天。地呢?眼前只有一片被开掘着的天空,于是涌起了悲壮,涌起了豪情。这么大的空间啊,仿佛只为我一个人开。
这是瞬间的感受。在市郊的白天,太阳明晃晃的,空气竟然很好,看得到蓝天和白云。
要是在夜晚,高架桥上奔跑的汽车会少很多,道路两旁的街灯整齐地亮着,明亮的灯芯外,一片橘黄色的迷茫。寂静无声。飞速行走的小汽车,将一种孤独高速返回。
很多时候我们都在前进,我们向往着前方,因为希望和曙光总被告知在前方等待我们。于是,勇往直前总是好的,畏惧退缩总是坏的,瞻前顾后呢,是让人唾弃的。
前进,所向披靡,所以也就可以掩盖一切。所以牺牲总是难免的,总是正常的,在前进这个充满光芒的字眼前,一切暗淡都会暂时地失去阴影。鲜血沸腾着,激情燃烧着,并不觉得是千军万马在过独木桥,而后退几步,就是一条通衢。
所以我说,人要为自己开一扇后窗。
也是在高架桥上的一次经历。那天疲倦至极,坐在出租车后座,头靠坐椅不经意往后一望,哇!好大一片天地,白云正在徜徉,蓝天无比纯净。
后窗开启的,竟是一片无限深远的天地。而再望前方,一片灰蒙蒙的天,一块块压过来,不见尽头。
是的,要为自己开启一扇后窗。在拥挤的城市,停一下匆忙的脚步,望一望飘扬的旗帜;在人群汹涌的地铁车站,让一辆列车开过,找一张空出的椅子坐下,静候下一辆列车的来临;在彻夜难眠的夜晚,推窗,接受月光的朗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