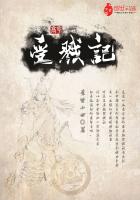引言
芭拉蒂?穆克吉于1940年生于印度,1961年获得英语硕士学位后离开印度去美国留学。之后,她与加拿大作家克拉克?布莱司结婚,并于1969年获得爱荷华大学英语与比较文学博士学位。经过印度、加拿大和美国三地的不断辗转后,1980年,穆克吉夫妇最终定居美国,由加拿大公民变为美国公民。1988年,她以短篇小说集《中间人》获得美国“全国图书评论界奖”。印度学者注意到,作为印裔美国小说家的穆克吉已经受到了世界各地评论家的高度关注。“她被大家公认为表达流亡与移居意识的代言人。”穆克吉二十多年的创作可以分为三个时期进行研究。从1971年出版处女作长篇小说《老虎的女儿》到1979年为第一个时期即流亡或曰自我流放时期;从1980年到1988年为第二个时期即自动流亡到移民定居的过渡期;1989年到1997年出版长篇小说《留给我》为移居期。与“殖民文学之父”吉卜林影响了一些殖民文学作家相似,奈保尔的后殖民创作对于一些后殖民作家也产生了深刻影响,这以他对穆克吉的影响尤为明显。在穆克吉的创作道路上,奈保尔是一个挥之不去的影子。她曾经声称,进行文学创作时,奈保尔是她 “心目中的榜样”。她还说:“我在自己身上隐隐约约地发现了奈保尔的影响痕迹。”1985年,穆克吉出版的短篇小说集《黑暗》(Darkness)在书名上便可见出奈保尔1964年出版的印度游记《黑暗地带》(An Area of Darkness,又译《幽暗国度》,下简称《黑暗》)的影响。晚于奈保尔进行文学创作的穆克吉对大她八岁的奈保尔不仅只有文学技法上的继承,还有艺术思想方面的超越。本文试图从几个方面对此问题进行探讨。
第一节 关于印度的观察与思考
同为印度后裔,奈保尔和穆克吉在作品中不可能回避印度。相反,印度成为他们艺术描写的重要对象,成为他们的作品在英语世界走俏的东方元素。他们书写印度的文体既有自传体游记,也有小说。客观来看,他们在对印度文明的观察和思考上存在一些相似之处。这些相似反映了两位印裔流散作家在世界移民大潮汹涌澎湃前的本能思考。这种思考本身带有前后相因的成分,体现了穆克吉对奈保尔自觉的“学习”和模仿。
作为海外游子的奈保尔,带着童年之梦前来寻根,他期望看到一个美好的印度形象,但他的“西方之眼”却使他更多地看到了印度社会种种愚昧落后的东西,更令他惊讶的是,印度人对此视而不见。西方文化的批判思维和立场使奈保尔在面对印度的现实时,采取了直言不讳的辛辣讥讽姿态,这使部分印度学者异常愤怒。
奈保尔曾经说过:“我从我的过去而来,我就得写我所来之地的历史——写被忘弃的人民。我必须写印度。”奈保尔曾经三次去印度寻根,并出版了“印度三部曲”。奈保尔关于印度文明历史和现状的思考、关于甘地的评价,均集中在这些作品中。奈保尔后来说过:“印度的衰败荒凉使访问者震惊。”他对印度的卫生状况和人们的卫生习惯非常关注。他看到,印度的乡村到处是狭窄残破的巷弄、流淌污水的排水沟、狭小众多的泥巴屋子、混乱相处的垃圾、食物、牲畜和人。奈保尔以人类学家田野调查的方式进行创作,将印度的负面形象放大,展示给他心目中的西方读者,这当然会招致部分印度学者的批判。如C?查特吉怀疑,奈保尔对于印度的负面描写是否“给白人提供一本真实可信的通往印度的指南”?事实上,奈保尔自己就认为,他的书不是写给印度人看的,是写给西方人看的。印度旁遮普大学迈尼教授认为:“奈保尔笔下的印度不是我们的印度。”奈保尔的《黑暗地带》是“奈保尔式的《黑暗之心》”。他将奈保尔比作描写非洲“黑暗”世界的英国殖民作家康拉德。
同为海外游子的穆克吉认为,作为在印度出生并接受教育、居住在加拿大或美国并以英语书写印度主题的作家,她主要是想以自己的审美方式进行文学“发言”,从而再现自己熟悉的印度文明。她承认:“我的审美观是在北美接受教育和居住期间形成的。我是受美国生活与美国小说影响第一代印度作家。”穆克吉坚持反对印度学者对她的印度题材小说的责难,认为自己是美国作家,是向美国读者艺术性地介绍印度。这和某些华裔美国作家的写作立场惊人相似。这种与奈保尔相近的写作立场决定了她在描写印度时所取的西方视角。
在穆克吉的处女作、1972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老虎的女儿》中,离开印度在外漂泊多年的塔拉,带着乡愁回到印度。当年离开印度时使她留恋的印度式时尚建筑,现在则以它的破旧不堪“震惊了她”。火车站在她看来仿佛是一所医院,里面坐满了“病人和残疾人”。在从孟买开往加尔各答的旅途中,塔拉与一个马瓦里人和一个尼泊尔人同处一个车厢。她想,这两个面容丑陋、使人恶心的东方人“将使她的加尔各答之行变得极不愉快”。塔拉后来见到印度人习以为常的麻风病女孩时,竟然恐怖尖叫起来:“不要碰我!不要碰我!”塔拉对印度人物场景的反应与奈保尔第一次印度之行几乎没有什么两样。有人评价说:“塔拉目前的思想意识扎根于她的美国生活……她对印度的反应是观光客或外国人的那种。”塔拉眼中落后而恐怖的印度折射了穆克吉心目中负面的印度印象。在1989年出版的小说《嘉丝敏》中,穆克吉笔下的印度是一个充满了种姓之间血腥冲突的“炸药桶”。她还栩栩如生地描绘了嘉丝敏和其他女性在野外入厕的场景。她写道:“然而,对这些住在附近的妇女而言,野外入厕是建立友情的最佳时机。她们一字排开蹲着,嘴里喋喋不休。我喜欢听她们说话。”这种自然主义描写与奈保尔简直如出一辙,惟一不同的是,穆克吉写的是印度女性,奈保尔写的是印度男性。他们将印度社会的“原始”一面快餐似地摆放在西方的阅读平台上。
奈保尔认为:“印度是虚悬在时间中的国家。”他发现,印度人欠缺历史意识。印度历史的悲哀在于,它缺乏成长的过程。“在印度历史中,你看到一连串开始,却看不到终极的创造。”奈保尔对印度历史的武断在穆克吉那里也有回音。穆克吉在1977年出版的与丈夫合著的印度游记《加尔各答的日日夜夜》中写道:“当然,美国才是我的所爱……美国历史更少让人迷惑不解。”相反,在穆克吉看来,印度历史全是不可阐释的事件。印度的历史事件“没有必须的起因”。这种关于印度与美国历史的二分法不自觉地折射了穆克吉隐秘的东西文化观。她坦率地承认,长期漂泊海外,她对区别于印度循环时间观、具有起点和终点的西方线形时间观有着清醒的认识。这使她身上的印度性变得越来越脆弱。她和奈保尔一样,均带着西方之眼重新打量印度,以线形进步/停滞循环的二元对立法“发现”了印度历史的“不可阐释”。
甘地是印度独立运动的领袖,是现代印度的象征。奈保尔对甘地的社会实践、宗教思想、民族主义意识等各个方面都进行了解构性评价,其基调是贬斥。奈保尔将甘地的一切活动皆与印度的“象征性”联系之。在他看来,甘地亲手操作的纺车被吸纳进“庞大的印度象征体系”中,很快丧失应有意义。它是“达到精神虚无的支撑”奈。奈保尔似乎发现了甘地的一种“洞察力缺陷”,即只具宗教意识而缺乏明确的民族(种族)意识。他特意引用托尔斯泰的话,甘地的“印度教民族主义玷污了一切”。按照奈保尔的逻辑是:“印度缺少意识形态,这是甘地和印度的双重失败。印度人民没有国家观念。”印度学者巴特尔认为,奈保尔是错误的,因为:“如果不是甘地,谁又赋予印度人以国家观念?奈保尔没有意识到,他忽视了甘地的伟大业绩,从而扭曲了自己的视线。”
与奈保尔对甘地的直接贬斥和责难相对应,穆克吉却是以小说虚构的形式对甘地的伟大形象进行后现代式解构。她在1985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黑暗》中收录了一篇题为《虚构的暗杀》的小说。这篇小说以印度旁遮普邦一个锡克教老人即“祖父”回忆暗杀甘地的方式,将甘地放在想象的语境中进行丑化。“祖父”认为,甘地在1947年印巴分治时负有历史责任,因为,他昏庸无能:“但是,甘地这个精神领袖,他对邪恶罪孽又能明白几分?像他那种一头雾水的脑袋怎能看清脚下的粪堆。”“祖父”认为,甘地应该对印巴分治期间印度教徒、穆斯林和锡克教徒之间的宗教大屠杀负责,是他使那些失去丈夫的妇女出于寂寞而勾引男人。“我们是堂堂正正的男男女女,但被吃恰巴底(一种印度食物)的甘地拽进了耻辱的情境里……甘地伤害了我们的妇女……甘地是妇女的敌人。因此,圣雄甘地成了我的敌人。”这就是“祖父”欲暗杀甘地的荒唐理由。“祖父”还恶毒地称:“在我看来,甘地这个禁欲者是历史上最大的强奸犯。”“祖父”的叙述还包括甘地与信徒见面并被暗杀的场景以及寡妇勾引男人的色情场面,颇有东方主义的叙事痕迹。这样来看,《虚构的暗杀》实际上是借一场虚构的暗杀行诋毁丑化甘地之实。和奈保尔一样,穆克吉也忽视了甘地领导印度取得民族独立的伟大业绩,以骇人听闻的“强奸犯”一词粗暴地颠覆了甘地的正面形象,伪造印度现代史,从而真正地扭曲了她自己的视线。
穆克吉虽然在某些方面继承和模仿奈保尔,但他们在某些方面还是有所不同。例如,奈保尔在20世纪90年代后,明显改变了对印度的刻板印象,发现了印度富于活力的一面,对甘地也借助印度人的内部视角进行客观而正面的评价,但在穆克吉那里,即使在她1997年出版的最新小说《留给我》中也很难看到对于印度文明的积极赞美。这似乎与他们书写印度文明的艺术动机有关。在“无根人”奈保尔那里,印度是他的寻根之地,他一再走进印度的怀抱,其心态会随着时间推移和印度的积极变化而阴转多云;而文化灵魂美国化的穆克吉则纯粹只将印度作为一个文学道具,作为她探索第三世界移民如何为第一世界接纳同化的主题的引子和屏风而已。换句话说,穆克吉对奈保尔的继承模仿本身就蕴藏了超越变异的因素。这在穆克吉对自己文化身份的思考和第三世界移民问题的观察中表现得尤其明显。
第二节 关于流放之痛的“模仿写作”
后殖民理论家赛义德说过:“某种程度上,早期的奈保尔也是一位现代知识分子流亡者。”瑞典文学院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说:“奈保尔是一个文学世界的漂流者,只有在他自己的内心,在他独一无二的话语里,他才真正找到了自己的家。”“瑞典文学院二〇〇一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辞”,奈保尔既是一个“内在流亡者”即没有自己的精神归宿,也是一个“现实流亡者”即没有自己的祖国。因此,许多印度学者联系到奈保尔心中的流亡意识来阐释其身份认同危机。他们认为,就奈保尔而言,流亡和家园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奈保尔流亡的基本动机是“寻求身份认同。他的创作便是发现自我的过程。当被一刀斩断实际的家园以后,他用语言来重建小说中的家园”。印度学者潘沃尔说:“奈保尔对自我身份和周围世界的探索,如关于民族、历史、族群和文化的探索,已经形成一种广义的‘自我流亡诗学’。”巴特尔说,奈保尔可以说是“双重流亡或曰二次流亡者”。他属于彻底的文化无根:“我们可用不同的术语来表述他的身份,如被放逐者、侨民、流亡者、移民、避难者或无家可归者。”
正如乔西所言:“奈保尔的印度书写本质上是对自己的一种身份追问。”奈保尔关于自己的身份探索主要通过《黑暗》来表现,后持续到《百万》中。奈保尔接受诺贝尔文学奖发表演讲时说:“我去了印度一年,那是我祖先的国度。那次旅行将我的生命分成两半。”这里的“两半”指他心目中印度记忆与印度体验的极不协调,指他的文化身份追问遇到了严峻挑战,一种“分裂的意识”由此产生。背负文化疏离心态的痛苦无奈,奈保尔对近在咫尺却又仿佛远在天涯的印度无法达成文化身份认同。奈保尔的确踏上了去印度的文化寻根之旅,但在他眼里,印度人全都是陌生人,就连印度的自然景观也过于苍凉杂乱,让他感觉格格不入。他在《黑暗》中叹息道:“身在印度,我总觉得自己是一个异乡人,一个过客。”奈保尔无法完成印度文化身份的建构,也就不能与娘家的印度人达成亲戚认同。第一次到印度的寻根之旅也就草草收场。有人评价说:“虽然奈保尔对印度的了解不可谓不多,但他仍然未能成功。对他而言,印度仍然是一个黑暗地带,不管他如何声称自己身在其中,他仍是一个局外人(outsider)。”第二次印度之行还是没有解开奈保尔心中对于印度文明的“陌生”情结:“印度,这个我1962年第一次探访的国度,对我来说是一块十分陌生的土地。”纳拉辛哈说,奈保尔所经历的是“无家无根者在无国无宗教也无赖以生息的价值信仰的情况下的痛苦体验”。这很准确地点出了奈保尔的悲剧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