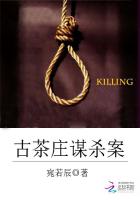回到东宫,文叔归跪在了面色发白的司马炽面前,伏身道:“小人罪该万死!”司马炽缓缓转头看向文叔归,“与你何关,是我没有顾虑周全。”文叔归摇头,“若非小人怂恿,殿下便不会急着赶去城门处宣令,若非如此,方才那些百姓……”文叔归哽咽道:“就不会有事了。”
司马炽低声一叹,“你何必如此,怪只怪我这个皇太弟无用,连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都护不住……”“殿下!”荀德跪下道:“如今殿下还在想着方才的百姓,可殿下就要大祸临头了呀!此事,河间王必然已经知悉,殿下性命堪忧啊!”
闻言,文叔归直起身向司马炽一揖,“殿下,此事皆由小人而起,小人这便去河间王面前请罪。”“不可!”司马炽令人拦下了起身就要往外冲的文叔归,道:“叔归,先不说此事与你有何干系,便是看在仲希与你这段日子忧国忧民的份上,我又岂能让你有事?”
“你们谁都不会有事?”门外忽然传来司马衷的声音,屋内众人立即向进殿的司马衷行礼。司马衷来到司马炽身旁,拍了拍他的肩膀,“丰度,这些日子难为你了。”司马衷转而坐下一叹,“只是,任你做再多的努力也是无用,司马越的前将已经打到了附近,司马颙与司马颖正准备南逃。”
闻言,司马炽诧异地看向司马衷,“他们怎么可以!既然要逃了,为何还不放那些百姓出城?方才还……”司马衷道:“这个时候一旦放百姓出城,长安城就乱了,他们再想率部而逃,就难了。”“畜牲!”司马炽怒道:“百年之后,他们怎么有颜面去面对高祖!”
司马衷道:“这也未必就是司马颙的意思,你也不是不知道他那犹豫的性子,很多时候都是受了底下人的糊弄。识人不明,断事不清,否则,就不会一次又一次错失良机。咱们眼下,什么也做不了,只有待他们离开后,咱们再作打算。”司马炽道:“可待他们出城,只怕司马越的人就该攻进城了。”司马衷一叹,“我当尽我最后的能力,若能护得一城百姓安全,自然最好,若不能,也希望能令他们少添些杀戮。”
司马衷转而看向默然而立的文叔归,“叔归,南城门的事儿我已经听说了,也是我不该写下那道手书,你们都不要太怪责自己了。况且,你既然选择了留下,就该接受这一切,看开些,否则,我倒不如让人送你早早出城。”文叔归跪下摇头,“谢陛下恩恤,小人想留下来。”
司马炽将殿内之人遣了出去,这才看向司马衷道:“陛下,都记起来了?究竟是谁……”司马衷打断了司马炽的话,语重心长地道:“此乃天命,当年曹魏代汉,是汉数已尽,而我司马晋代曹魏,其数尚未尽,武帝开国之君一代雄主,此劫只能应在我身。但我司马气数也尚未尽,社稷之事,或许还会另有转机,但也不过狗延残喘而已。”
司马炽又看向文叔归,“你选择留下,仲希选择离开,但不代表她没有争天命,她只是在另一种方式争罢了。我想,你不希望看到她有事,同样,她也不希望你有事,便是为了她,你也多多周全自身,不要争一时意气。我……欠弘度太多,也欠她太多。”司马衷起身道:“这几日就呆在宫里,哪儿也不要去了。”
火光漫天,烟尘四起,不堪入目的街道伏尸遍地。一行盔甲兵士缓缓从街尾走来,为首一人甲胄鲜明,仪容威严,像是一位将军。不一会儿,一行停下了脚步,从众人身后追上来一人,那人在那将军面前停下,躬身低头似在说着什么。忽然,那说话的人拔出匕首便刺向了那将军,将军似早有防备,迅速向后退去,随即行刺的人便被兵士重重包围……
“叔归!”出了一身冷汗的吴仲希坐起了身,外面的天色已经微亮。“怎么了,仲希?”甘棠冲了进来,点燃了烛火,待看清吴仲希的脸色时,不禁上前温声道:“怎么了?又发噩梦了?”吴仲希闭了闭眼睛,再睁开时,眼里已是一片清明,“长安要出事了。”
甘棠拿了帕子替吴仲希拭掉冷汗,道:“北方战事已起,无非是你生我亡,受苦的还是无辜的百姓。仲希,你是不是有牵挂的人在长安?”吴仲希点头,甘棠道:“那当日你从长安出来,为何不带着他一块儿出来?”吴仲希道:“他有他的想法,我不想阻止他,但我真的害怕他会冲动行事。”
甘棠道:“若这是他的命数,你多想无益,若他命不该绝,怎么也不会有事儿。”吴仲希轻轻一笑,“棠姨,我听着你这安慰,更想哭了。”甘棠也笑了起来,“所以,你不要再胡思乱想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数,你只要尽力了,就够了。”吴仲希颔首。
很快,司马越前将祈弘率人打到了城下,而司马顒与司马颖早已率部往南逃去,长安可谓空虚无防。祈弘来到城下,却见城门大开,一行人正立在城门外,似是迎接的架势。祈弘近前才看清为首之人是皇太弟司马炽,于是下了马上前行礼。司马炽一揖道:“祈将军远师劳顿,陛下已在宫中设下肴馔,还请祈将军一往。”
祈弘向上一揖,“微臣敬谢陛下!”司马炽看了一眼祈弘身后众人道:“只不过,河间王与成都王皆已出城,如今城中尽是手无寸铁的普通百姓,还请祈将军务必约束众军士,不要妄伤无辜,今晚庆功宴,陛下自有论赏。”祈弘再一次谢过恩,正想说什么,众人就听闻城内喧嚣声突起,司马炽脸色一变,很快就有人匆匆来报,“皇太弟殿下!他们攻进城了,而且……”那人看了一眼祈弘,“见人就抢杀!”
司马炽不可置信地看向祈弘,“祈将军,你……”祈弘连忙道:“启禀殿下,此事,微臣实在不知!”司马炽一甩袖,转身上马,飞奔着入了城,一众随行策马跟上。祈弘吩咐了一声保护皇太弟,便也率着人进了城。待看到眼前的屠戮,司马炽悲愤地看向祈弘,“祈将军,天子尚在城中,你就要屠城吗?”
“微臣不敢!”祈弘看了一眼眼前的景象,随即一叹道:“殿下有所不知,微臣所领兵马分为好几部,除了本部兵马,其他几部兵马皆不听令于微臣,微臣这便去见他们的首领!”说完,祈弘打马上前,一众兵马随在其后。城中很快火光漫天,惨叫声延街,喧嚣之音不断,直到傍晚,城中才渐渐安静下来。
司马颙与司马颖走后,司马衷与司马炽便立即吩咐人携着司马衷的手令在各城门处迎候东海王的人马,为的就是阻止屠戮。甚至连司马炽都不顾安危,亲自来到城门处迎候,然而这场屠戮还是发生了,守在其他城门处的官吏皆被斩杀,他们根本来不及阻止。
街道上充斥着悲号声与嬉笑声,文叔归只觉十分刺耳。司马衷看着无言的司马炽还有文叔归道:“东海王为了赢这场仗,不惜招揽各路人马,可惜洛阳财物两年前早已被张方的人马劫掠,如今东海王的人进了长安,自然不会放过掠夺财物的机会。我们虽百般想阻止,但人算不如天算,人心也算不准人心。”司马衷一叹,“这是天意。”
文叔归腾地站起了身,向司马衷与司马炽一揖,“小人先行告退。”文叔归退了出去,司马衷看向了司马炽,“你若想离开,我会为你安排。现在退出,还来得及。”司马炽垂首,良久,摇了摇头,“臣弟不会离开。”
文叔归只觉心中憋着一团怒火,正焦燥间,突然看见前方远远地走来了一行人。文叔归目光一闪,突然避进了旁边的门墙旁,他缓缓拔出腰间匕首,耳听脚步声越来越近,正想冲出去。忽觉一道奇大的力将他迅速拖入了旁边的一间小屋后。
文叔归诧异转身,随即低声惊呼,“踏月?”踏月比了个噤声的手势,然后两人来到一僻静处,踏月才道:“你呀,你想做什么?难道要杀了那祈弘不成?”文叔归道:“他是罪魁祸首,那些人胡作非为,随意屠戮百姓,他却说他不知道,我不相信!”
踏月摇头道:“果然仲希担心地没有错,就你这性子,没惹出件惊天动地的事出来就奇怪了。”仲希?文叔归看向了踏月,“仲希还在长安?”“当然不在。”踏月道:“是仲希担心你冲动行事,所以要我偷偷回长安,暗中盯着你的举动。这不,我方才才走开一会儿的功夫,你差点就惹出了乱子。”
文叔归道:“你有法力,为何不阻止那帮人?”踏月道:“文叔归,你有完没完?我好心来帮你,你却还来指摘我?你以为我没出手?但我再有法力,也架不住他们人多气势凶啊!你看我这瞬间移动的本事,也不过十几丈而已,再多带一个人的话就更吃力。况且,满城都是如此,我往哪里带啊!”踏月气得转过了身。
文叔归冷静下来,低声道:“报歉,方才是我太激动了。”“你知道就好。”踏月转身道:“看在仲希的面子上,我不与你计较。但你给我听清楚了,你既练了道法,就绝不可以妄动杀念。更何况那个祈弘,若不是有他在征西府外头护着,这征西府早被扫干净了。到时陛下性命不保,你看这天下会不会更乱!死的人会不会更多!”
见文叔归不作声了,踏月放缓了声音,“叔归,离开长安吧,仲希说了,晋国在北边的江山很快就要不保了。这些日子,你不也在试图改变天命吗?结果呢?越改越糟!仲希她不是绝情,而是她早已经知道了事情会是这样,她不忍亲眼看着罢了。其实……”踏月道:“若论身份,仲希的悲痛何尝比你少半分?”“仲希她……现在何处?”“青城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