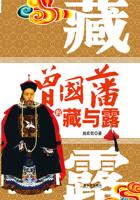只可惜,正如我们一开始就指出过的,在真实的历史语境中,从来是落子无悔、驷马难追的,就算本人乃是那话语的发明者,后来如果看到势头不对,也只剩下徒唤“不幸风会已成……”的份儿了!
由此就不难推想,越是到了暮年阶段,如果让这福建三杰凑到一起,辜鸿铭就越可能恶狠狠地那样讲,而严复也就越会自知理亏无言以对。无论如何,中国当时那台热闹的大戏,总是有严复早年的推波助澜在,而且也正因此,在严复和辜鸿铭的社会地位之间,才形成了热闹与冷寂的强烈对比。既然如此,逐渐沦入穷困潦倒的一方,当然有理由口出怨言,——我们应当基于这种同情,来宽容辜鸿铭的出言之刻毒,更何况在他刻毒的戏言背后,还不乏一针见血的洞见。
还可以接着再往下推想,在辜鸿铭对严复的痛斥背后,又埋伏着这样的潜台词:唯我辜某人才真正了解西方!这让我们醒悟到,就言说的途径和对象而言,严复和辜鸿铭两人的文化言说,原本就有难度上的不同,因为他们一个是用外文说话,一个是用国文说话。——可让人无奈的是,不用母语写作的人,在本土当然就少受关注,而把风头留给了别人。更何况,正所谓“画鬼容易画人难”:他们一个专拿中国向外边说,说的是国人熟悉的事,而且必然要有所简化,由此一旦说得有点走样,肯定很容易被国人看出来;另一个则专拿国外朝国内说,说的是国人陌生的事,当然也造成了很多简单化,不过就算问题已是山积在哪里,一下子也很难被看出来。
正因此,对比着严复和辜鸿铭的文化言说,更有必要再去重温一位行家在当年发出的知言:
溯自吾国知道西洋留学生以来,留学生之能究心西洋文学哲学而探明西洋思想精神者盖鲜。严几道(复)晚年议论,颇多透辟精深之见解,然此实得自中国旧籍,而非得自西洋。严氏之于西洋思想,仅知旧世纪及19世纪之功利主义及进化论天演论。其所介绍传译者,为孟德斯鸠、斯密亚丹、约翰弥勒、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等。此非西洋思想精神最精要之部分,不待详说。而其对于吾国之影响如何,亦不难判定。若辜鸿铭氏则有进于是。辜氏身受英国之教育较为深彻长久,其所精心研读之作者,为英国之卡莱尔、安诺德、罗斯金以及美国之爱玛生等。故其思想出严氏翻译西籍时之上。由吾人观之,辜氏一生之根本主张及态度,实得之于此诸家之著作,而非得直接之于中国经史旧籍。其普崇儒家,提倡中国之礼教道德精神,亦缘一己之思想见解确立之后,返而求之中国学术文明,见此中有与卡莱尔、安诺德、罗斯金、爱玛生之说相类似者,不禁爱不忍释,于是钻研之,启发之,孜孜焉,举此中国固有之宝藏,以炫示西人。此其中又以国家主义(爱国思想)为之动机。(吴宓:《悼辜鸿铭先生》,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至此我们才真的大彻大悟:原来这两个人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学器物的、一个学文化的。也就是说,尽管严复本人——主要是在归国以后——确实在西学方面很下过工夫,然而这位所谓“近代西学第一人”,在文化观念上却只属于业余客串;而相形之下,倒是那位曾被极度丑化的辜鸿铭,曾经学过更加专深的文科学术,还是英国大思想家卡莱尔的正牌弟子!由此也就可知,在任何的一种文化历史中,“倾听”二字都是一个重要的关键词,因为对于不打算或者来不及倾听的耳朵来说,再正确的言说也根本就不存在。
如果此刻再来回顾老年严复充满自疚的书简——鄙人早习旁行,晚闻至道。旧所纂箸,不皆折中。睹兹风波方深悔惧,而公等猥以输进哲理,启发人文目之,盖其过矣。(《与<;宗圣汇志>;杂志社书》,《<;严复集>;补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第309页)
那么,即使说他到后头有点儿倒向了辜鸿铭,恐怕也并不为过吧?
十二、文化之合题
正如上文所说,其实包括我自己在内,以往都未能从悲剧的意义上去理解辜鸿铭,而只把他曲解成了一个喜剧人物。而现在,人们的文化心态已经平复了不少,已经可以平心而论严复的晚年,不再把它看成单纯的掉队和落伍,而把它看作自赎与回归了;那么与此同时,当然也应该可以平心而论辜鸿铭了,而不再只是说人家奇怪,倒看出真正奇怪的,反而是那些看不懂他的人。——基于这样的出发点,再来回顾对其“怪诞”的种种判定,就显得更加反讽和吊诡了:在“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时候,其实所谓“正常”本身,反而更有些荒诞的意味呢!
归根结底,究竟应当怎样去认识他们共同从事的跨文化言说呢?——在我看来,这个有趣的案例再清晰不过地表明:在人类文化的交融进程中,正是对话性本身,才构成了自我性的一个重要部分;也只有在持续的、深入的和激越的对话中,很多潜藏的自我才能得到挖掘,很多无形的自我才能得到型塑。此外,激烈的和相争不下的跨文化争辩,虽然难免带来视线的变形,从而往往会造成视而不见,造成对于心智的遮蔽,但与此同时,它也同样会带来眼界的洞开,使幽深的问题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哪怕只是暴露给了一个“片面深刻”的角度。——真的,即使只是为了在争论中占上风,也往往能调动主观能动性,于无意间道出很多真理,有时候简直不假思索就话到嘴边了!
接下来,正由于严复和辜鸿铭的文化言说,都是相对于和受限于某种特定的话语场,所以尽管严复到晚年深有所悔,并给家人留下了这样的遗嘱:“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但我们仍然不能简单地说,在他们两人中间,哪一个就绝对正确,而哪一个就绝对错误。——唯一能咬定的是,谁要是无条件地倒向了他们中间的一极,而去湮灭了另一极,他这么做肯定是不对!
正因为这样,我们当然不会一俟可以平心而论辜鸿铭了,就非要为他的每一个具体论点去大肆辩护。比如,我们仍要记取林语堂对他的下述批评——夫以得化民,以政教民,孔道理论上何尝不动听?西洋法律观念之呆板及武力主义之横行,专恃法律军警以言治,何尝无缺憾?然中国无法治,人治之弊,辜不言。中国虽言好铁不打钉,而盗贼横行,丘八抢城,奸淫妇女,辜亦不言。《春秋大义》诚一篇大好文章,向白人宣孔教,白人或者过五百年后亦可受益,而谓虽过不需法治,不需军警,未免掩耳盗铃。(林语堂:《辜鸿铭》,载《林语堂集》,花城出版社2007年版,第218页)
真正重要的是,到了当今这个全球化时代,借助于对两位前贤的阅读,我们更应当时刻念想着,其实跨文化的对话性,更应宽广地收纳到我们自己心里,以便让这堵胸膛更加开阔与包容,也让各种曾被极化处理的人类认识,都逐渐走向它们在精神上的合题。——也就是说,在超越与护佑之间、改革与保守之间,应当注意保持某种张力;在批评自己和批评别人之间、自我认同与自我超度之间,应当注意保持某种平衡。我在刚刚发表的一番谈话中,又把这个文化使命大胆描绘为重新激活的、建立在“中-希文明”之间的“中体西用”:在如此复杂和空前严峻的挑战下,仅仅去调动中学或西学资源,都已经不足以救度我们,所以真正的转机毋宁在于文明对话,并且首先在于中西之间的文化间性。让我把这意思说得更具体一些。要知道,寻常所谓的“西方文明”,其本身也是多元的甚至分裂的,而真正能跟中国文明既相通又互补的,则首推所谓“两希文明”中的希腊文明。跟中国文明的基因一样,这种文明的基因同样既是理性的、怀疑的,又是现实的、审美的,还是人间的、乐观的;但跟中国文明不同,由于偶然发生的历史成因,它却发展出了科学文化与民主制度,而这两者都被五四先辈总结为现代文明的基本因子。在这个基础上,晚近以来我一直在思索着,应当重新阐释和激活“中体西用”之说。试想,如果我们未来的社会共同体,能够建立在“中-希文明”的文化间性之上,既保有丰厚的传统文化资源,足以修持个人的道德心性,又能借鉴从希腊舶来的民主体制,来调节这些个人之间的关系,那么将会是一幅多么和谐又活跃的图景!进而,如果将来培养出来的年轻人,都能既有“慎独”的道德操守,又有“仁者爱人”的相互关系,还更能以喜悦静观的好奇心,去探究自然物理的奥秘,那将会是一种多么成功的教育体制!如此一来,我们就将在个人与自我、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个人与自然诸方面,全方位地进入良性规范,——这将是一个多么健康的、生机勃勃的文明!(刘东:《关于“当代精神困境”的答问》)
这种再造文明的努力,当然也是在继承着辜鸿铭帮助建立的话语传统:
我们坐着谈论新式的信条和古老的学说,还有那现代的主义,从古至今滔滔不绝地谈个不停。
你渴望的是最优和最优者的组合,要打破那东方与西方的畛域。
(辜鸿铭:《怀念赫尔曼·布德勒,已故德国驻广州领事》)
惟其如此,就本文的论域而言,我们才能借助于严复与辜鸿铭的写作,来窥探和体会在激烈的文化冲突中,人们是如何发挥出选择的主动性,来建构出自我认同和文化论说。——也唯其如此,在不断走向文化基因之合题的过程中,中国人的自我认同才会不断向前迁移,而我们身上的中国性才是灵动的和充满生机的,才会印满我们的持续努力。
(本文为作者在浙江大学“浙大东方论坛”上的讲稿,题名有改动)
[作者简介]刘东(1955-),男,1981年毕业于南大学哲学系,1985年考入中国社科院,师从著名思想家李泽厚,2000年至2009年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2009年7月到清华大学工作,现任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国学研究院副院长等职。
我曾于1982-1983年任教于浙江大学,时沈善洪先生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常有请益,遂成忘年交。今值沈先生八十寿庆,谨以本文致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