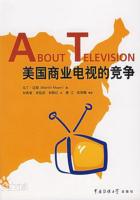在海拔2260米的高度,我看到了耸立于云层之上的秦岭主峰的一角。它凝结着汉朝的坚冰和唐代的积雪。甚至凝结着不可计数的遥遥岁月的冷冷之霜。14点15分的阳光,宁静的照耀着那里的洁白境界,郁郁苍苍的群山,一律拜倒在它的脚下,我既激动似潮,又沉默如雷。
我是随我的同事到太白来旅游的,这样的活动在单位是一春一次。不过步入充满诱惑的社会之后,整整八年时间,我没有一次参加单位的活动。八年,我恐惧地发现,这是一个恰恰相当于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的过程,在这么一个过程,我确实一次都没有伴着同事玩山玩水。不是别的缘故,唯一原因是我自己缺乏旅游的心情。将自己投放山水之间,需要一种平和的态度,然而,此起彼伏的欲望,使我的浮躁盈于手脚,如果不是我久仰太白的境界,那么我仍然不会出来。我多么希望自己能单独在这里眺望秦岭之巅,但我却不能,我是一个苦苦求索的学子,我做梦都想捕捉真理之女的裙裾,可惜孩子的面包与玩具已经耗尽了我的俸禄。我不能有独行的交通工具,所以单位的汽车是我所需要搭乘的。但我的灵魂却难以从众。
太白刚刚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很是压抑,它那游动在空中的巨大的沟壑,仿佛向我逼迫。太阳已经被森林遮挡,在长长的黄昏,无数平庸的山岭包围着太白的雄姿,我什么都不能看到,我只感觉它们的阴郁,沉重与强大。不过就是因为有这些平庸的山岭为基,太白才成为主峰的。我徘徊于它的脚下,发现周围到处都是卖吃卖喝的地摊,肮脏一片。这使我忽然涌出一种鄙视自己的情绪,我感觉自己竟不如那些石头。那些流水,那些摇曳的树木,甚至不如那些随便扎根在什么缝隙的野草。它们生于自然,长于自然,永远是一副真实的自然的姿态,但人却在冠冕堂皇之中包藏着多少猥琐的心思。
暮霭降临之后,我拉开了我与太白的距离,沿着一条河谷走向远方,然后回头望着它。在狭长的一片虚空的天色之下,太白坚实而黑暗的轮廓,巍然而庞然。山下,旅馆灯火通明,我的同事正在其中快乐地下棋,跳舞,聊天。大家将投宿那里,为明天的攀登养精蓄锐。五月的风在这里仍然是寒冷的,我的目光穿过越来越浓的夜色向山顶看着,那里凝结的冰雪,既是这里寒冷的元素,又是我身旁的河流的源泉,清凉的水,潺潺地穿过河谷的白石,曲曲折折地寻找其他的河流,一起走向海洋。
太白属于盘踞在渭河与汉江之间的秦岭的顶巅。对这么崇高的主峰,生息在它的膝下的人当然是敬畏的,膜拜的。古书记录,太白是金星之精坠于秦岭的结果,祖先尊它为西方之神。我约略知道,汉时,这里就筑有敬神的祠堂,唐时,唐玄宗从这里获取了一枚福寿之符而大赦天下。特别是关中的农民,遇到干旱岁月,一定要在太白之端祈雨,那里有三个明净的水池,昼映红日,夜映白月,祈雨是非常灵验的,就连乾隆皇帝都为之感动,竟为太白封王。这样神奇的大山,当然是一个诱惑,难怪李白和苏轼都曾经攀登,并连连赞叹。
太白就是太白,在夜晚,它突然展示了自己严峻的一面。大约零时左右,一股凶猛的风将旅馆的窗帘卷起,浓重的雨气从原始森林滚滚而来,闪电,垂直于天空和地面的细长的闪电,进发着强烈的白光,它急剧地抖动着,照亮了半个宇宙,一瞬之间,覆盖着太白的绿色树木,清清楚楚地暴露在那里,我感觉闪电仿佛给它喷射了一层透明的雾气,此时此刻,森林之中的禽兽是睡着还是醒着,是惊恐地准备逃跑还是安然地立足原地,我都难以知道。巨大的响雷连续在太白周围滚动和爆炸,旅馆的门随之有了奇怪的颤音,我听见密集而急骤的雨点鞭打着窗外的世界。躺在床上,我痛苦地认为。可能明天难以攀登太白了。然而过了一会儿,雨便停息。万籁俱寂,蕴含着草味花味森林之味的清冽气息处处可闻。
早晨六点出发,自山下至山上,足足80公里,即使不到顶巅,行动也不宜迟缓。没有谁愿意拖拉,一种无形的引力牵动着所有兴奋的心。蔚蓝的天空之下,相互交错的山岭,为雨所浸,一片青葱和鲜碧,雾与云已经被洁净的空气调和了,太白庄严地坐落在那里,是如此的雄壮和如此的奇伟。
攀登太白,理想的方法应该是悠然步行,不过,要汽车送一段属于单位的规定,我是无可奈何的,不但如此,导游小姐将关于太白的粗俗故事兜售给大家,尤其使我难受。我的考虑是,在太白这样的造化面前,人最好保持沉默,保持谦虚,因为人远远渺小于自然,任何轻佻的行为,都可能减弱和隔阻它对人的启示。问题是,随着都市生活的发展,人渐渐淡漠了自然,疏远了自然。实际上人是多么需要自然的熏陶和感染。自然无疑是人最美丽的母亲和最伟岸的父亲,是人必须反复阅读的神圣经典。如果人不走进自然,体味自然,让自然的气息灌注自己,那么人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健全和真正的高尚。对于太白,我便怀着这样的感情。
在杵窝,汽车停下了,我走出它的金属之门,立即感到山的世界穿着古老的森林向我扑来,身前身后的嬉笑声音,一下消失在透明的充满鲜花和腐叶气味的空气之中。此地为孙思邈隐居之处。在唐代,他拒绝当官的邀请,无疑是他对世事洞察的结果。从杵窝向前。山路变得曲折,真正的攀登便是从这里开始的。柔和的光芒斜斜地倾泻天空,尽管太阳仍然在山的后面,但一些高耸的峭壁却涂抹了金色。旅游的人渐渐拉开了距离,捷足的当然先行,散漫的当然尾随,我瞻前顾后,发现人在坑坑凹凹的山路上断断续续。瞻前顾后不是我的性格,不过我知道自己的身前有人身后有人。我平缓地走着。山的黑色从上到下作垂直的变化,植物的种类应有尽有,只是树的叶子渐渐缩小。山有多高,鸟就有多高,那种我不认识的长着红翅红尾的鸟。总喜欢孤独地呆在水旁或石角。风铃仿佛妙语穿越着森林的古木与新苗,在空中作响。仰望悬崖,放纵着流云而紧系着飞瀑,苍黑的石缝站立着傲岸的松树,在阳光永远不能照耀的阴处,湿润的青苔依附着郁闷的石面,粗壮而纠缠在一起的藤萝追赶着硕大的树冠,花谱没有记录的紫朵与黄朵,自由地开放于河边溪旁,清纯的水滴向它们抛洒。五月的风没有一个夸张的动作。野草没有因风起伏,树枝没有因风摇摆。然而我全身心地感到风的存在。空气已经稀薄得暴露了天穹的骨髓,广阔的蔚蓝便流淌在我的周围,如果举臂抓它,那么蔚蓝将会染上我的手指。很多的山峰相继落下,很多的山峰仍在崛起,浩然太白是一个山峰摞着一个山峰的立体,攀登它,除了向前就是向前,它的顶巅在海拔3767米的高度。
登上红桦坪。二十公里开阔的峡谷倏地闪开,锋利的风从天而降,那天仿佛是用石器打磨了一样光洁匀称,我身旁唯一深情的女士的裙裾在风中拂动,她忧郁的眼睛向着远方,而人则站在凸出河流的一块石头上指指点点。明亮的碧空之下,稠密的原始森林承受着阳光的照耀表现得静静悄悄,由于温暖仍然徘徊在海拔一千米以下的地带,这里的树林显然都是阴郁的干枯的。那光秃秃赤裸裸的枝杆,像僵硬的牛筋和皮鞭一样伸向天空,染了绿带了青的只有稀疏的几点松杉。在灰暗的森林之中,一瞬之间,我感觉这森林像冬天贫穷的乡村一群农民穿着破烂的棉衣站在那里,其中,能够反射尊贵色泽的树是红桦,它高大的树身,疏朗的树冠,仿佛是红铜铸造的一样坚实而傲岸。天光的每一映照和山风的每一触动,红桦都要在巨大的峡谷发出回声,仅仅它的这种回声就使人惊诧。到处都是红桦,它成了这个高度的显赫的植物,其他所有的杂木都退缩在它粗壮挺立的躯干之后。在这里,我看到了秦岭主峰太白的一角,它远远从两个铅色的山头之间闪现。豁然开朗的沟壑恭敬地把它暴露在外,蔚蓝的天空作了它永恒的背景,那是真正的蔚蓝,没有一点杂色,水一样柔和而透明的阳光,非常轻盈地照耀着它。在只有鹰可以立足的倾斜的山岩,凝结着高寒之地和悠久之年的皑皑冰雪,圣洁的主峰望之皓然。夏末秋初之际,朗朗晴日,站在关中平原的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看到太白的反照。一个道士告诉我:在主峰附近,生长着各种各样的杜鹃,其中最大的一片足有一千余亩,数峰嫣红,十分壮观。
根据我的力气和蛮劲,我完全可以攀上太白的顶点。不过我不想向上了。我感觉它高尚的如此孤独而美的境界,唯有伟大的灵魂的人才能够接近它,像我这样渺小的俗人,只配站在它的脚下仰望,如果我不断地努力,不断地努力,那么也许会有向它靠拢的机会,然而现在不行,现在不行。倘若我冒昧地找到了它的顶点,那以除了证明我的浅薄,只能显出我的丑陋。不过我在空旷的红桦坪看到了太白的一角,山冈上的风卷起祥和的阳光吹拂我的头发,我伫立在海拔2260米的高度久久仰望着,尽管十分之九的太白仍为其他山峰而遮掩,不过我依然情不自禁地呐喊起来。我感觉,一个腐朽的躯壳痛苦地震裂着,随之,我的灵魂开始了新的升华。
此时此刻,太白威严地俯视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