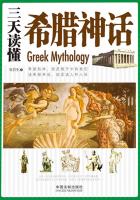梁实秋是文学批评家,但是他对文学的看法与一般的批评家从美学出发有所不同,而这种不同又与白璧德的影响有关。白璧德将文学批评与伦理学结合起来,将卢梭作为主要攻击的敌人,以防止文明的解体。梁实秋曾将白璧德的学说称之为人本主义,其实人本主义在近代就有不同的含义。对于西方近代之后愈演愈烈的科学主义乃至工具主义,一种来自情感上的反动就是反文明而回归自然,从卢梭、尼采到伯格森,随着工具理性对人的惨烈的压迫,这种反理性、反文明而回归自然的倾向构成了现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这种文化思潮以对物质文明与科学技术的反抗以及对人的注重,也曾被人称做人学思潮或人本主义。但是,白璧德的人本主义显然是作为这种文化思潮的反动而出现的。白璧德既反对科学主义与工具理性对人的价值的贬低,对人的生存的压迫,又激烈地反对自卢梭开其端的浪漫主义文化思潮。在白璧德看来,科学主义与工具理性是将人当作动物一样进行研究与观照,而浪漫主义文化思潮则是像毫无束缚的野兽一样对科学主义与工具理性进行反抗——也许白璧德会认同罗素对浪漫主义者的描绘:典型的浪漫派要把关押老虎的笼子打开,来欣赏老虎吃绵羊的那壮丽的一跃。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白璧德将与科学主义、工具理性更为接近的现实主义、自然主义也划入他所批判的浪漫主义的范畴中,认为它们都统一于没有凸显人与自然差异的自然主义中。白璧德一方面反对科学主义与工具理性对人的尊严的侵害,要求以人为本,另一方面眼看基督教无可挽回的衰落,又试图以希腊的古典理性精神来节制人的情欲,以拯救文明。梁实秋既反对文学批评的科学主义,又反对文学批评的印象主义,遵循的就是白璧德的批评路线。
梁实秋认为文学批评与哲学是最近的,“文学批评的出发点是人对人生的态度,这是一个哲学的问题。自亚里士多德以至于今日,文学批评的发展的痕迹与哲学如出一辙,其运动之趋向,与时代之划分几乎完全吻合。”在古代的时候,批评家就是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是古典主义最重要的批评家,也是最著名的哲学家。只是随着知识越来越分科发展,文学批评才与哲学分家而另立门户。在哲学中,与文学批评最近的是美学与伦理学,而梁实秋批评的特色就在于,他认为就文学批评与哲学的关系而言,伦理学与文学批评的关系比美学更亲近也更重要。梁实秋说:“一个艺术学家要分析‘快乐’的内容。区别‘快乐’的种类,但在文学批评家看来最重要的问题乃是‘文学应该不应该以快乐为最终目的’。这‘应该’两个字,是艺术学所不过问,而是伦理学的中心问题。假如我们以‘生活的批评’为文学的定义,那么文学批评实在是生活的批评的批评,而伦理学亦即人生的哲学。所以说,文学批评与哲学之关系,以对伦理学为最密切。”
当朱光潜留学归国宣扬美学并以美学来解释文学问题的时候,就受到了梁实秋的批评。梁实秋争辩说,美学对于解释绘画与音乐是恰当的,对于解释文学问题就不恰当,因为文学必然要描绘在梁实秋看来与美无关的社会人生。梁实秋说:“把文学、图画、音乐等都认做是艺术的部门,而以美学做为一切艺术的哲学,把美学当做一把钥匙,用它可以打开各种艺术的门”,这仅仅是一种理想,而不是事实。“我们欣赏一副画,能不能与欣赏一部戏剧采同样的态度?图画的题材与戏剧的就不同,一棵松树可以画成一副图画,一枝梅花、一块石头也可以画成一副图画,而戏剧的题材就必须是一段人事。我们欣赏一副图画,看它的用笔用墨,看它的姿势气韵等等,这叫做美感经验,这牵涉不到思想与情感,可是我们欣赏一部戏剧,就不能这样的沉溺在美感经验里,我们的思想不由的要受刺激,我们的情感也不由的要受刺激。我们不由的要联想,我们不由的要以剧中内容与实际人生相印证。”也就是说,文字这种媒介与色彩、声音是不同的,在文字里感受音乐的美与绘画的美并不算尽了文字的功能,如果文字经过大作家的巧妙编排,“它能记载下作者的一段情感使读者起情感的共鸣,它能记载下人生的一段经验使读者加深对于人生的认识,它能记载下社会的段现象使读者思索那里面含蕴着的问题,总之文学借着文字能发挥它的道德的任务,但是这与美无关。”
梁实秋一直是以西方文学批评的正统自居的,在《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中他也说自己根据的是西方批评的正统,但是他将文学偏离于美学而与伦理学结亲的批评理论,却是偏离了西方自美学概念产生之后文学批评的正统。他认为欣赏一副绘画牵涉不到思想与情感,就令人不得要领。事实上,即使强调文学的道德力量与理性特征,也完全可以在美学的范围之内强调,譬如康德是在《判断力批判》而不是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分析了文学经典,并且提出了“美是道德的象征”的命题;黑格尔更是在《美学》中提出了“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的命题,而且也轻视梁实秋反对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之类的“浪漫的混乱”,而重视显现理念的并且为梁实秋所推崇的《浮士德》。梁实秋尽管误认为儒家没有文学理论,但是他将文学与伦理学合在一起,除了白璧德的影响,恐怕与儒家文学批评的影响有关。儒家以“善”释“美”,要求“尽善尽美”,强调文学的伦理教化功能,以诗“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正是梁实秋以文学与伦理学结亲的批评理论的传统文化基因。因此,梁实秋批评中国文化注重实际,他自己也没有摆脱这种注重实际的文化传统。
有趣的是,梁实秋认为文学的美就是文学的音乐性与图画性,从而将文学与音乐、绘画进行了比较。在《〈草儿〉评论》中,梁实秋就感觉到新诗缺乏音乐性,在《诗的音韵》中他进一步指出新诗比起旧诗来缺乏“音乐的美”,从而让新诗人创造新音韵。从美国留学回来后,尽管他的文学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倡导浪漫主义到反对浪漫主义,但是在寻找新诗的音乐的美这一点上却没有什么变化。他在《新诗的格调及其他》等文中认为,中国旧诗是有固定格调的,平仄也是一个大概的规律,外国诗的音节也是有固定的格调的,但是现在的新诗之最令人不满者即是读起来不顺口,缺乏音乐的美。尤其是在《文学的美》一文中,梁实秋对诗歌与音乐的关系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讨论。他说,“诗本来是和音乐有密切的关系的。‘诗三百篇孔子皆弦歌之’,汉时古诗歌谣称为乐府。自唐以后诗一方面随着音乐变迁而为词曲,一方面就宣告独立而与音乐分离。西洋文学也是有同样的经过,所谓‘抒情诗’(lyric)本是有lyre伴着歌唱的,‘史诗’(epic)、‘浪漫故事’(romance)也是由‘行吟诗人’口头传播的,戏剧的诗也是含有大量的歌舞的,直到近代(自印刷术发明之后)诗才与音乐几乎完全分开。所以大致讲来,诗最初是‘歌唱’的,随后是‘吟诵’的,到现代差不多快成为‘阅读’的了。”梁实秋不赞成对诗歌的音乐成分进行切碎式的“科学分析”:“诗里的音乐美,不分析还好,与诗的内容相配合着的时候似乎还有其价值,若单独的提出来分析,其本相是非常简陋的。”而且梁实秋也不打算过度强调诗歌的音乐美,他认为“文学里的音乐美是有限度的,因为文字根本的不是一个完美的表现音乐美的工具”,“音乐已经发展成为精妙之艺术,而文学自另有其任务”,如果硬要“欣赏音乐的美,为什么不直接了当的去听交响乐”?当然梁实秋如此立论是有针对性的,他看不惯现代派诗人对诗歌音乐性的强调,马拉美(S。Mallar me)就特别注重诗歌的音乐性,培特甚至说一切艺术到了精妙的境界都逼近音乐。梁实秋认为,“‘类型的混乱’(confusion of genres)正是近代艺术的一种不健全的趋势。”
梁实秋在《诗与图画》与《文学的美》等文中,也探讨了文学与绘画的关系。贺拉斯在《诗的艺术》中说:“ut pictura poe-sis。”(“画既如此,诗亦相同。”)这种“诗画同理”的说法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有进一步的阐发。王维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几乎是人所共知的,西方也有“字的画”的文学主张,普鲁塔克(Plutarch)说:“诗是能言的画,画是静默的诗。”梁实秋认为,“这是文学艺术的融会贯通,非大家莫办之处。实在讲,图画的素质在诗里并不能完全免除。尤其是我们中国的文字,很大的一部分,本身就有图画的意味,试读一首中国诗,在未了解诗意以前,只消看看字形,便觉有无限的趣味。”但在梁实秋看来,文学里的绘画美是有限度的。首先,诗是人类活动的模仿,人性的表现不在静止的状态而在活动的状态里,诗要模仿人性便不能不模仿人的动作——外在实际的动作与心灵情感的波动、思维活动,这样绘画又怎能经常跑到诗里呢?梁实秋说:“图画的素质在诗里的地位,应该便是自然在人生里的地位。……如其我们专肆力于风景物件之描写,不论描写得如何栩栩欲活,结果不是诗。因为诗若没有人的动作做基础,就等于一座房子没有栋梁,壁画油饰便无从而附丽。”其次,莱辛(G。E。Lessing)的《拉奥孔》就划清了诗与画的界限,一种是时间艺术,一种是空间艺术。梁实秋说:“用文字来表现‘空间的艺术’的美,那是如何的勉强?意境是稍纵即逝的,若想用文字把它固定下来,只能用极少数的文字。所以讲意境者,只能称引短诗或摘句了。”这就是说,一首诗要想表现绘画的美,那么这首诗必然是很短的,“篇幅稍微长些的作品,如其里面有一段故事,则故事是动的,是逐渐开展的,便不能仅仅表现一个静止的意境;如其里面含着一段情感的描写,则情感须附丽于动作,亦自有其开展的程序,亦便不能仅仅表现一个静止的意境。”于是只好在这些长篇作品的细部进行摘句,但是一串串“有画”的“佳句”凑合起来,未必整体上就是好作品。再次,从题材与内容上看,“在图画里,题材可以不限,一山一水一树一石,无不可以入画,只要懂得参差虚实,自然涉笔成趣。文学则不然,文学不能不讲题材的选择,不一定要选美的,一定要选有意义的,一定要与人生有关系的。”而且像《失乐园》、《浮士德》、《神曲》之类的诗歌,如果用绘画来展现,就需要画成连环画,其意义能和文字写的作品比拟吗?可以说,文学与绘画“性质不同、工具不同、内容不同,不能混淆”。但是,梁实秋的比较不是没有问题,他将西方主要是描写人的诗歌与中国主要是描绘山水自然的绘画比较,当然是这样一种结论;如果他将中国主要是描写自然的山水田园诗歌与西方主要是描绘人的绘画相比,那又会是怎么一个样子呢?他一方面认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是一种非大家莫办的化境,一方面又反对艺术类型的混淆,也是自相矛盾的。当然,梁实秋反对类型的混淆并非是针对王维,而是针对现代主义文人之“浪漫的混乱”的。他认为近代的象征主义者、克罗齐等直觉主义者都陷在这种混淆里而不能自拔,现代“新的艺术评论”就是“不肯分析的、笼统的、感情用事的鉴赏”,尤其是美国的意象派诗歌运动,主张“字的画”,以诗歌能够描绘新奇触目的图画为追求,就都是这种艺术类型之混乱的表现。但是,梁实秋没有看到,西方现代主义诗歌在某些艺术技巧方面恰恰是向中国诗歌的认同。
梁实秋还对文学与宗教、科学等人类其他表现领域进行了跨学科研究。他说:“一切艺术的起源,都和宗教仪式有密切关系。诗,无论在西洋或东洋,在最初阶段是极富宗教性的。所有男女相悦的情诗,描写风景的诗,以神话为中心的剧诗,以英雄为题材的史诗,以及涵有哲理的格言诗,这都是后期的东西。”戏剧也是如此,希腊的戏剧的发达就与宗教有关,在希腊看戏并非是去娱乐,而是参与宗教活动。后来文学开始与宗教渐渐脱离,但形式上虽能完全脱离,在精神上脱离的过程是很慢的。诗固然早已不是宗教仪式的一部分,然而宗教的观念却常常在一般诗人的心里涌现出来。在原始的社会,诗不是单人的创造,是人群之自然产物;在文明的社会,诗人便成为人群中之特殊人物。宗教在人群中的重要性虽日趋低落,而少数诗人却常常能保存一些原始人的宗教精神。最好的一个例子是,英国的华兹华斯,他一方面歌咏人生,一方面便在歌咏自然界的时候流露出泛神的思想,山谷河流都好像是有神灵寄在其间。这便可以说是宗教思想的遗留。勃雷克的有名的四行:
在一粒砂里看出世界,
在一朵野花里看见天堂。
在你手掌里握到无限,
在一小时里涵着永恒。
这不仅是疯话,这其中似乎颇有一点禅意了。丁尼生的一首小诗:
墙隙里的花,
我把你从隙里拉出,
我擎着你,连根和一切,在我手里,
小花——但是假如我能理解,
你是什么,连根和一切,一切,一切,
我便知道上帝和人是什么了。
这首小诗里涵着一点宗教观念,并且除了这一点宗教观念以外这首诗便没有一点好处,因为这首诗的音节字句都极不讲究。可是这一点宗教观念竟使这一首诗成为很流行的一篇文字了。因为这一点宗教观念从根本上说很浅显,所以一般人能理解,但由此可见宗教精神在诗中的遗留是一向不曾绝迹的了。
杜甫是一位“每饭不忘君”的儒生,但是在历尽坎坷与劫难之后,也不是没有遁入空门的念头,梁实秋的《杜甫与佛》研究的就是杜甫这一思想侧面。四十岁之前,杜甫失意落魄之时,仅仅是于道家中求安慰,而与佛无缘,即使在四十岁后受到佛家影响之后,那种“求仙隐遁的情绪,杜甫一生都多少保持着,一直到临死还有‘葛洪尸定解’的谶语”。杜甫开始接触的是南派禅守,与赞公往还后入佛渐深,所谓“老夫贪佛日,随意宿僧房”。《赠蜀僧闾丘师兄》一诗说:“漠漠世界黑,驱驱争夺繁。惟有摩尼珠,可照浊水源。”那么,杜甫是随意取典,还是真心皈依佛门?大概杜甫老年确是有意于诗酒之外钻攻禅理,《望兜率寺》中的“不复知天大,空发见佛尊”,已是极力赞叹佛法博大超过儒家了。杜甫老年,万念俱灰,求禅之旨昭然若揭。尽管杜甫心向佛门,但是对于诗、酒、妻子的留恋或无法安排,使他终究没有遁入空门而得彻底解脱。
但是,随着文明的进步,宗教在人类生活中的位置一天比一天降低。梁实秋说:“宗教原是全体人群的实际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竟逐渐变成一种生活上的装饰品,变成一种特殊的心理上的需要,变成一般无知的人的迷信行为,变成少数人的职业。”于是,诗便与宗教脱离了。“近代科学已破除了不少的迷信,亦无疑的破毁了许多宗教思想,换言之,亦摧残了不少诗的奥秘处。这是无可奈何的。……诗这样东西,原是野蛮的遗留,虽已发展成为高级艺术,而今后将不断受科学影响,其中不合科学的成分亦将无疑的被科学所摧毁。”在这里梁实秋的科学乐观主义态度定然得不到白璧德的赞同,他忘了他的白璧德老师对于科学的发展可以摧毁文明的告诫,而且他对宗教在西方文学中所占的重要位置似乎也估计不足。
梁实秋对科学精神的肯定可能与儒家文化传统中的理性态度有关,与中国没有宗教传统有关,也可能与他讨厌反科学而回归原始的现代派诗歌有关。在原始时代,诗与宗教、巫术有着密切的联系。如天旱不雨,他们不像今人那样担水掘渠,他们有巫师,有诗人,只消口中念念有词,“念动真言”,天上就会落雨的。他们相信文字是有魔力的。希腊文中的“ode”,德文中的“lied”,英文中的“lay”,都有魔术咒语的意味。拉丁文的“car mina”可作诗解,亦可作符咒解,“vates”可作魔术家解,亦可作诗人解。诗原是从原始宗教中的符咒起来的,巫师以为念动真言便可呼风唤雨,以为文字有使事物实现的魔力。等到这习惯养成之后,用文字的力量真能在想像中把所希冀的事物实现出来,这就是纯粹的诗歌了。梁实秋所讨厌的现代派诗人“就是想要回复到诗的原始状态,诗里没有用意,没有教训,没有思想”。但在梁实秋看来,这却是诗歌堕落的表现。梁实秋没有想到,当他遵循白璧德的教诲批评“浪漫的混乱”之末流现代派的时候,又在拥护为白璧德所反对的科学主义,因为在白璧德看来这二者是一丘之貉,所以白璧德将现实主义放进浪漫主义的大筐子里一并加以声讨,而梁实秋在拥护科学的旗帜下,后来顺理成章地肯定了写实主义。
关于文学与科学的关系,梁实秋有一段妙论:“科学先战胜宗教,再战胜哲学,最后和文学冲突。”文学也一样,“文学先战胜了哲学,再战胜了宗教,最后和科学冲突。”在与宗教、哲学为敌上,文学与科学曾经是同路人。但是随着文学与科学的坐大,二者也冲突起来,英国历史上阿诺德与赫胥黎(T。H。H uxley)之争,就是文学与科学之争。阿诺德承认科学的重要,以为科学可以把物质现象一项项加以分析实验,以探究真理,但是这些真理如何才可以和人生问题联系起来,这是科学家不过问的,而是文学的领地。“如人性不变,文学的魔力是不可抵抗的”,因而在并非专门领域而是面对大多数人的教育中,应该以文学为主导。赫胥黎承认文学的价值,但是却扩大科学的领地,认为对于人生问题,也须要提倡科学方法,至少在教育上科学与文学是同等的重要。梁实秋说:“在阿诺德与赫胥黎的论战里,我们可以看得出文学是取守势,想保守它从文艺复兴期以来的在教育上的领袖地位,科学是取攻势,想在教育上分一席地以与文学抗衡。这冲突究竟是教育方面以内的冲突。但到了现今,情势又加紧了一步,现阶段的冲突是暂撇开教育不谈,科学采取了猛烈的袭击,冲到文学范围以内要夺取文学的大本营。”
事实上,“从十六世纪以后,诗人与科学家的领域之间的鸿沟便愈来愈明显,诗并不是一切知识的精华了。而科学的领域愈来愈扩充,科学不仅是研究自然现象,对于人生问题也要逐渐的过问。所以诗的领域是愈来愈缩小。在十七世纪科学家如加利留如牛顿如德卡已经把诗人从宇宙问题中驱逐出去,不容诗人置喙;如今呢,科学家如Pavlov如佛洛伊德如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又把诗人从人生问题中驱逐出去,不容诗人置喙。”梁实秋特别介绍了以科学侵入文学领地的诗人与学者伊斯特曼(M。East-man),在《文学心理:科学时代的位置》一书中,伊斯特曼曾经嘲笑那些忽视科学的文学家与人文学者,认为他们之间的争吵不过是维护他们“随便乱说”的权利,维护自文艺复兴以来尊贵的地位,并且在科学时代还要人听他们“随便乱说”。他举T·S·艾略特与白璧德为例,说艾略特一会儿说要以理性控制情感,在别处却说以宗教“训练”情感,在别处又说以诗“陶冶”情感,别处又说使情感“发而为诗”,别处又说诗中“描写”情感,这是“随便乱说”的一例。白璧德在《人文主义之定义》一文中,用了十四页的篇幅也没有把人文主义的定义交代清楚,是“随便乱说”的又一例。伊斯特曼认为,科学已经说清楚的部分,便不容文学再胡说八道,如果仍然随便乱说,就不能被视为真理,而且在他看来,似乎所有的文学领域都可以享受到科学之光。
梁实秋对于科学对文学领地的入侵持一种辩证态度。他认为“科学是不断的在进步,所以向来属于宗教哲学等等的领域,渐渐被科学占领了不少,这趋势是不可抵御的。科学研究的结果,我们不能不接受。至于‘人’呢,他们身体的构造是机械的,也是物质的,所以在这方面的研究也自然属于科学”。他甚至认为阿诺德与赫胥黎的争执也是不必要的,“文学与科学应该有更密切的联合,科学家是人,所以不能不理解文学,文学家要做有知识的人,便不该不努力理解科学。文学要吸取科学的知识,科学也要‘人化’。”而且“人生问题原不是文学家所能垄断的,不过同一对象可以有多方面的处置,科学以实证的方法研究自然与社会的现象,文学以经验的想像的方法来说明人生,科学的方法没有文学的方法之优美动人,文学方法亦没有科学方法之准确精细,文学与科学是无所谓领域的冲突,因为是不在一个层境上。”就文学批评而言,“旧式批评家的思想之含糊笼统,诚是一个大病”,应该效法科学力求严密。
但是面对科学咄咄逼人的攻势,梁实秋作为受过白璧德人文主义教育的文学批评家还是难保持中立。他认为科学的作用是有限的,不能代替文学的创造:“科学的结果也许可以开辟一些新的文学的材料,也许可以令文学家对于一部分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得到较精确的认识,但如何使这些材料与认识成为文学,依然有赖于文学家之天才与技巧,非科学所得支配,科学能制造机械,尚不能制造天才,所以亦尚不能制造艺术。”科学侵入到文学领地的两大学科是“社会学”与“心理学”,而这两大学科研究文学并非没有弊病。诚然,社会学的统计方法可以使我们模糊感觉到的东西更加精细,更符合“科学”,但是这种统计学的方法并不能达到人生价值与人性深度的层面。而社会学,尤其是以人类学研究古代社会来反观现代文学的方法也是很危险的。古代原始人的生活遗迹与现存的野蛮民族的生活状态,固然是一种文化研究资料,但是现在的文明社会毕竟与之有了很大的差异,用这种研究结果来套用现今人类生活的若干问题,很难说就是科学的,其危险就像心理学中以低等动物来测量人类的心理一样。心理学也是以科学的名义侵入到文学领地的学科,“但是人的身体是否完全为一堆物质,人的心理是否亦完全受物质规律的支配?这是问题。与其科学家承认人的生活中有所谓精神现象,这种精神现象如何可以用实验科学的方法加以物质的说明?人的脑及神经系统之活动状态,是尚无法剖析实验的。白鼠的实验的结果有多少可以无疑的推论到人的心理?”这种推论不是像研究原始人来论证现代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一样危险吗?梁实秋说:“心理学如在科学的旗帜之下冲到精神现象的范围里去,它将不但不能夺得营盘,且将隐入迷阵里去。像弗洛伊德一类的学者,打着科学的名义深入人类的心灵,其片面性以及对文学价值分析的毫无帮助立刻就显现出来。可以说,心理学社会学若是科学,一踏入主观的精神的领域里去,立刻就成了假科学。”
自称科学的文学批评另外一个表现,就是强调文学受历史背景的制约与社会环境的支配。梁实秋引用了葛涅逊(Gnierson)教授的《英国文学之背景》,对这种强调进行了反驳。骚塞(R。Southey)经历了爱德华三世之法国战争的大部分,但是在他的诗里没有一点关于战事的引证,若非有别的来源,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他曾经参加战争并且被俘。“幸亏伯克的演说偶然的也成了文学,否则十八世纪的战争就没留下任何记录。”伟大诗人济慈却像伊利莎白(Elizabeth)时代的人一样,独往独来,不管当时政治的及军事的骚扰,专心地寻求美。在一番征引之后,梁实秋得出结论说,大多数作品不直接反映当时的历史状况,记录历史事件的作品也往往不是最伟大的文学,即使成为好作品被人传诵,“往往是因为技巧优美或是内容有深刻的人性的描写,而不是因为它的记载的真确。”因此,梁实秋断言,文学不像一些人想像的那样容易在科学面前败退,“文学的根基是和人性一样的稳固,文学的前途是无限量的。”
由于白璧德的将文学与伦理学的结盟,使梁实秋在进行跨学科研究的时候,尤其在分析美学与伦理学、文学与绘画、音乐时,并非没有片面性,但是总体来看,梁实秋的确是穿着西装的“孔夫子”。他以孔子的伦理理性认同了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但是却没有像新人文主义那样具有非科学的倾向,或者更确切地说,他没有像西方学者那样陷入片面的思维中,而是以中国传统思维的整体性容纳了文学与科学,这在他的跨学科研究中表现得很明显。本来,在机器杀人更为惨烈乃至使用了核武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所接受的白璧德学说应该更向反科学的倾向发展,但是他更乐于接受不排斥科学的常识。这种孔子式的常识使他并不截然排斥宗教,但是却像孔子一样“不语怪力乱神”,甚至将宗教看成是无知的迷信。因此,即使在精神很痛苦的时候,梁实秋也没有真正能够进入宗教的境界,而更近似“祭如在,祭神如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