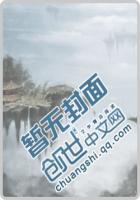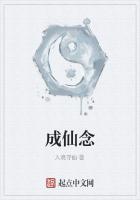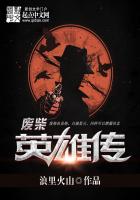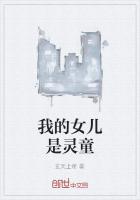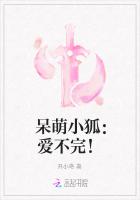在人性问题上,王夫之没有完全接受张载的说法,他认为人性是在后天的习行中逐步形成的,并提出“习与性成”说。王夫之说:“习与性成者,习成而性与成也。”(《尚书引义》卷三)同时,他又认为,人性即使形成了,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可以在日常习行中发生变化并逐渐完善的,即人性“未成可成,已成可革”
(同上),并提出性“日生则日成”的命题。王夫之的这种说法,不仅否认有先验的道德,而且强调了后天习行对人的道德形成的作用,强调人应该在实践中努力塑造自己,完善自己的人格。这是对孟子以来的先验人性论的重大突破。
受历史的局限,王夫之的道器观还存在着一些缺陷或不彻底的地方。这主要在于,王夫之所说的“道”,其内容过于宽泛,不仅包括一般的理念、原则等抽象的、观念形态的东西,也包括规律、实体的功能、属性、条理之类,这就使道器关系出现复杂的情况而使其观点不能一以贯之。此外,在社会生活领域,王夫之尚不能把道器关系作为纯粹哲学范畴的关系贯彻到底。在认识论上,他认为君子应该“尽器”。但在道德生活中和价值追求上,却又错误地认为追求“器”只是“小人”之事,而君子应该求“道”,主张“君子不器”。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王夫之的思想尚未脱离宋明理学的窠臼。
二、黄宗羲、顾炎武、颜元的实学思想
在明清之际,黄宗羲是对君主专制作了深入批判而又独树一帜的一位思想家。在君主专制还在强化的情况下,他公然指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明夷待访录·原君》),并把“君”视为“寇仇”、“独夫”,还说“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同上),其批判锋芒已指向“君臣之义”这一封建统治最本质的观念。他主张必须改变君主独揽天下大权的情况,认为“君为主,天下为客”的情况应该颠倒过来,而“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同上)。在这一思想基础上,黄宗羲还提出以“学校”来发挥议政的作用和限制君权的主张,“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公其非、是于学校”(《明夷待访录·学校》)。这些都具有早期启蒙的意义。
在哲学上,黄宗羲反对程朱理学,并对他们所宣扬的“理先气后”、理本气本的观点作了有力的批判。他十分赞赏罗钦顺关于“理在气中”、“气外无理”的说法,认为宇宙间存在的只有“气”,“离气无所为理”(《蕺山学案》,《明儒学案》卷六二)。不过,黄宗羲虽然批判了程朱,但又受到陆王心学的影响,他夸大“心”
的作用,把“心”说成是统摄天地万物的东西,认为“盈天地间皆心也”(《明儒学案·自序》),“人心之理即天地万物之理”(《江右王门学案七》,《明儒学案》卷二二),这和他的“盈天地间皆气也”以及“离气无所为理”的说法很不一贯。其实,黄宗羲所说的“心”不同于王阳明心学的本体之“心”,而是指“气之灵处”,他说:“气未有不灵者,气之行处皆是心。”(《河东学案上》,《明儒学案》卷七)这种即气即心、视物质和精神为一体的说法显然具有泛神论的特征。此外,黄宗羲还赞成刘宗周的“器在斯道在,离器而道不可见”(《南雷文定·先师蕺山先生文集序》)的道器观。也正是基于这种思想基调,他对道学家不切世务、空谈性理的浮虚风气深恶痛绝,指斥“其所读之书,不过经生之章句;其所穷之理,不过字义之从违”(《南雷文定·留别海昌同学序》)。总体上说,他的思想是与程朱理学相对立的。
顾炎武被清人推为“开国儒宗”,由他而开出有清一代的考据学风。他对理学中心学一派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而“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与施愚山书》,《亭林文集》卷三)。现在的“理学”尽讲些“明心见性”等空虚无用之语,而不留心经世之学。他认为真正的“圣人之道”应该是“下学上达”,“其用之身,在出处、辞受、取与,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法,其所著之书,皆以为拨乱反正,移风易俗,以驯致乎治平之用,而无益者不谈”
(《答友人论学书》,《亭林文集·补遗》)。故他指斥心学都是“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日知录》卷九),完全流于清谈。他尝辨“亡国”与“亡天下”,说:“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日知录》卷一三)他多次谈及清谈误国的道理,并指出“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只是表现形式有所不同,“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日知录》卷九)。由此,顾炎武主张要以经世致用的“实学”,代替空谈心性之理学(心学),倡导实事求是、实事实功。由于顾炎武视经学为正统,所以他沿着明代“兴复古学”的一些学者如焦、陈第、钱谦益等人的足迹,“治经复汉”,致力于复兴经学的努力,开出了一代新风。
在宇宙观上,顾炎武受张载思想的影响,主张气一元论,提出“盈天地之间者气也”的命题,并主张“非器则道无所寓”(《日知录》卷一),认为道在器中,道依乎器。同时,他也强调学习与道德修养的重要性,说“圣人之道”的核心就是“博学于文”和“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他特别强调,如果“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如果是一个“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的人,这样就去圣“弥远”了(见《与友人论学书》,《亭林文集》卷三)。
颜元(1635—1704)与他的学生李塨(1659—1733)(史称“颜李学派”)也极力批判理学家的空谈心性,提倡“实文、实体、实用,卒为天下造实绩”(《习斋年谱》)的“实学”,强调“习行”和躬行践履,其突出的贡献是重视“习行”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颜元认为理学家所谓的“致知”,“不过读书讲问思辨已耳。不知致吾知者皆不在此也”(《四书正误》卷一),而关键在于实行,这就把认识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上了。由此,颜元对“格物致知”作了新的解释,认为“‘格’即手格‘猛兽之格’,手格杀之‘格’”。即“格”就是亲自去做、去实行、去践履,在“习行”上下功夫,“手格其物而后知至”(同上)。显然,他强调通过习行来认识事物的规律、道理,说明颜元很重视人的感性经验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不过。颜元有忽视理性思维的倾向,表现出一定的经验主义的特征。其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他所著的《四存编》(即《存性》、《存学》、《存治》、《存人》)一书中。颜元的学生李塨也强烈批评了理学的空谈心性,提倡“实事”、“实学”,主张学以致用,如他批评理学家“纸上的阅历多,则世事阅历少;笔墨之精神多,则经济之精神少”,认为“家用之亡,此其志也”(《恕谷年谱》)。
在哲学上,颜元提出了新的“性理”观。他反对理学家以“气”为恶,以性或理为善的看法,认为“若谓气恶,则理亦恶;若谓理善,则气亦善”。就是说,如果没有气质,理就无所依存。他强调理与气、性与气的统一,说:“盖气即理之气,理即气之理”;“非气质无以为性,非气质无以见性”(《驳气质性恶》,《存性编》卷一)。可见颜元不承认有先天的“理纯一善”的本性。这一思想是很独特的。
三、戴震的哲学思想
戴震(1723~1777)虽然生活在清代的全盛时期(乾隆时期),但中国古代哲学却已到了强弩之末。此时较有哲学思想的学者,以戴震为代表。戴震批判了理学家极力宣扬的理欲对立观,强调理存乎欲,已表现出某种要求个性解放的倾向;他继承并发展了张载以来的气一元论,并对理气、道器关系作了富有特色的说明;他在对“知”的论述方面,许多见解也超过了前人;他提出的“分理”思想已表现出向近代思维方式推进的新动向。所以,戴震是中国古代哲学向近代哲学转化中的一位重要思想家。
戴震的哲学思想主要有:
1.以“理存乎欲”的理欲统一观批判了理学家“存天理,灭人欲”的虚伪说教
戴震依据自然人性论,肯定“人生而后有欲、有情、有知。三者,血气心知之自然也”(《孟子字义疏证》卷下,以下称《疏证》)。认为人有生命,就自然会有各种求生存的欲望,人性的内容就是人的“血气心知”所自然具有的欲、情、知。
正常的情欲在戴震看来是无可非议的,是符合“天理”的,他说:“欲,其物;理,其则也”,“人伦日用,其物也;曰仁,曰义,曰礼,其则也”(《疏证》卷下)。“物”就是人伦日用,即包括饮食男女之类的人之欲;“则”就是仁义礼之类社会的道德规范。在理与欲的关系上,他提出“理者,存乎欲者也”(《疏证》卷上),指出“有欲而后有为,有为而归于至当不可易之谓理。无欲无为,又焉有理?”(《疏证》卷下)就是说,“理”不在“欲”之外,就在“欲”之中,是“欲”的“至当不可易”之规则。
从理欲统一观出发,戴震尖锐地批判了理学家宣扬的“存天理、灭人欲”的说教,指出程朱的“理欲之辨,适成忍而残杀之具”(《疏证》卷下),并揭露说,在理学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贵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还说“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疏证》卷上)他认为,理学家所鼓吹的“天理”实际上成了尊者、长者、贵者责备、压制、奴役卑者、幼者、贱者的工具;人们正常的生存要求被说成“人欲”而加以遏制,“理”成了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故戴震痛切地控诉说:“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与某书》)这是程朱理学在古代社会所受到的最为严厉的批判。同时,他的“理存乎欲”的理欲统一观,也可视为“指向近代自然人性论解放思潮的先驱”。
2.“气化为道”与“分理”思想
戴震继承并发挥了张载、王夫之的气一元论。他明确把“道”(理)看成是气化运动、万物生生不息的过程及其规律。他说:“道犹行也。气化流行,生生不息,是故谓之道……阴阳五行,道之实体也。血气心知,性之实体也。”(《疏证》卷中)认为道就是气化流行之道,生生不息之道,阴阳之气就是道的实体,血气心知就是人性的实体。他明确说,气是道的实体,而不是如程朱所说的“道”是气的实体。理学家常利用《易传》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说法,宣扬有一个超越具体事物而独立存在的绝对的精神实体(“道”),戴震对此从语法结构和语言哲学上作了分析,他说:“形,谓已成形质。形而上,犹曰形以前;形而下,犹曰形以后。阴阳之未成形质,是谓形而上者也,非形而下明矣。”
(《疏证》卷中)在戴震看来,“形而上”与“形而下”都是一气之流行,二者的区别只是物质运动过程的不同阶段、不同形态的区别,即“未成形质”与“已成形质”,从而否认有超越形器的独立的观念性实体。也就是说,“道”存在于“气”中,“非事物之外别有理义”(《疏证》卷中)。
戴震没有一般地讲事物的规律,而是十分重视区别和认识事物的特殊规律,这集中体现在他提出的“分理”思想中。戴震认为,事物是千差万别的,并且各有自己的特殊规律,“未有生生而不条理者”(《读易系辞论性》,《戴东原集》卷八)。因此,要认识事物就要善于区别它们,他说:“理者,察之而几微必区以别之名也,是故谓之分理。在物之质,曰肌理,曰舣理,曰文理;得其分则有条而不紊,谓之条理。”(《疏证》卷上)“分理”即一事物区别它事物的特殊规律、特殊根据。又说:“分之,各有其不易之则,名曰理”,故“明理者,明其区分也”(《疏证》卷上),而“事物之理,必就事物剖析至微而后理得”(《疏证》卷下),强调应该从对个别具体事物的认识开始,才能把握事物的一般规律。由此,戴震批评了理学家的“理一分殊”说,认为它不是去引导人认识事物的特殊规律,而是热衷于追求那个抽象的、虚构的所谓“太极”之理。他说:“后儒尊大之,不徒曰‘天地、人物、事为之理’。而转其语曰‘理无不在’,以与气分本末,视之如一物然,岂理也哉?”(《绪言上》)这一批评,触及了理学家“理先气后”、“理本气末”的思想实质。戴震关于“分理”的思想在哲学史上是有贡献的。中国古代哲学思维方式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侧重于对事物的整体直观把握,注重事物的一般联系与和谐发展,追求事物的同一,这固然有其合理的方面,但是却往往忽略了对事物进行分门别类的考察和对特殊规律的研究。古代除先秦的韩非等个别哲学家曾注意到事物的特殊规律外,几乎很少有人关注,而戴震则突出地强调了这一点,这透露出中国古代哲学思维在向近代哲学转化的某种新动向。
3.“有血气斯有心知”
戴震在气一元论基础上论证了物质和精神的关系以及认识论的一些问题。
他认为人的精神是以“血气”即人的形体为物质基础的,人的认识能力、思维功能(“心知”)也是以人的感性生理器官为基础的,所谓“有血气斯有心知”就是这个意思。他说:“血气心知,性之实体也。”(《疏证》卷中)血气心知与人性本是统一的,而将二者分割开来,乃是宋儒所为。他说:“孟子矢口言之,无非血气心知之性。孟子言性,曷尝自岐为二哉!二之者,宋儒也。”(《疏证》卷中)人区别于动物的地方,在于人有“神明”(思维),但“神明”则源于人的“精爽之气”:“凡血气之属皆有精爽,而人之精爽可进于神明。”(《疏证》卷中)“精爽”指人的感觉、知觉等初级意识,他认为感性与理性的认识能力都本于人的“血气”。从认识论上说,戴震也认为人的理性认识(神明)必须以感性认识为基础。他说:“味与声色,在物不在我,接于我之血气,能辨之而悦之;其悦者,必其尤美者也;理义在事情之条分缕析,接于我之心知,能辨之而悦之;其悦者,必其至是者也。”又说:“有血气,则有心知,有心知。则学以进于神明,一本然也。”(《疏证》卷上)强调认识是主体对外物的反映,知识是后天形成的,这显然是反映论的观点。与前人比起来,戴震更多地考察了主体能力以及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对理学家把“血气”与“心知”、形与神相割裂并把“神”(理、心)说成世界本原的错误观点,从认识论角度作了有力的批判。此外,与他的“分理”思想相联系,戴震也强调认识事物必须注意对对象进行“剖析至微”的审察、分析和“思之贯通”的逻辑论证,这一点对中国古代认识论侧重于直觉思维来说也是有所突破的,即强调了逻辑认知的作用,这无疑是一大进步。同时,戴震从语言学角度去分析和评判许多哲学问题,也表现出一种古代哲学向语言哲学的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