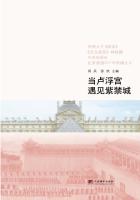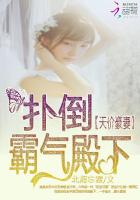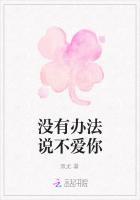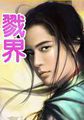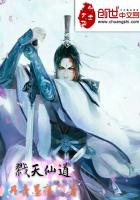托克维尔的观点亟待修正:首先,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改革危险,不改革则更危险,改革如行蜀道,不改则坐以待毙——稍有头脑的执政者,都会选择改革赌一把;其次,对于一个已经开始改革的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改革者止步或倒退的时刻,若一门心思改革,争分夺秒改革,一往无前改革,也许能跑赢革命呢——改革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政治游戏。
请允许我中断叙事,对改革与革命的辩证做三点总结:
(一)改革的阻力有多大,革命的引力就有多大;革命的压力有多大,改革的动力就有多大;
(二)成功的改革是革命的消毒剂,失败的改革是革命的催化剂;
(三)不改革,必革命;假改革,必革命;慢改革,必革命;错改革,必革命。
读晚清史可知,这三点皆不幸言中。
“皇族内阁”成立后一天,清廷颁发上谕,宣布将各省集股商办的铁路收归国有,补偿的办法却十分不公,这相当于在国人的伤心之处再撒上一把盐。其中对四川人的补偿尤为苛刻,如两湖人民所缴的股金,十足发还;川人的股金,却换成了所谓的“保利股票”——这不是私吞国有资产,而是公吞私人资产——随即,黑云摧城,乱起西南。
这里且多说两句。无论是中国共产党还是国民党的正史,都将辛亥革命的开端定格于武昌起义。武昌起义之成功,遮蔽了此前诸多起义之失败。人们只记得,四川的保路风潮为武昌起义制造了擦枪走火的契机;却忘了,在此风潮之中,同样有枪声,同样有起义。起义者曾占领成都城东五十里的龙泉驿、双流县与新津县,尤其是新津县,义军坚守了一月,直到10月13日,武昌起义后三天,才因弹尽粮绝,被清军攻陷。
为什么历史的荣光都落在了武昌起义头上呢,想来缘由有二,其一,这是一场成功的起义,激起了四海九州的革命火花,这么说,大概有一些成王败寇的意思,然而历史之神就是这般世故,更眷顾成功者而非失败者;其二,武昌起义是革命党人所领导,四川的保路风潮,据尚秉和《辛壬春秋》记载:“……素无同盟会党踪迹,徒以激起怨忿,揭竿而起,故乱数月而省城不陷。及武昌兵起,大江南北踵迹独立,川人始实行革命矣。”杨早《民国了》则直接将四川的辛亥革命归结为“袍哥革命”,认为“立宪派不过充当旗号,同盟会更是敲敲边鼓”。看来,领导者为谁,才是关节点。因为后来的历史,乃是由当年的革命党人及其政治后裔所书写。
诠释辛亥革命这一段历史,托克维尔的作用,到此为止。再向深处追索,就需要引出我的疑惑:这场革命,与改革的政治谱系的关系,与改革者的关系,到底有多大?
近代史研究者都无法忽略一个吊诡的问题:1909年后,晚清改革出现了倒春寒,按理说,此消彼长,接下来理应是革命的高潮迭起,实际上,从1909到1911年,革命党进入了前所未有的低潮期。改革与革命几乎一同沉寂,这是为什么?
据路康乐考证,1905到1908年乃是革命党人最活跃的时期,随后则偃旗息鼓;据张玉法《清季的革命团体》,从1903年到1908年,每年至少诞生20个革命团体,1909年到1911年,均数则降至15个;据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所建构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辛亥革命前十余年间,革命话语的高峰,出现在1903年与1906年,从1907年起开始下降,1911年则跌至幽暗的谷底。对最后一项研究结果,有人会反驳:革命不仅仅是话语,不谈革命,并不代表不去实行革命。这个观点,置于其他历史时刻,也许可以成立,但在晚清却丧失了灵效,因为当时革命的一大表征即造势,言革命即是行革命。
是故,金、刘结论称:“1911年清王朝被推翻,乃是由绅士公共空间扩张而颠覆王权造成,它是立宪改革必然导致的结果。”
这可不是什么一家之言。就我阅读所及,这一宏论,应由张朋园发端,在2011年——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大陆学界(这一年关于辛亥革命的图书出版盛况,诚可谓“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得到了广泛的印证。譬如雪珥称辛亥革命为“计划外革命”,革命只是改革路线的歧出,武昌起义只是偶然迸出的革命星火(连革命党领袖都未曾料想由此而成就燎原之势);祝勇眼中的清朝:“仿佛一个巨人,竟然死于一次微小的感冒。”
我大致认同这些观点,只是需要警醒,为晚清改革翻案的同时,切不可高估;重审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是非功过的同时,切不可情绪化——“高估”与“情绪化”的佐证,便是一些论者,满怀现实的块垒,刻意抬高改革而贬低革命。纵然百年以前,改革者与革命者相争不可开交,甚至视对方为寇仇,实则他们构成了一枚硬币的两面。辛亥革命,正出自这两派的合力。
在雾霭沉沉的辛亥年,改革的低潮使立宪派倾向革命,革命的低潮则造成了革命党领袖的缺席,如武昌起义的第一枪打响之际,孙中山在美国,黄兴在香港,宋教仁在上海,这一缺席,成就了立宪派的契机,他们刚刚转身革命,便攫取了领导权,并主导了革命的走向:集中于城市与精英,以妥协为主流,破坏性被限定,暴力色彩被弱化……
空口无凭,且以数据和史料为例。先说辛亥革命的领导权,正史归功于革命党人,实则他们的功用只是“引导”,而非“领导”。武昌起义之后月余,响应独立的共计十四省;未独立的共计八省。十四省里,如江苏、四川、贵州、安徽等省的独立,几乎由立宪派一力发动;广东、广西、福建、浙江等省的独立,基于立宪派与革命派之合作;湖南,则由革命党人发动,十天后政权落入立宪派之手。据张朋园统计,除了陕甘二省的立宪派对于辛亥革命的浪潮表现消极乃至反动外,其他诸省——特别是那些未独立的省,因革命党被当局视为贼寇,欲赶尽杀绝而后快,立宪派反而获得了更广博的活动空间——立宪派及其领导的咨议局,皆扮演了举足轻重的政治角色。如张一麐称:“辛亥革命,皆以咨议局为发端。”
我们的某些史书,曾大肆讥嘲时任江苏巡抚的程德全,为了落实“革命必有破坏”的谬说,亲自爬上巡抚衙门的屋顶,用竹竿挑下三片瓦,将衙门的招牌换为军政府,便宣布江苏(苏州)独立。并以此为例,教育青春期的受众,辛亥革命的果实就是这样为立宪派的硕鼠所无耻窃取。我无法判断这是不是谎言,却可以判断,这必定是一种偏见。事实上,那么多龙盘虎踞的清朝封疆大吏,程德全乃是第一个公开反正者,这份胆色,这份心胸,足以光耀汗青。除了我一直未找到出处的“挑瓦革命”,程德全还割去辫发,将院司的印信、官服一起焚烧,以示决裂于清朝——这庄严一幕却被历史的书写者与教育者故意遗忘了,他们只允许后人的头脑记得,一个滑天下之大稽的立宪派如何反动,如何卑劣,如何一面与革命同行,一面挖革命的墙脚。
程德全所领导的江苏独立,绝非个例。所谓革命者,并不一定要躬冒矢石,辛亥革命并不完全是湖北那样的枪林弹雨,还有江苏这样的“和平演变”——借用冷战时期的一个时髦词语。统计起来,倒是为正史所不齿的“和平演变”的省市居多,如我寄居的城市宁波于辛亥(1911年11月5日)光复,几乎未费一枪一弹,绍兴、南昌等莫不如是。所以说,相比此前与此后的种种革命,辛亥革命实在是一场“低烈度的革命”,一场“天鹅绒革命”,基于立宪派与革命派的合作,实现了流血牺牲的最小化。帝国的巨人,不是死于腰斩,而是死于感冒。
辛亥革命,另有两大特征。这是一场城市革命,与农村无关;这是一场精英革命,与民众无关。如曹聚仁回忆录《我与我的世界》所述:“其后两年,辛亥革命到来了。我们乡僻地带(浙江兰溪),交通阻梗,不知秦汉,遑论魏晋,如‘革命’这样的名词,从来没听到过;乡间所说的,还是‘造反’,说是有人卖‘九龙票’。‘九龙票’,我也一直没见过,后来才知道这是光复会徐锡麟、秋瑾那一派所干的……”
辛亥年,后来威震一方的湘西王陈渠珍,当时是清朝军官,正驻军西藏。当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作为同盟会员的陈渠珍深知形势危殆,便策动部下湘黔籍官兵115名从西藏出逃。其至青海,在1912年6月,遇到一位随左宗棠出关而定居于此的七旬老人:“余询以内地革命事,但知:‘袁世凯为大元帅,孙文为先锋,国号归命元年。’亦道听途说,且误‘民国’为‘归命’也。”可见辛亥革命的话语传播,半年不达民众。难怪毛泽东说:“辛亥革命,乃留学生的发踪指示,哥老会的摇旗呐喊,新军和巡防营一些丘八的张弩拔剑所造成的,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没关系。”
在前现代的农业社会,当革命仅仅限于大中城市;在金字塔型的社会,当革命仅仅限于官僚、商人、军人、学生等中上层精英,那么它的杀伤力、影响力等,只可能滞留于这个社会的肌肤,而无法洞穿制度的心脏。
总结起来,我所理解的辛亥革命,是一场由革命党点火、立宪派烧饭、革命与改革两大阵营联袂打造的革命,一场低烈度的革命,一场城市革命,一场精英革命。辛亥革命的真实图景,远远背离了我们对革命的一贯定义,背离了意识形态所赋予我们的政治与历史想象。
改革与革命的双重变奏
我重点论述了戊戌变法的革命因素与辛亥革命的改革因素,唯愿由此推出一点事理:改革与革命,并不是必然处于相互对立的两极,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蜜里调油,水乳交融。它们好似调节社会平衡的两根杠杆,演奏政治乐章的两根琴弦,没有革命的压力,执政者哪会主动改革呢;反之,当改革的战车陷入了泥沼,对民众而言,若不革命,难道要束手待毙、引颈受戮吗?
革命与改革孰优孰劣,其实是一个伪问题。作为国家转型的政治路径,要革命,还是要改革,大多时刻都不是一种价值之争,而是实用性之争。甚至争都不必争,因为,有时不是中国选择革命,还是革命选择中国。
与其斤斤计较于辛亥革命的性质,不如登高一步,考察它的成果与方向:我们不仅要看到它的断裂,更要看到它的承续;不仅要看它为中国带来了什么,还要看它阻挡了什么。托克维尔反思法国大革命,认为革命前后的法国并无本质上的差异,他打了一个比方说,革命砍掉了政府的脑袋,然而其躯体依旧完好无损,行政机构的运行依旧按部就班,以前他们以国王的名义,随后以共和国的名义,最后以皇帝的名义审判和执政。对比之下,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何尝不是如此呢?时人总结:
共和政体成,专制政体灭;中华民国成,清朝灭;总统成,皇帝灭;新内阁成,旧内阁灭;新官制成,旧官制灭;新教育兴,旧教育灭;枪炮兴,弓矢灭;新礼服兴,瓴顶礼服灭;剪发兴,辫子灭;盘云髻兴,堕马髻灭;爱国帽兴,瓜皮帽灭;阳历兴,阴历灭;鞠躬礼兴,拜跪礼灭;卡片兴,大名刺灭;马路兴,城垣卷栅灭;律师兴,讼师灭;枪毙兴,斩绞灭;舞台名词兴,茶园名词灭;旅馆名词兴,客栈名词灭。
这许多改变,如“爱国帽兴,瓜皮帽灭”“卡片兴,大名刺灭”“律师兴,讼师灭”“旅馆名词兴,客栈名词灭”等,都是换汤不换药,其实并未改变什么。如“剪发兴,辫子灭”,国人脑后的辫子虽然剪去了,心中的辫子依然在纠结。民国与清朝,仍旧维系于同一条精神脉络。再如“总统成,皇帝灭”,变更的只是表面的名号,论权力之大,民国的总统远胜于清朝的皇帝。难道革命后的中国,没有前进,反而在倒退么?亲历革命潮并在湖北都督府任参谋之职的熊十力回忆道:“到了辛亥武昌起义,革命党也曾掌握过南方许多省,而新官僚气味重得骇人,暴露浮嚣侈靡淫佚种种败德,一时舆论都感觉……革命只是换招牌,而过去腐恶的实质,不独丝毫没有改变,且将愈演愈凶。”
所以我实在不能认同,将辛亥革命称作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历史并未在1911年出现断点,大革命并未摧毁旧制度,中国还是那个中国……
辛亥革命后二年,康有为、梁启超纷纷哀叹共和在中国“不过一时幻象”;六十年前的法国,托克维尔同样对大革命后的乱象痛心疾首。然而,将“幻象”、“乱象”的罪过全盘推到革命头上,是否合适?
百年后,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依旧是如何观察这一场革命。有时,不是革命出了问题,而是我们观察革命的眼神与视角出了问题,我们对革命的定性过于狭隘,对革命的观感过于粗暴,对革命的理解过于妖魔化,我们的历史视网膜蒙上了厚重的意识形态阴霾。托克维尔曾经提醒世人:“法国革命对于那些只愿观察革命本身的人将是一片黑暗,只有在大革命以前的各个时代才能找到照亮大革命的灯火。对旧社会,对它的法律、它的弊病、它的偏见、它的苦难、它的伟大,若无清晰的透视,就绝对不能理解旧社会衰亡以来60年间法国人的所作所为;但是人们若不深入到我们民族的性格中去,这种透视还不足以解决问题。”
——这难道不是在说辛亥革命与中国人?
2011年10月8日
参考文献:
《旧制度与大革命》,托克维尔着,商务印书馆,1992年8月第一版
《回忆录:1848年法国革命》,托克维尔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10月第一版
《谭嗣同全集》,蔡尚思等编,中华书局,1981年1月第一版
《北京法源寺》,李敖着,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年3月第一版
《革命逸史》,冯自由着,新星出版社,2009年1月第一版
《辛亥革命宁波史料选辑》,宁波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宁波出版社,2011年9月第一版
《中国近百年政治史》,李剑农着,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10月第一版
《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石泉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11月第一版
《立宪派与辛亥革命》,张朋园着,吉林出版集团,2007年8月第一版
《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周锡瑞着,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10月第一版
《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金观涛、刘青峰着,法律出版社,2009年12月第一版
《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金观涛、刘青峰着,法律出版社,2011年1月第一版
《告别皇帝的中国》,马国川着,世界图书出版社公司,2012年1月第一版
补记:
此文原系约稿,主题是“托克维尔与中国”,适逢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我便将托克维尔与辛亥革命放进一个锅里炖。于今来看,要谈辛亥革命,则当单刀直入,实在不必拉托克维尔的大旗,因其非但当不了虎皮,而且有可能妨碍我们把握辛亥革命的历史脉络。当然,需要反省的只是此文的写法,而非观点。
2014年2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