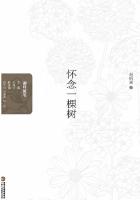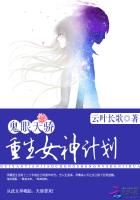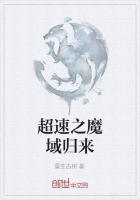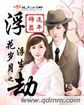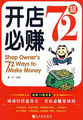一个小孩骑了自行车冲过来,买弄本领,大叫一声,放松了扶手,摇摆着,轻倩地掠过。在这一刹那,满街的人都充满了不可理喻的景仰之心。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罢?
如果仅从字面做简单概括,这番话主要的意思是“人生最可爱的”是“充满了不可理喻的”“那一撒手”,体现了一种张爱玲式的审美理想;但如果结合上下文来读,那么张爱玲的这种审美理想与社会理想是一致的,即期待一种充满温厚、宽容与混沌的母爱的自然流露的社会氛围。或者说,她以审美的方式建构了人生的价值取向。这种做法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现代竞争社会的哲学不大吻合,所以往往会被现实看做过于奢侈,不切合实际,但这种看法产生的原因不是作者本人远离了实际,而在于阅读中存在一种传统的思维定式,即她的写作难以限定在现代性的两极化视野里。其实张爱玲散文描写的恰恰是当时当地人最具体、可感的生活细节,但由于她阐述的人生理想既没有站在传统的立场,也不迎合现代性观念;既不依从革命的潮流,也不讨好反革命的主张,在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里一时竟找不到这种审美言说的位置,所以得不到强调对立和斗争的历史叙述的理解和认同。不过就真正的女性文本而言,这倒是张爱玲所做的最恰当的选择。
就女性写作与历史叙事的疏离倾向而言,以张爱玲的部分作品为例,不仅可以看到这位女作家由对现代性复杂的思考所形成的叙述张力;也可以看到在二元对立的现代性思维框架中,那些将历史剪接成革命与反革命、前进与落后的宏大叙述模式所具有的遮蔽和阉割历史的可能性。现代性诉求的历史合理性,已经成为现代政治最重要的内容,但由现代性设定的历史叙述方式,却使这种叙事滤去了更为复杂而丰富的历史内容,尽管历史中那些被忽略的内容,又会在叙述间隙不断以各种方式出现,使现代性难以形成叙事的一统天下。
尴尬的现代性尺度:向传统回眸的当代叙事
自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开始直到“文革”结束,把这一段当代文学史叙述为左翼革命文学发展为工农兵文学的历史时段,已经成为二十世纪文学史叙事中的一种定论。然而,对照“十七年”和八十年代对这一时期文学的评价,其间的一些文学作品既非“社会主义”性质(如“文革”前和文革中对它们的批判),又非“资本主义”性质(如“文革”结束后对这些作品的反思和重新评价),使“十七年文学”成为难以评说的历史。实际上,当我们以启蒙主义或现代性的标准作为评价这段历史的依据时,就会置身于这样的两难境地。一方面,作为二十世纪文学史的一个有效的历史环节,我们不能忽略它在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所经历的复杂的演化和蜕变,否则就不足以说明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文学的审美基因;或者说,现实的文学不可能凭空而来,只不过我们的文学史叙述由于种种原因,有意忽略了一些重要的线索。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用现代性的尺度加以衡量,这一历史时段的文学的确不符合启蒙主义所倡导的个性主义的标准,虽然启蒙主义的历史因素也深刻地影响到这些作品,但它们的确谈不上是对这种单一因素继承和发展的结果,从而也就更谈不到最终走上西方十七、十八世纪以来的文学发展道路了。不仅如此,它们还表现出对传统文学的眷顾,对乡土文化的持守,以及在此意义上对启蒙精神的背离。
这里的问题是,如果我们不再以现代性为惟一的历史评价尺度,不再由于要实现现代化目标就把一切不属于现代性视阈中的文化因素粗暴地予以摈除,不再用那种以其人之道还至其人之身的逻辑方式,用一种由现代性话语权力制造的新的二元对立模式来对待转型期复杂的文学现实,那么,这一历史时段中复杂的文学因素就会“浮出水面”,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从而揭示由它们形成的和连接过去与现在文学的历史扭结。
一般说来,承接五四和四十年代延安时期的革命文学传统,五十年代初期的大陆小说基本上以表现革命内容和工农兵生活为主。当时影响较大的作品有1950年发表或出版的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马加的《开不败的花朵》,朱定的《关连长》,方纪的《让生活变得更美好罢》,王安友的《李二嫂改嫁》,马烽的《一架弹花机》,张友鸾的《神龛记》,碧野的《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等;1951年至1954年发表或出版的柳青的《铜墙铁壁》,管桦的《小英雄雨来》,马烽的《结婚》,白朗的《为了幸福的明天》,孙犁的《风云初记》(第一册),杨朔的《三千里江山》,胡风的《伟大的热情创造伟大的人》(特写),刘绍棠的《青枝绿叶》,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李准的《不能走那条路》,巴金的《英雄的故事》,杜鹏程的《保卫延安》,知侠的《铁道游击队》,刘真的《春大姐》等;直到1955年出版的赵树理的《三里湾》,峻青的《黎明的河边》,周而复的《燕宿崖》,康濯的《春种秋收》,老舍的《无名高地有了名》,刘绍棠的《运河的桨声》,刘真的《我和小荣》等作品。仅从这样的作品目录来看,当时文学作品立意表现革命题材的倾向便十分明显。对新时代热切的期盼,对新生活热情的讴歌,通过描绘一个更合理、美好而健康的社会图景,以报答无数志士仁人为新中国的建立而付出的鲜血和生命,这一切作为文学的主题都充分体现在这些小说所刻画的人物、渲染的氛围,以及所绘制的故事情节中,使这一阶段的小说充分体现了革命时代的主导价值倾向。
但是,从读者对文学反馈的信息中可以发现,即使在革命时代的主流趋向中,文学的选择也不是单一的。当时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副主席、《文艺报》主编丁玲发表的文章《跨到新的时代来--谈知识分子的旧兴趣与工农兵文艺》,就反映了读者对文学的不同价值取向,文中说:“最近我们收到许多读者来信,谈到喜欢些什么书,不喜欢什么书和需要什么书的问题。”丁玲把这些来信的意见概括为这样几条:一、不喜欢读描写工农兵的书,认为这些书单调、粗糙、缺乏艺术性。
来信说“这些书既看不懂也不乐意看。又说这里主题太狭窄,太重复,天天都是工农兵,使人头疼。还有人举了一个工人的例子,说工人也不喜欢,那个工人认为这些书太紧张了,他们乐意看点轻松的书,如神话戏,或山水画。他们工作生活都紧张,娱乐还要紧张,怕要‘崩了箍’,他们说这些书只是前进分子的享乐品”。二、他们喜欢巴金的书,喜欢冯玉奇的书,喜欢张恨水的书,喜欢“刀光剑影”的连环画,还有一些人则喜欢翻译的古典文学。三、要求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苦闷,要求写知识分子典型的英雄,写出他们在解放战争中的可歌可泣的故事。要求写知识分子改造的实例,或者写以资产阶级为故事的中心人物,或者写城市的小市民生活的作品。“并且要求这些书不要写得千篇一律,老是开会,自我批评,谈话,反省……”虽然丁玲文章的主要意思还是要维护新的革命文艺,想对当时的接受倾向有所引导,比如说旧小说就像“那件龙袍,不管怎样绣得好,却只能挂在墙上任人展览了”,但她并没简单地对当时读者的不同意见采取否定或不屑一顾的态度,而是理解读者“希望能按照他们的兴趣来要求作者们有些注意和改变,他们希望能按照过去巴金、冯玉奇、张恨水的办法,来写些革命的浪漫故事,他们企图从这些书中受到益处,改造自己”。丁玲在这篇文章中对解放初期的图书市场曾做这样的统计:“比较通俗的作品,一般的可以销十万册以上,突出些的就不止这样,各地翻印,其总数有些应该是超过十五万本的”。这些数字表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读者对文学的需求与当时创作的总体倾向有一定距离。
任何时代的作家都不会无视作品被社会接受的可能性,也就是接受美学所谓“期望的疆界”的作用,文学史不仅由作家和作品这两个要素构成,读者的反应与接受也将决定作家的创作视角和表现疆域。五十年代初期的文学批评中虽然存在简单粗暴的风气,对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和朱定的《关连长》等作品的批判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例子,但即便如此,小说还是在读者接受的诱导下,把写“革命的浪漫故事”越来越多地推向前台,即使在表现政治色彩十分强烈的作品中,也可以使人领略“过去巴金、冯玉奇、张恨水的办法”。赵树理在一篇创作谈中说:“我写那篇东西(《邪不压正》)的意图是‘想写出当时当地土改全部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使土改中的干部和群众读了知所趋避”’,但如果小说从写土改斗争,一直写到整党纠偏,“篇幅既要增长,又容易公式化”,不如“套进去个恋爱故事”,“在行文上讨-点巧”,“把上述的一切用一个恋爱的故事连串起来,使我预期的主要读者对象(土改中的干部和群众),从读这一恋爱故事中,对那各阶段的土改工作和参加工作的人都给以应有的爱憎”。
由于读者在接受领域的需求,不仅作家选择了避免革命文学“容易公式化”,而把一切“用一个恋爱的故事连串起来”的这种“在行文上讨一点巧”的写作方式,而且在文学研究领域,专家和学者也把目光投向了五四运动以来,革命文学曾久违了的古典小说传统。1951年,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孙楷第撰写了题为《中国短篇小说的发展与艺术上的特点》的长篇论文,这位在三十年代被胡适誉为“研究中国小说史最用功又最有成绩的学者”,也曾把他长期研究古典小说的成果贡献给这个新的时代。他认为:“中国白话短篇小说的发展,由唐至明,经过三个阶段:
一是‘转变’,二是‘说话’,三是短篇小说。转变唐朝最盛。说话宋朝最盛。短篇小说明末才有,亦以明末最盛。”根据他对小说史的整理,他提出中国短篇白话小说艺术上有三个特点:“一、故事的;二、说白兼念诵的;三、宣讲的。故事是内容,说白兼念诵是形式,宣讲是语言”。他举明末短篇白话小说的“说白念诵之体”为例,认为“明末是中国白话短篇小说的黄金时期”。当时孙楷第讲古的目的是为了喻今:“明朝为故事而写短篇小说的风气,现在过去了。现在写小说,要教育人民,要为人民服务。这个理论,颠扑不破,稍微通道理的人,都不反对。不过,我想,人民是喜欢听故事的,并且听故事已经习惯了。我们要教育人民,必须通过故事去教育。故事组织得好,教育人民的效果愈大。若是以故事性不强的小说去教育人民,人民一展卷,就知道是教育他。他若是不愿在小说中受教育,索性弃去不观,则作小说的一片好意,一时化为乌有,岂不可惜?明朝的短篇小说,很少是有教育人民意味的,甚而是有毒的。但从有教育意义的几篇成功的小说看,我们从头至尾读下去,只觉得是听讲故事,并不是受训。却在听讲故事中间,不知不觉地受了感动。不管他的教育是如何教育,至少他的教育在宣讲的故事中,已经成功。这一点,我觉得可以供热心作短篇小说的同志们参考”。
孙楷第的文章表明,在五四薪文化运动中受批判、甚至被摈弃的古典小说形式,在建国初期的文坛又有复苏的迹象。正如他在那篇文章中指出,“明朝人用说白念诵形式宣讲口气作的短篇小说,在五四新文学运动时代,已经被人摈弃,以为这种小说不足道,要向西洋人学习。现在的文艺理论,是尊重民族形式,是批判地接受文学遗产。因而对明末短篇小说的看法,也和五四时代不同,认为这也是民族形式,这也是可批判地接受的遗产之一。这种看法是进步的。我想,作短篇小说,用明朝的形式也好,用明朝的形式加以变通也好,可以不必过拘。而明朝人作短篇小说的艺术精神,却极值得我们注意。因为,他们作短篇小说,的确是将自己化身为艺人,面向大众说话,而不是坐在屋里自己说自己的话。”(同上)
文学形式决不单纯是形式的问题,这一点今天几乎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孙楷第提倡小说形式向古典学习的动议中,其实包含了对启蒙话语的某种批评。在明朝人的短篇小说里融合着一种“将自己化身为艺人,面向大众说话”的“艺术精神”,这种“艺术精神”不是居高临下,教诲式的,而是把自己“化身”在和大众平等的位置上;不是自命清高地“坐在屋里自己说自己的话”,而是希求得到大众的理解和接受。由于这种小说观念汇合了五四以来的新小说形式,五十年代中后期便出现了“新”英雄与“老”故事相混合的革命英雄传奇小说的出版热潮。如果仔细分析这批作品,无论《林海雪原》、《青春之歌》,还是《红旗谱》、《红日》,等等,它们的小说观念都不是单一的,而是西方小说与中国传统小说写作方式的合成,现代意识与古典意趣的合成,当然其中也不乏非常强烈的由现代革命观念催发的浪漫倾向,这些纷至沓来的文学观念在当时形成一种社会和文学价值取向的生态环境。
而这些都不是用单一的现代性发展眼光加以打量,就可以说明了的。
现代性叙事中的反叛与对垒
上面所说的文学状态是在激烈的政治变革、政权交替刚刚完成后的五十年代。
由于波及思想文化界的政治运动还没像1957年以后愈演愈烈,或者虽然作品发表或出版在1957年后,但作家的主要创作活动是在此之前完成的;由于这一时段与过去历史关系比较密切,像《啼笑因缘》这样的通俗小说还有销售“十万册以上”的记录,也许还不足以说明在那样一个强调政治与阶级斗争的时代,文学却依旧有自身为现实政治无法完全左右的一面。如果我们再来看一下六十年代小说创作的情况,就可以进一步发现,随着现代小说作为一种汉语文学体裁被作家应用得更为熟练,它所包含的复杂意蕴不仅不能被当时流行的政治倾向所完全规范,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它由对传统的眷顾而表现出对现代性的不满,以及对现代性规定的单一发展目标的质疑,更表现出意识形态难以制约和涵盖的复杂内容。
六十年代的小说已接近“十七年文学”尾声。在不断升温的政治环境里,对小说艺术的探索却仍在继续。然而,探索的艰难不仅仅来自外部环境,也在于革命文学内部存在的分歧。把文学冠之以“革命”,是因为这种文学与革命的关系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