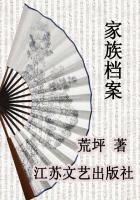圣诞节的校园十分安静。校长办公楼前大片开阔的空地,夏天是绿油油的青草地,眼下却是一片白雪皑皑;周边茂密的高大松柏上大雪压枝,放眼望去,青白相间,树木间似游走着一层忽厚忽薄的银蓝纱雾,让人联想到童话里的雪原景致。我踏着积雪斜穿过雪地,直面迎上逸林系里位于坡地边缘的大楼。
节日期间,大楼的门是锁上的。我拉下羽绒服上的帽子,口里哈着寒气,抹了抹脸上薄薄的雪水。想起丹文的消声匿迹、逸林的去向不明、许梅的猜疑反目,不禁叹了一口长气,蹬着靴子的双脚,无法自控地在积雪上踹着。这时,正好看到一个印度学生模样的人在推门往外走,我来不及犹豫,就身不由己地跨步上台阶,抢在大门合上之前,拉住门把,溜进了楼里。
我只要是抄近路步行往返于学校和住处,总会经过逸林系里的大楼,但平日里却不常进来。林产化工系是老系,楼也是老式的,而且还是有主、副楼的复式结构。走廊很长,却不宽,依楼面的走向曲拐折弯。一间间办公室、实验室的门显得很窄,却是木制的繁复花样,又故意漆成深深的原木色,更加重了楼道空间的压迫感。上下楼梯有很多处,都是窄窄的,到一层楼面就有一扇门。因为对楼的结构不熟,它总给我以迷宫的感觉,我在里面曾经走丢过两次,总要问过好几个人,才能最终到达逸林那儿。所以如果没有要紧的事,我一般不到这儿来。
我后来听逸林说,如果是乘电梯上下,就比较容易,因为主楼里只有一个电梯,记得上到三楼后,出了电梯,沿着走廊两个左拐再两个右拐,就到逸林的办公室门口。逸林的办公室和实验室都在三楼。
上电梯要经过系办公室。在幽蓝的日光灯下,窄窄的走廊显得空寂幽长。为了分散注意力,我一边走着,一边去看墙上的招贴。接近系办公室外面的墙面布告栏里,各种招帖花花绿绿的一片。我不经意一瞥,看到了旁边张贴系里教职员工和学生们照片的玻璃橱窗。
你看他的照片!你看他的眼睛!丹文那天夜里带着哭腔的高声在我的脑后传来,我立刻站了下来,幽深的沉寂随即压迫过来。我似乎听到了腕上手表秒针的摆声。丹文该不会到过这里,在橱窗里看到了逸林的照片吧?我忽然想。随即一个急步向前,抬头去找逸林的照片。这一看可不得了:橱窗的玻璃上,对着逸林照片的位置,竟然有一个红色的"X"号!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赶紧踮了脚凑近再看。
那是一张逸林在自己办公室里的照片,他穿一件阴丹士林色的衬衫,系一条深灰的领带,靠着电脑,坐在办公桌上,双手合着放在腿上,姿态舒缓而放松,面带微笑。跟丹文怀里揣的那张照片比起来,眼前照片里的逸林,有着掩饰不住的、由内向外发散的自信、沉着,完全一派阅尽沧桑后波澜不惊的淡定从容。照片下写着他的名字、职称和办公室门牌号。我再趋前一步,鼻子几乎是贴到了玻璃上,想去看清楚他的眼睛。可那是一张"拍立得"相机照出来的相片,清晰度很低,根本没法看清他眼睛的内涵。从总体印象来说,照片里的逸林比平日里来得活泼。我犹豫了一下,伸手轻轻碰了碰那个"X"号。直觉告诉我,它是用口红划出来的。
我的手刚想放下来,忽然想,也可能是血呢?这个想法吓了自己一跳,正犹豫要不要再摸一下感觉感觉,电梯出口那边走出一个男生。他背着一个大书包,大概见我抬手摸向那个红"X",便挤了挤眼睛。我努力想笑,却笑不出来。男生站下来,朝橱窗抬了抬下巴,操着一口南美口音说,看来胡博士有很多地下仰慕者啊。我尴尬地咧咧嘴。他也不看我,眼睛盯向那个红"X"号,若有所思地说,呵,大概是那天那姑娘干的,呵,你没见她盯着胡博士照片时的那表情,完全呆住了,简直就是震惊的样子。那一定是丹文了!我想,便退一步出来,朝男生问:什么姑娘?长什么样子?男生表情滑稽地看了我一眼,耸耸肩,说,当然是中国姑娘咯,挺好看的呀,很苗条,个儿挺高,脸很白,这点不象中国人。唉,姑娘们,可惜啊,太晚了,胡博士已经结婚了。他说着,也不看我,伸手去摸了摸那个红叉,嘴里喃喃说:"Lucky guy!"(幸运的家伙),然后有点幸灾乐祸地看了我一眼,走了。
Lucky guy?大概他是按美国人的思路,将这个红叉号读成了简示"拥抱"的符号;可他不知,在中国的法院布告上,这鲜红的"X"号,是划在死刑犯的名字上的。
我打了个哆嗦,回头再望向长长的走廊,已是空无一人。远处的一盏灯闪悠了几下,竟灭了,走廊更暗下来。那肯定是丹文了。想到这是丹文出没过的地方,我突然觉得过道里机关密布、危机四伏,吓得赶紧转身,快速地冲出了大楼。
我们系的大楼是现代化的钢筋混凝土简单结构,没有什么独特风格,却是一味地宽大,阳气十足。我来到课题组的研究生办公室,过节期间,这里别无他人。我一边喝着凉水,一边反复对自己说,忘掉他们忘掉他们。是他们──丹文、逸林和许梅。
退下御寒的衣裳,换下靴子,我打开了办公室里所有的灯,在热烘烘的暖气里听着音乐,埋头整理文件、实验报告,收发email。不知不觉,一个下午就过去了。天黑下来的时候,我走到学校边上的一家快餐店吃了份三明治,才慢慢走回家中。
远远看去,只有顶层厨房有微弱的灯光。我踩着斜梯上的积雪,轻手轻脚地从地下室的门口进到自己的屋里。因为担心许梅知道我回来了,可能再来多话,我的动作都有点小心翼翼的,只拧亮了桌上的台灯。脱下雪靴,挂好羽绒衣,沿着床沿坐下,很郁闷地叹了两口气,才想起回来后一直这么忙乱,竟连衣裳都没有洗,便打起精神,收拾起扔在洗衣筐里的一堆脏衣裳,准备到洗衣房里洗衣服。通向洗衣房的门一开,我便听到楼梯上传来隐约的话声。我屏住呼吸,竖着耳朵再听,竟听到了逸林的声音!
逸林回来了!逸林回来了!我兴奋得几乎叫出声来,扔下衣筐,直往楼上冲。刚上到楼梯拐角,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的鲁莽,立刻停了下来。这时,从一层楼面上传来了许梅的哭诉声,一阵高一阵低,呜呜的,她一定在努力克制着自己。因为那哭声非常压抑,所以显得特别凄凉。我给吓着了,一只手撑到墙上,想使自己安定下来。
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许梅流泪,更别说是这样的哭诉了。许梅这么好强的一个女人,都跟我说出了"不管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离婚的那口饭,都是很难吃的啊",真让人感到心酸。这时,我听到逸林的声音高起来:……我从来没有瞒过你,你总得也理解一点她的感受吧!我听清了他的话。她是谁?肯定是丹文了!逸林看来是跟丹文联系过了,他们应该还见了面。他要许梅理解什么?理解他和丹文的见面?他没瞒过许梅什么?他伪造学历的事,许梅知道吗?如果许梅不知道,在这么关键的时候,逸林会不会告诉她呢?……这时,逸林又高声说了一句什么,可我因为在走神,错过了。我从未听过逸林这样大的嗓门。疯了,全疯掉了,丹文,全是因为丹文的出现!我转身一骨碌溜回自己的屋里,关紧了门,坐下来,呼呼地喘着大气,可心里还是很高兴的,无论如何,逸林到底是平安回来了。再一想,逸林这样不明不白地失踪了两天一夜,许梅闹一阵,也是可以理解的。许梅也是人啊。我想着,心里也有点原谅她了。
在楼上时高时低的吵闹声中,我忽然想到了丹文。丹文现在哪里?感受如何?她和逸林是在哪里、以什么样的方式见面的?她得到了她想要的WHY吗?想到这儿,我看了一眼电话,心里竟盼望丹文会来个电话了。
丹文应该是见过逸林了。他们都谈了什么?怎么谈的?在那么极端的状态下,丹文竟然把持住了?当着逸林的面,她出示了手腕上的狐狸刺青?她有没有盯着他的眼睛,讲述那个美国女人将负心郎的睾丸割下、压成耳环带在耳上的故事?提到逸林用她的黄金岁月在新大陆上建起的事业大厦时,她是不是克制不住,拔出了揣在怀里的枪,在逸林的面前晃着,扬言要用历史的炸弹将那大厦轰塌?以丹文最后跟我通话时所处的精神状态,当她跟逸林──这个她号称是谱写了她的青春血泪史(唉,实在滑稽)的男人狭路相逢时,那些场景应该是无可避免的。
不管发生了什么,那个没有第三者见证的激烈场景,只能是当事人自己的秘密了。以局外人的眼光来看,却显然是没有发生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反倒是我自己虚惊了一场。无论如何,逸林到底是将事情给摆平了,幸亏我没有叫警察。他真不愧是个老狐狸。"老狐狸"这三个字,在我的喉咙里鲠一下,它让我突然想到,我也许是根本不认识逸林的。这个想法让人心里发毛。再转念一想,不认识其实也有不认识的好吧,比如说,如果我没有认识丹文,唉……想到这儿,我站起来,在屋里踱了几步,然后站在灯下,有点感伤地想,好了,丹文,他的本事大到这样,你也该服了,好好回到你未来的生活里去吧。
我拴紧了门,庆幸今晚可以睡个平安觉了。正在这时,楼上传来了摔门声,然后是车库里传出汽车引擎的轰响。许梅,许梅!那是逸林的声音,一路响出大门外。许梅开车走了?
我走过去轻轻掀起窗帘的一角,看到许梅的车子打着高灯,三下两下滑出车道,冲上了街上。转弯时车轮在冰雪上磨擦打滑时,传出了让人揪心的响声,可是许梅好像都没有减速,开着那飘忽的车子快速离去。这冰天雪地黑灯瞎火的,她能到哪儿去呢?不过是给逸林点颜色吧。我放下窗帘,忽然意识到,这倒是第一次,见到许梅向逸林耍脾气呢,还是不闹则已,一来就是个离家出走?唉,原来外表再成熟坚强的人,也有不堪一击的时刻,也会玩这种意气用事的游戏。我想到白天许梅对我的态度,苦笑了一下,摇摇头,熄灯上床。在黑暗中翻来覆去,至少有近一小时,才昏昏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