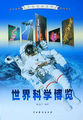有些善找另外含义的红学家,提出贾母与张道士有特殊关系的见解。这很有趣。
第一,当年,张道士是荣国公即贾母丈夫的替身,替荣国公修行出家。中国的办法实在很好,贵人要享福,也要行善、还愿、敬神,做一些受苦的事,受苦的事谁愿意做?可以委托代理。善可以代行,苦可以代受,愿(许诺、保证等)可以代还,神可以代敬,终极关怀也可以雇人派人代办,这是中国人的精明至极,精明过头的独一无二的做法。
其次,此张道士曾被先皇御口亲呼“大幻仙人”,贾母见他也是呼“老神仙”。善哉!一边是最高是皇亲国戚是权贵是此岸的形而下的顶尖,一边是宗教头面人物,是大幻是神仙是彼岸的形而上的精英。二者和谐相处,相得益彰,亲密无间。这种存其异而整其合,什么都为我所用的能力,也是罕见的,是一绝。
其三,刚刚责罚过贾蓉与下人的贾珍,与张道士一面见,便“把你的胡子揪了”云云地调笑起来,而见到贾母又毕恭毕敬地说什么“张爷爷来了”,这个老道的地位特殊,与贾家的关系特殊,谁能看不出来?
其四,他与贾母谈话确像老友老搭档。不仅谈话随意,而且谈得很深,而且,他是唯一能与贾母谈荣国公本人的人。贾母告诉张道士,她的那么多后代,谁的长相都不像荣国公,但是玉儿(宝玉)像,而这一点又是张道士先看出来先提的头儿。贾母向张道士诉苦,宝玉的爸爸逼着他念书,逼出病来了,这些话,甚至使二位老人双双落泪,关系不寻常,相知不寻常,感情不寻常,交流也不寻常。
是不是二老有过什么浪漫故事呢?我看不见得。以贾母的地位、思想、价值观念、行为规范、身价,以她的达观与善于享受生活(书里叫“享福”)的状况,不大可能做出太勇敢太颠覆太叛逆太满不论的事,这里还不仅是利害与道德问题。中国的一套防淫反淫观念确实深入人心,这里既有意识形态的规范作用也有经验上养生上的实际“根据”并从而形成的情感倾向。例如,中国人长期以来缺少良好的洗浴条件,肉体给人以不洁的感官刺激。中国人从生活到造型艺术,从穿衣到戏曲形象,都拼命遮蔽掩盖自己的身体,叫做“臭皮囊”的。国人还缺少营养乃至温饱的经验,更无性保健性卫生,性生活使部分人觉得吃力,有后遗症。包括曹雪芹,他在写贾瑞的时候也是走的防淫反淫的老路,《三言二拍》中的故事很多篇具有这方面的内容。“*”的教育意义也是视肉体需要为妖孽虎狼,看美女则必丧生,看骷髅才能有救。此外《红楼梦》中绝大多数女性,都是坚决反淫乱的。再看看我国各地的烈女传与贞节牌坊吧,其中不少是真实的与充满痛苦(哪怕是变态)激情的产物。
纵欲与禁欲,快乐与责任,私密性与伦理性,动物性与人文性,一直是人类男女交合中的悖论。我们反对封建,我们不赞成压制人欲,但我们仍然承认文化,承认必要的约束与自我控制,承认责任感、教养与野蛮的区别,承认淑女与荡妇的区别,正派人与流氓的区别,承认升华也承认仅仅yu望是不够的。
中国有一句很无奈也很实用,很通情达理也很苍白荒凉,却终于是有效的与有道理的话:发乎情,止乎礼。让我们假设贾母与张道士很有友谊,很有理解,很有共同语言,很有好感……好了,又怎么样呢?在铁的律条下面,他们能说说话,见见面,见面后找到个藉口一起洒洒泪,已经很人情味儿了,已经很温馨了,已经很弗洛依德了,还是不要再往好莱坞式的床上镜头方面胡思乱想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