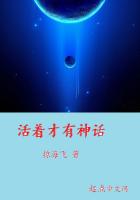出了项家大宅,项嵘和安忆苦同时回头看了一眼灯火通明的宅院,然后相视一笑。回到车上,项嵘帮安忆苦系好安全带,“对不起,说好要保护你的,却让你面对这种场景。还有,谢谢,谢谢你的挺身而出。”
“你家的蚊子咬了家里的客人,难道还要你替蚊子道歉么?夏天的蚊子何其多,即使有敌敌畏,也是杀不光的,更何况是人。不要把我当瓷娃娃一样藏起来,我要的是能够和你一起面对。至于谢谢,更谈不上了,我可是败坏了你的名声呢,以后人家都知道你的未婚妻是个没有教养不懂尊敬长辈的人,你会不会觉得很丢脸呢?”
项嵘用力的摇了摇头,隔着车手刹将安忆苦轻轻拥入怀中,安忆苦急忙推开他,“小心伤口”
项嵘却只是笑着,“看着你站在我身前,雄赳赳气昂昂为我们辩论,让我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温暖。”
“是吧,我也觉得我当时很有气势。”
“恩,很有女神范儿。”
“瞬间压倒那个葫芦女,呵呵~”
“葫芦女?”
“就是惟馨。”
噗嗤,项嵘忍不住笑了出来,“这个名字,额,很形象。”
“那你喜欢吃葫芦吗?”
“不,我喜欢吃黄瓜。”
安忆苦一听,作势伸手过去掐项嵘的脸,“你的意思是说我像黄瓜?!”
“恩?咱们不是在说吃的吗?”
“是在说吃的呀,食色性也,女人和食物在你们男人眼中有区别么?”
项嵘见身旁的妮子鼓着腮帮子气呼呼的样子真想去捏两下,脑子里这么想着,手也跟着伸了过去捏了起来,果然,手感不错。于是,车内两人很有喜感的互相捏着对方的脸,直到双方脸蛋别捏的通红才松手并大笑了起来。
如果说刚刚还有些因为母亲对自己和对安忆苦的态度而闷闷不乐,那么此刻那一点不快也被脸颊的痛感很对面女子的笑容给吹散。
而反观项宅内,众宾客纷纷告辞离开了,唯独剩下惟馨和另一名男子分散着坐在项家客厅的真皮沙发上。
惟馨低声安慰着项母:“阿姨,您消消气,学长肯定只是一时冲动,母子哪有隔夜仇呀。不过阿姨,您对学长还是得态度软一些,虽然自古忠言逆耳,可大多人还是喜欢听好话不是,您看那位姑娘能言会道的就知道啦。”
“哼,男人,都是这么肤浅。”
一直未说话的男子突然站起身,“项伯母,时间不早了,我们多有打扰,就先告辞了。”
项母这才记起身旁还有旁人,连忙站起身道歉到:“抱歉抱歉,我不是在说你,你知道的,我只是气过头了。”
“恩,我明白。不过这些毕竟是您的家务事,我们与您也只是第一次见面,实在不便讨论,馨儿,走了。”说着朝项目施了个礼便带头向门外走去,而他刚走到门口就听到了项嵘他们从车内传出的笑声。眉头不自觉的皱了起来,眼中隐约寒意凛然,眼看着伴着笑声的车子在夜色中疾驰而去,口中呢喃“原来你也会这么笑么?”
“哥,你走这么快干嘛呀?”身后响起惟馨的叫声。
“她说的没错,你的确很无知。”
“哥!你在帮那个女人说话?!难道连你也被她勾引住了吗?”
“我只是就事论事,项母根本做不了主,你如果真想得到项嵘还是多花点时间在正主的身上,别投错了医。”
“怎么会?世间有哪个儿子不听妈妈的话的?”
男子盯着惟馨看了许久,无奈的摇摇头,“回头我会将项嵘的资料送你,到时候你就知道我说的意思了。”说完抬头看了看夜空,一轮迷蒙的月亮独自挂在空中,他想对着月亮许个愿。
半夜,安忆苦突然从沉睡中惊醒,耳边似乎传来很多轻微的噪杂的声音,越来越响越来越响,好像一节节绿皮火车突突的冒着热烟朝她飞冲过来,烟雾笼罩着,身边的温度也越来越热,她慌忙睁开眼睛,房间中漆黑一片,什么都看不到。深秋夜晚的宁静被脑中火车声打破。安忆苦想坐起身,可除了一颗心噗噗乱跳,好像随时准备从口中跳出,接着便开始浑身打哆嗦,仿佛自己又成了一只因贪嘴去河边捉鱼而被冰冻在河中的猫儿,只一个脑袋露在冰面外,恐惧的本能让它大脑停住了思考,忘记了呼吸,连基本的喊救也不曾。直到慢慢适应这种冰火两重天的转变,大脑才重新能够思考,可依然无法动弹。安忆苦转头看看项嵘,他仰面躺着,睡得好不沉熟。轰隆轰隆…突突突…脑中火车声一遍一遍运转不停。好像无数次从她的脑门上碾压过去。突然沉睡中的项嵘突然翻了个身,手臂圈住了她的腰,在这当口,安忆苦像是古代武侠中被点了不让动的穴的人突然因那只手臂的碰触而被解了穴。可即使如此,火车仍在继续它的疯狂,安忆苦拿开圈着自己的手臂蹑手蹑脚的从床上爬下,摸黑打开了房门,走出了卧室。冷风吹在湿漉漉的肌肤上,让人忍不住的打起了哆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