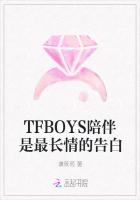我们一路上没说什么话,也因为老陈在睡觉。我想起来的时候在路上的情景,那似乎已经是很久以前了。我们可能都没料到:曹大余死了。
路两边是枯燥的冬天的风景:灰白、光秃的山崖,一蓬蓬长在夹缝里的干枯杂草,一小块褐色的、贫瘠的土地。有时候,我想闭上眼歇一会儿,可那张抖动着嘴唇、充满痛苦和哀求的、朝我仰起的脸总在眼前浮现,像水中的倒影一样,不断模糊又不断变得清晰。当我要从病房里走出去的时候,我本可以顺手给他搭上被子的,可我没有,我也可以听听他想说什么,如果我听了,可能他就不会死,可我不听,反而逃走了,我拒绝了一个垂死的人最后的要求。没有人想到他会死,我们并不知道哪些事会变得无法挽回。
回到场部以后,我们先去科室里报了道。把报销单据交给会计以后,我就到办公桌那儿,假装收拾抽屉里的杂物。后来,他们俩走了,其他人也都走了,我锁上抽屉,在办公桌前呆坐了十来分钟,才起身离开。
每一间办公室里都熄灭了灯,紧闭着门。我走在那条走廊里,听着自己的脚步声在空寂中清晰地回荡。我回想到那天的情景,就在这条走廊里,一个老人跑过来,跪在我的面前……而现在,她应该在医院里,陪着她的是一具尸体。不知道为什么,我也想起我的母亲。小时候,我爱哭,我会因为家里的狗病死而哭泣,她总说:“这孩子心软。” 可我现在走到了哪里?我的心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坚硬、冷酷?我一直替自己辩解,说死的那个人是个恶棍,悲惨的死是他应得的惩罚,说这一切都不是我的错。可我知道,这不过是用他人的罪恶替自己的罪恶开脱!
我走出场部办公大楼。寒风猛然向我迎面打来。外面,天已经黑了,不远处监狱高大的灰色围墙正和夜色融合起来。我走下大楼前面那十几级庄严、宽大的台阶,可那个投射在脚下、仿佛朝前爬动的影子毫无庄严之处,甚至让我越来越恐惧:一个冰冷、扭曲、畏缩的人,已没有了怜悯和怜悯的勇气。
2009年7月15日于新加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