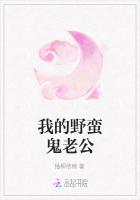文化是一種反映群體特性的意識形態,文化與其所反映的群體之間,往往表現為一種緊密的對應關係,從其中一方加以考察,易見另一方之形態(結構)與性質。因此,考察某一時期學術的發展變化,從兩方面的互動關係着手,應當是一種有效的方法和途徑。第一節《漢書·藝文志》所反映的漢代
“文化”格局與體系在中國早期的學術發展中,有兩個影響非常深遠的階段。其一是學術由“王官學”向“私學”的過渡,“道術將為天下裂”,百家之說紛出,從此形成了傳統學術的多樣面貌和多元格局。其二是漢代“獨尊儒術”,諸家紛然殽亂的局面又有了“一統”的指向,當然,此時的“一統”並非彼時的“不分”,衹不過是後儒為恢復先王理想的政治圖景所做的一種努力,諸家依然存在,不過由於經學的獨尊和淩駕其上,諸家學術具有了“流”的性質,一是“支裔”之謂,二是高下之分。這一觀念確立的影響是深遠的,後世學術雖代有其變,但大要總出入不遠。漢代的學術總謂之“文學”,此乃廣義言之;狹義言之,“文學”乃指經學(漢代的“文學”有時泛指一切學術,如張蒼“本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善律曆”,“秦時為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太史公稱其“文學律曆,為漢名相”(《史記》卷九六《張丞相列傳》,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2681、2676、2685頁),“文學”則包羅張蒼以律曆為主的所有知識;“於是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為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矣。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而賈生、晁錯明申、商,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史記》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第3319頁),則律令、軍法、章程、禮儀、詩書等等,均為“文學”;“宣王喜文學遊說之士,自如騶衍(陰陽)、淳于髡(學無所主)、田駢(道)、接予(道)、慎到(法)、環淵(道)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史記》卷四六《田敬仲完世家》,第1895頁),則稷下學可謂之“文學”;其他如“恬嘗書獄典文學”(《史記》卷八八《蒙恬傳》,第2565頁),這裏的“文學”指有關獄訟的文書、文件等等;晁錯“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先所,與洛陽宋孟及劉禮同師。以文學為太常掌故”(《史記》卷一〇一《晁錯傳》,第2745頁),此處的“文學”略指刑名之學。從上述例子大略可知,在漢代,“文學”具有廣義的意義,代指一切學術;狹義的意義指儒學,如“及今上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史記》卷一二一《儒林列傳》,第3118頁)、“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史記》卷一二一《儒林列傳》,第3118頁)、“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史記》卷一二一《儒林列傳》,第3119頁)等等。本文所謂“文學”,乃是現代意義上的“文學”概念。)。漢代的這一狀況頗有意味,“文學”主要指經學而言,當“文學”泛指一切學術時,這“一切學術”仍以經學為“獨尊”,這一字意的發生演變頗能反映漢代經學漸始獨尊的發生過程。漢代學術經學“大一統”的格局頗為典型地反映在總結西漢一代學術的《漢書·藝文志》當中。
一、“藝”與“藝文”:經學觀念之“文”
(一)劉向父子“七略”分類的意义:載道之文與術數之文的分渠
到劉向父子校書時,經學“大一統”的學術局面已經形成並深入人心。政治上,官僚系統既已無不重經,無不治經,唯經是導;社會上又以利祿相招,以經學為貴尚,經學觀念深入到社會各個階層,成為政治、文化、生活的指導之術。作為反映一代學術之盛的這次校書,勢必深刻地反映着時代的學術氛圍,從而形成自身特定的思路和構架(對於漢代學術內在構架的建構,于迎春曾說:“他們(漢代的學者智士)試圖建立起一個巨大的綜合,打通天地自然和人類社會的界域、分野,使各類事物和現象相互感應、貫通。董仲舒及其《公羊春秋》學說,就集中體現着這種大綜合的意識和努力。”(前揭《漢代文人與文學觀念的演進》,第35頁)如果說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和《公羊春秋》標誌着漢代學術“大一統”格局建構的開始,那麽可以說劉向父子編撰《七略》,就意味着對已經形成體系的漢代學術思想格局進行總結,並進一步予以強化和確認。)。
關於此次校書的原因,史載無多,《藝文志》在“(武帝)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諸子及傳說,皆充秘府”之後,緊承以“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言“書頗散亡”,當並不是指原有藏書的流失,因為從武帝收集圖書之後並没有大的戰亂、遷動、災異等發生,一般而言,皇家、官府藏書不易流失,較為合理的解釋原因,是成帝廣求天下圖書,而欲成一代學術之盛事(如《漢書》卷八七《揚雄傳》上載:“其(元延二年)三月,將祭后土,上(成帝)乃帥群臣橫大河,湊汾陰。既祭,行遊介山,回安邑,顧龍門,覽鹽池,登歷觀,陟西嶽以望八荒,跡殷、周之虛,眇然以思唐、虞之風。”(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3535頁)就反映了成帝欲效先王建盛世的心理。)。歷代帝王多有這種心理及文化舉措,而于成帝或更為明確。武帝時國勢的強盛及文化事業的輝煌,宣帝“循武帝故事,招選名儒俊材置左右”(《漢書》卷三六《楚元王傳附劉向傳》,第1928頁。),召集諸儒會講石渠等盛事,均不遠於前,這可能成為成帝此次校書的內在動因。
成帝時的這次校書,其分工是比較明確的,“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漢書》三〇《藝文志》,第1701頁。)。在此之前,是否有個集中的會議以確立校書的義例與“指導思想”,不得而知,不過從《藝文志》的情況看,《七略》的書目編排確實有嚴密的體系,首先體現的就是載道之文與術數之文的分渠。
載道之文與術數之文的分渠,是古代知識體系發展的必然結果。知識是先民在認識和改造世界過程中經驗及認識的積累,其原初狀態應該是,對生產、自然的認識與其實際的勞作過程是統一的、同步的,兩者之間不存在分離。但隨着這些經驗或知識逐漸集中在某些人手裏,並需要由之帶領,組織更複雜、更大規模的生產生活活動時,經驗或知識的把握就有可能與實際的勞作發生分離。並且,外在世界的神秘和強大使那些因為掌握經驗、擁有知識因而能更有效地組織生產勞作、克服苦難的人群得到尊重和崇敬,這時候知識就可能對具體、實際的操作發生超越,從而造成“勞心”、“勞力”的人群分化(至於“勞心”與“勞力”差别產生的根本原因,不是此處要討論的,這裏衹是指出知識在社會人群當中大致有這樣的分化。)。由於社會職能的不同,勞心者之知識漸與實際應用知識脫離,而向生產之管理與維繫人群秩序之制度轉變,這種知識的不斷積累和總結便形成各種所謂思想。
在傳統文化當中,思想的最高層次為“道”,“諸子紛紛,則已言道矣”(章學誠《文史通義·原道中》,葉瑛《文史通義校注》,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133頁。),古代的“道”有宇宙本體論的意味,但其根本的核心特徵是極具現實性的“治道”。儒家認為“道”在“王官學”未分之時,莊子感歎天下大亂,“道術將為天下裂”,其未裂時之“道術”,亦指向“王官”一統之時,“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司馬談《論六家之要指》,《漢書》卷六二《司馬遷傳》,第2710頁;《淮南鴻烈·氾論訓》也說:“百家殊業,而皆務於治。”(《百子全書》,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867頁) ),帶有本體意味的“道”更大程度上是為“治道”尋求終極依據而存在的。在言道而有影響的幾家當中,孔子、孟子、荀子、老子、莊子、墨子、韓非子是具有代表性的,其大略可分為兩類:孔、孟、荀、墨、韓略同,其道乃典型的“治道”;老、莊為一類,其有對現實秩序進行解構的傾向,但解構與建構為一體之兩面,“道家”仍有“君人南面之術”的內涵,事實上,言“治道”為諸家共同的主體性特徵。在諸子之前的先人的實踐當中,“道”、“器”雖已分化,尚還離之未遠,“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錯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周易·繫辭上》,《十三經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83頁。)。“道”、“器”結合表現為“用”,成“用”乃謂之“事業”,在歷史的記載中,掌握“道”的先王基本都是親力親為,與民眾一同勞作的。
與先王往聖躬身親事不同,諸子既已離事言理,空言論道,其“道”論就有了脫離、超越形而下的職事之勞、物事之思的體性。孔、孟、荀、韓的“道”論,無不以對具體職事的忽略乃至鄙視為特徵,墨子倒是重視“小人”道,其本人也善技,其留意于先王能與民同役、賢人或起於農工的上古情形,但其言及的內容及所針對的对象是“王公大人”,並無重視具體職事之意,且把“小人”道期望成對統治者的一種要求,因其“刻薄”,也就快速地被統治者拋棄了。老子主張捨棄“什伯之器”,《莊子》文中雖多有即“技”求道的場景,但“臣之所好者,道也”,“技”衹是進乎“道”的途徑,全書當中並没有提升具體職事的意思。當然,“道”、“器”之分,“道”上“器”下之别並非由諸子開創,其實現實的社會生活中,已有了制度上的規定:“凡執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出鄉不與士齒,仕於家者,出鄉不與士齒。”(《禮記·王制》,前揭《十三經注疏》,第1343頁。)不過諸子紛紛言道,繼社會的實際存在、制度的具體規定之後,對“道”為貴、“用”為輕的觀念在思想文化上予以了強化和確認。作為文化由王官學向私學轉軌的中介,諸子的思想對後世的影響是相當深遠的,《七略》對漢乃至先秦的學術進行總結,正是以“道”、“用”不同論對學術進行了二分。
章學誠認為:“《七略》以兵書、方技、數術為三部,列於諸子之外者,諸子立言以明道,兵書、方技、數術皆守法以傳藝,虛理事實,義不同科故也。”(前揭葉瑛《文史通義校注》,第985頁。)葉長青說:“三略(《兵書》、《數術》、《方技》)皆致事實之跡,與《諸子》、《詩賦》之徒托空言者不同。”(葉長青《漢書藝文志問答》,正中書局民國二十九年(1940)版,第134頁。)姚名達也說“虛理有殊於實藝”(姚名達《中國目錄學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6頁。),“其(《七略》)稍可稱者,惟視實用之‘方技’‘術數’‘兵書’與空論之‘六藝’‘諸子’‘詩賦’並重,略具公平之態度”(前揭姚名達《中國目錄學史》,第57頁。)。程千帆《校讎廣義》在分析《七略》為什麽要分成六類時說:“首先學術有不同。《六藝略》的主要部分是王官之學。《諸子略》所收為個人以及他那個學派著的書,是私門之學。詩賦、兵書、數術、方技則因各有專門,必加分列。其次是校書有分職。劉向是這次校書工作的主持人,他負責校理經傳、諸子、詩賦,而他不熟悉的兵書則由步兵校尉任宏分校,數術由太史令尹咸分校,方技由侍醫李柱國分校。”(程千帆、徐有富《校讎廣義》目錄編第四章《目錄的分類沿革》,齊魯書社1998年版,第110頁。)亦言兵書、數術、方技各有專門(這裏需辨析一下的是,說劉向不熟悉兵書、數術、方技當不盡然。在《漢書·藝文志》中,班固認為《七略·兵書略》中的《伊尹》、《太公》、《管子》、《孫卿子》、《鶡冠子》、《蘇子》、《蒯通》、《陸賈》,《淮南王》與其他略中的內容重複,因而把它們省略掉了,並把《司馬法》從《兵書略》中摘出而放入《六藝略》的“禮”類。先不論妥當與否,原先的情況至少說明劉向是部分地參與了《兵書略》的工作的。就現在還有留存的典籍看,《七略》原本列入“兵書略”的《管子》、《孫卿》,劉向就分别寫了《書錄》。另外,劉向作《五行傳記》,在孝成世又“總六曆,列是非,作《五紀論》”,劉歆作有《三統曆》(《漢書》卷二一《律曆志》上,第979頁),可知劉向父子對“五行”“律曆”是比較熟悉的。分工的不同當與職事的差别有關。)。
可見“七略”有“虛理”與“實藝”之分,並且,此“虛理”與“實藝”之别應不僅僅是“講道理”和“實際操作”的差别。“實藝”部分亦當有“講道理”的內容,此處的“虛理”當指“述道”之言,即“形而上者”,“實藝”乃指具體言“形而下”之技、藝、器者,即“道”、“用”兩分。“六略”當中,關於前三略“述道”,留於本節的下一個問題一併討論,這裏簡單說一下後三略的“技”、“用”特徵。兵者,歷來就是兵械、戰陣、技巧、形勢內容的彙集,屬於實用之技,與言大道的虛理不同,其為“王官之武備”,《藝文志》言“其用上矣”,即說明“兵”其為“用”的特質,也透露了在“用”之行列中,“兵”之用為“上”的事實,這應該是“兵家”列在後三略之首的原因。“術數”、“方技”為具體之技術,其質在“用”,如《術數略》言“天文”:“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紀吉凶之象,聖王所以參政也。”“曆譜”:“序四時之位,正分至之節,會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殺生之實。……此聖人知命之術也……”“五行”:“五常之形氣也。《書》云‘初一曰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言進用五事以順五行也。”“蓍龜”:“聖人之所用也。”“雜占”:“紀百事之象,候善惡之徵。”“形法”:“大舉九州之勢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數、器物之形容以求其聲氣貴賤吉凶。”無論是“序”、“步”、“紀”、“形”、“事”、“術”、“法”、“度”還是“器”,无非是對具體物事、術藝的記錄、推闡,無非是物“用”而已。又如《方技略》:“皆生生之具……今其技術晻昧……”二略記錄的都是實用之技。因此,正如許多研究者認識的那樣,“六略”有“虛理”與“實藝”之别,或者說,這樣的概括還不算準確,應當是“道”、“用”之分。
(二)“六藝之文”:漢代載道之“文”的最高綱領
《莊子·天下篇》說:“《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莊子集釋》卷八《天下篇》,前揭《諸子集成》第三冊,第462頁。)“六藝”早在諸子時期就儼然已有了超乎諸家的優勢,因為它是古代王官之常典。不過,“王道衰”、“政教失”之後,“諸子”並作而蜂出,這些原來的“王官政典”的地位受到衝擊,其再次取得政治、學術上的獨尊地位,是到了漢代的事情。漢代獨尊儒術,儒家從諸子各言其道的局面中脫穎而出,儒家之“道”成為“道”的核心和最高綱領。“六藝”之稱名,原指禮、樂、書、射、御、數六種技藝,以之來指稱《易》、《樂》、《詩》、《禮》、《書》、《春秋》,較早見於賈誼《新書》(《新書》卷八《六術》:“是故必待先王之教乃知所從事,是以先王為天下設敎,因人所有,以之為訓,道人之情,以之為真,是故內法六法,外體六行,以與《書》、《詩》、《易》、《春秋》、《禮》、《樂》六者之術,以為大義,謂之六藝。令人緣之以自修,修成則得六行矣,六行不正,反合六法,藝之所以六者,法六法而體六行故也。故曰六則備矣,六者非獨為六藝本也,他事亦皆以六為度。”(前揭《百子全書》,第111頁)),以後便流衍開來。到成帝時,經學已經取得獨尊地位,“六藝”被奉為經典,《易》、《樂》、《詩》、《禮》、《書》、《春秋》成為體現儒家之“道”的最高範本。國家既然組織這次校書,其目的自然就是要總結、建構、完善封建政治思想、文化體系,以昭示世人,規範、指導人們的思想意識。劉向、劉歆父子既為經學大儒,又是皇室宗人、政府官員,他們校書當然要完成對作為政治指導術、作為文化權威的經學的推崇,並把其他學術思想和門類納入到經學體系當中來,以完成學術“一統”的格局。對此,劉向、劉歆父子是煞費苦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