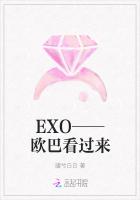吼完最后一句,唐浅早已流泪满面。这段日子她所有的无助,所有的恐慌,所有的怒火,所有的控诉都在话语和眼泪中倾泻而尽。她从来都不觉得自己软弱,但是为什么,为什么,眼前的这个男人要无情地摧毁她丁点的希望轻而易举!
“乾憩,你是弱者。所以你只配当本王的棋子。”
这是穆词殉离开之前给出的答复。多么理所当然的答复啊!唐浅想。
“可惜……我不是乾憩。真可惜。”
偌大的厢房,小孩惴惴不安地拿起刻刀,动手雕刻着手里的树根。突然,门轰然打开,一个年轻的女人尖锐地叫起来:“来人!把书童的眼睛给我挖了!”
哭闹声,求饶声,尖叫声扑面而来,场景变得乱糟糟一片。
两颗血淋淋的眼球在地上打转,停在他脚边,小孩呆若木鸡地注视它们,就像它们注视着他一样,手一滑,刻刀撕开指节的皮肤,殷红的血喷涌而出,污染了整个画面……
穆词殉兀地睁开眼。
黑夜,床,额头上密密的冷汗。
心悸?多么久远的感觉……他自嘲地笑着。
乾憩,你真该死!
“侧妃娘娘这几日并无异常,安分地呆在府内。”
“继续监视。”
“是。王爷。”
第十三天,距离那次晚饭已经过去十三天。穆词殉当初下达这道监视命令时其实也认为自己有些小题大做。从某种角度来讲,他算是相当了解乾憩吃软怕硬的个性,因此能很好地将她掌控在手里……只是,不知为何,突然觉得最近的乾憩太过于脱跳,貌似哪一块地方出了故障,却又找不到原因,隐隐觉得越来越握不住重心。
“呼……”
穆词殉甩出一本奏折,整个背懒倒于椅。这是父王当朝扔给他的奏折,瞧都不用瞧,一定是穆词靳又在郡土惹什么“祸国殃民”的岔子。
“该死,一个比一个该死!”
抱怨完,他倒失笑了。乾憩算什么东西,怎么能和他的宝贝亲弟相提并论?!
第二十六天,距离那次晚饭已经过去二十六天。
唐浅精神奕奕地练习着扎安绘教她的古字,虽然宣纸上满是鬼画符,但依稀能辨认出是几个字。难记,难看,笔画多,这是她对古字的一致评价。
逃出去的准备,似乎已偷偷搞得差不多,她目前唯一面临的两大难题:一件是时机,一件是悦露。
所幸,后一件正在逐步展开。来到这个挨千刀的古代她并没有和任何人深接触的打算,悦露是个扎眼的例外,如果她有幸回去,那也得把悦露的后路安排好,不然,王妃的刁蛮妹妹指不定把她祸害成什么样。
想来想去,那个扎安王妃总算不失为一个好归宿,让她教教字,乘机熟络熟络她和悦露的关系,到时候拜托起来也比较方便,一举两得。
心里打着小九九,唐浅冲着满桌子的鬼画符傻笑。傻笑一阵,又继而认真地鬼画符起来,脑子掂量着穆词殉什么时候能别跟个啃老族似的闲在家,出个征赈个灾啥的,也让她钻机会送他一件“超级大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