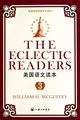五年前到北平时,为了要上课,配了一副眼镜,买了一座闹钟。五年来,人是流转了几个地方,却终于回到北平;闹钟也经了几个朋友的手,但最后仍回到故主身边来了。同来北平的朋友,甚至连好些来北平后才认识的,都星散了,眼镜也早另换了一副,有时望望这硕果仅存的闹钟竟不禁会发一点沧桑之感呢。
而且我这闹钟又有个特点,那是几乎所有我的熟朋友都知道的,便是永远快。朋友来找我,在屋里等了很久不见归来。便留字而去,字上的时间一定注明是“你的钟”若干时。因为“我的钟”既这样不同于寻常,我也便建设了我的理论,说:人有过快钟的,有过慢钟的,为了共同遵守时间就必须各人照自己需要把钟拨得快慢不同。譬如宴会,有人好早到,有人好迟到,有人性急,有人性缓,若大家的钟全一样,大家的时间反不一样了;因为同是五点钟,在这些人心中等于五点半,在另一些人心中却又当作四点多的。然而,我自己却是个性急的人,所以这理论还是不能做我要把钟拨快的辩解的。
不过近来这钟却老而反常,竟需要我天天往回拨了。本来是永远快半点至一点甚至一点半的,现在竟至少快到两点以上了。似乎将要到了赛跑的终点,几根针竟用上加速度了。起先,我还很高兴,以为这毕竟是我的钟;但后来它异乎寻常地疯了起来,连我也摸不着头脑了。有天正午十二点,我出去吃饭,饭铺里只有我一个客人,饭还没有蒸熟。又一天明明听到一声午炮,回头一看,短针正指三点。如果任其自然,结果是很容易算出来的。第一天照常快一点钟,第二天快两点,第五天不快不慢刚差六点,第六天开始慢起来,一直到第十天恢复准确后又重新开始快下去。于是算了一算,便不得不咬咬牙关破例把针往回拨了。但仍要维持原来的快钟,所以规定一天往回拨半点钟。但是它跑是加速度,我赶是等速度,两者依然不成比例。前进两步,后退一步,本来是好事,但对我的钟而言,却是不大方便的。
因此,某日黄昏,把这位老友送去治病了。因为他照这样急于前进,结果一定会疯狂自杀的。
晚间回来后,进屋的第一个感觉,便是忽然阒若无人了。一想,很奇怪,岂不是天天也这样没有人陪伴吗,何以今晚才感觉出来呢?一人坐在椅上,越过越觉得寂寥得很。听到街巷中的汽车呜呜,更感到自己像突然埋在深谷之底听谷上的风水声了。凑到电灯下,想翻开一本书来看,却总是发呆,不能看书。起来走几步,在室内绕了两个圈子,又到院中望了望星,还是不能驱除这突然袭来的孤独之感。打算睡了,照例一望那边柜子,想照例去上钟,才恍然于这位滴答不息的朋友今天倦勤休息了。
怪不得有的人出门要拿手杖,进屋要含烟斗呢。连这发挥单调的教训的老学究也不是能马上分离而不怅然的。“一个老朋友便是两个好朋友。”我擅自编改谚语了。
于是全神贯注回想滴答的声音。奇怪,这滴答的声音竟是那样亲切了。它亲切得像我母亲的絮语,听时那样厌烦,以后回想又是那样甜蜜。从母亲的絮语想到嫂嫂每晚灯下读弹词的歌音,那真是家庭幸福的最高点:一盏煤油灯,三五个缝衣妇,低而有抑扬的歌音缕缕叙出古时想象的女英雄的胜迹。这歌音对她们驱睡,对我却催眠:我是永远听不完故事就伏在母亲膝上睡熟的。
从迷茫的梦中回转来,微笑了笑,想该是上床睡的时候了。其实我是没有上床的准时候的,从晚八点以至次晨两点都是我上床去睡的时候。但这晚上却不然,竟想到是几点钟了该不该睡的问题。于是又起了无钟的怅惘,幸而还认得天上的钟,便打个呵欠起来到院中去看星。院子里多树,利于纳凉,却不利于观天。望了一会,把几颗明星略认定了位置,估量总有十点钟了,才进来准备睡。
上床以后更加想念这位老友的亲切的谈话了。因此想起了许许多多的事,反覆不能入梦。有什么办法呢?已经觉到了的缺陷是越来越觉其为缺陷的。
醒来时望望窗外,天是亮了,却好像没有太阳。究竟太早或是有云,在屋内当然看不出,于是去望永远对着床头的钟,然而不见。无名的怅惘又来了。
我何尝每天按时起床?天晴天阴于我又有什么关系?没有了时间岂不是正合吾意吗?那么当然是因为骤然离别了一个亲切的伴侣了。但是我向来对失落任何东西都只微笑而不肯皱眉,何以对这滴答不休的闹钟倒会眷恋起来呢?聚散之理自觉早已勘破,然而在实际人生中仍不能排除极细微的人之常情,智慧也者也就不仅是可悲的玩物,简直真是烦恼之根了。
年纪轻轻正该念念《雅歌》,叫叫妹子和新妇,却连《约伯记》也不感兴味,竟咀嚼起《传道书》来,难道是正常的现象吗?敬老人,爱儿童,恶人类,惧女子,种种奇特的不该有的感情每天从心中过来过去,而实际生活中却连一座闹钟也流连不舍,这又是何等不调和呢?
人世不易住,因为存了住的心。若根本不觉得自己的住,又何来好坏与难易呢?但自己还是住在人世,正像你不觉得有时间而你还在时间之内一样。对于自己的客观自觉和对于他人的设身处地只是一件事,以主观观客,以客观观主而已。这当然是智慧的起始,可不也便是烦恼的根源吗?人类原只是能造出自己达不到的理想的一种动物。
又一觉醒来,居然红日满窗了。
这一天跑了好几位朋友处,畅谈了一整天。黄昏时忙去取出闹钟,提了回来。
骤然失去滴答的老伴侣因而感到孤独;现在却因觉察出滴答声的亲切而更感到寂寞了。中年丧妻者的悲哀我固然从此能体会到较深的地方,但续弦之夜的新郎居然也会有要哭的感情,却是我这一次的重大发现了。
然而,坐对着这新交的老友,我心中还有个问题:
到底是我又有了时间,还是时间中又有了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