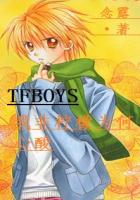转天一早,海棠就被周大娘叫到大厨房,说是有事情请她帮忙,海棠见我魂不守舍,很是不放心,但是碍于情面还是去了。没有她在旁边唉声叹气地要为我请郎中,我倒是清净了许多,只是一味地打哆嗦,仿佛走在两山之间的索桥上,稍不小心就会掉下去,摔得粉身碎骨。
周大娘推门进来时,我正在发呆,并未察觉有人进来,还是她出声叫我:“纪姑娘”,我才象灵魂出窍的人被猛然唤回来似的醒过神来。勉强起身相迎。
周大娘上下打量我,看得我心里发毛,不由抓紧了腰间的衣服。我的局促不安没能逃过她的眼睛。她回身关上屋门,将手中的食篮放在桌上,打开盖子,一股苦涩的药味散逸出来。她从篮中端出一只白瓷碗,里面黑稠的药汁兀自冒着热气。
她看着我,目光怜悯,“纪姑娘,长痛不如短痛。”
我一下子明白了那是什么,恐惧一下子将我纠紧,我下意识地摇头后退,盯着桌上的那碗,仿佛那是一碗毒药,会让我肠穿肚烂。
周大娘叹了口气,“留不得的。”说着端起碗走到我的身边,她每走一步,我就会后退一步,直到后背顶着墙,我已经是退无可退,大滴的冷汗顺着我的额头滴落下来。虽然这一日来,我不停想着如何才能解脱,可是真到此时我却如濒死般感到绝望。
我慌不择路地一闪身跳开,哑声叫道:“周大娘!”声音中已然有了哀求的味道,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在哀求什么,只是感到彻骨的悲凉。我看也不敢看她手上的汤药,仿佛那是恶毒的咒怨,只想躲得越远越好。
见我如此,周大娘凝眉思量,“可是莫漓先生的?”
我目瞪口呆地看着她。
“我曾在湖边见过你们。”她说着点了点头,“莫漓先生那样的人物倒也没有辱没姑娘。”她低头思索,随即抬头看我,“你赶快给莫漓先生写封信,让他即刻赶回来。外府的荣实是我的侄儿,我让他想办法将信送到南越。事不宜迟,赶紧!”
骤然听到莫漓的名字,我只觉得有一把钝刀来回地在我心上割划,那么痛,痛得我五脏六腑都跟着搅动。我多么希望这个孩子是他的,是我与他相爱的结果,可是此刻连这样想都觉得是折辱了他。
我身子晃了晃,面如死灰地摇摇头。
周大娘惊愕地张着嘴,仿佛不认识般地看着我。半晌方回过神来,她一言不发,默默地将手里的药端到我面前。我木然地伸手接过来。
是啊,我如何能留着这个孩子。暂且不谈这个孩子尴尬的身份,无奈的由来,我与莫漓的未来,我心心向往的明天都将断送在这个无法逾越的鸿沟面前。
泪水顺着我的脸颊滴落在碗里,我慢慢地抬手将碗凑在唇边。脑海中似乎有个声音在蛊惑:“喝下去吧,喝下去就什么烦恼都没有了,一了百了!”
就在这时,腹中扭动了一下,让我一下子停住了手里的动作。一般怀孕四、五个才会有胎动,我无法解释仅仅两个多月的身孕会有腹内抽动的感觉,但是我真的感觉到了,也许不是胎动,仅仅是一种绞痛。但是我一下子如被打醒一般,本能的母性瞬间被激发出来。他附着在我的体内,与我同呼同吸,血脉相连。他是这样柔弱,这样无辜,我是他唯一的倚靠,唯一的保护。我不能就这样抛弃他,我可以不在意谁是他的父亲,甚至可以忽略他是如何来到我的身体里,我只知道这是我的孩子,我要让他在我的体内孕育成长,我要将他带到这个世上,我要乳养他将他紧紧搂在怀里,我要牵着他的小手看着他一点点长大……
我手一松,碗滑落到地上,随着清脆的一声响碎成几半,飞溅的药汁溅到了我的裙角,屋里立刻弥漫了苦涩的药味。
周大娘摇头叹息,“即便拼上你的性命,你也不一定能留住这个孩子。”
我心里一惊复一凉,是啊,在这个时空如何能容得我未婚生子?
周大娘又叹了口气:“这药我让我侄儿抓了两副,厨房里还剩一副,我给你煎去。”
正在此时,紧闭的屋门突然被人用力推开,一个尖细的女声在门口响起:“不必了,姑娘还是先随我走一趟吧,云夫人有话问你。”
我愕然回头,却是云夫人身边的那个妇人,此刻叉腰站在屋内,一脸的鄙夷和幸灾乐祸。
我和周大娘面面相觑,周大娘勉强陪笑道:“李大娘,这演的是哪出啊?”
那个李大娘冷哼了一声,“演的哪出还得问你呀,一大早儿就在角门那儿看见你侄儿将两包药鬼鬼祟祟地交给你,什么病啊这么见不得人?要不要请个郎中给看看?实话告诉你们吧,荣实已经被夫人拘起来了,现在还请你们二人走一趟。”
周大娘脸色一下子惨白,我心砰砰直跳,已感到不详,仿佛大祸临头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