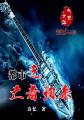清州城,织田家内。
晨光熹微,残存的黑色渐渐隐退,斑驳的雾气浊浊,笼盖苍穹四野。
房门吱呀,织田信长伸着懒腰信步走出,似乎是睡了个不错的好觉。
“国主,就在方才,今川军向围攻大高城的守军发动了突击。”说话的是长谷川桥介。
“哦,鹫津方面看样子也得有些动向了啊,跟我说说战备情况。”织田并没有过多的慌张神色:“哦,丸根方面的消息也说一下。”
“朝比奈泰朝等对织田玄蕃和饭尾近江守定宗父子五百人,丸根方面,松平元康对佐久间盛重四百人。敌方占有绝对的优势。”长谷川桥介恭敬地禀报着。
“嘻!嘻!叫小姓来,击鼓,取我的折扇。”突然听到这个消息,信长的举动又开始怪异起来。
桥介早已习惯了主人的脾性,当下也不多问,遵命照做,不多时小姓和折扇都一一到位,信长站在庭院里,冲着抹白的苍天高歌一曲,那是演绎四百年前平敦盛在源平合战中故事的能剧幸若舞:“人间五十年,万事如梦幻。一度生存者,岂有长不灭?”整只歌悲怆激越,慷慨激昂。
“拿具足来,吹响法螺贝。”信长穿上典型的伊予札当世具足,头戴风折乌帽子,手里拿着头型星兜,腰中别着阵太刀以及肋差,从身边仆人手中拿过早饭胡乱的吃了一通,抹了抹嘴便跨上战马,叫齐人手奔赴前线。奔出城寨,信长勒住马,转身看向自己的身后,清州城像是厚重的黄土塬,安详的在那里沉睡着,里面的居民还没有承受到战争肆虐的风沙,天色灰霾,不知道会不会降临一场暴风雨。
“想不到我织田会走到这一步,身边只剩下了一群草包啊。”的确,此刻在他身边的还活着的脑袋,只有岩室长门守、长谷川桥介、佐藤藤八、山口飞驒守、贺藤弥三郎五名骑马武士和两百足轻而已。信长感到胸中憋闷,打马朝着前方放肆奔行,一路上路过守备将领处便下令炮击呐喊,在睡梦中的守备军将纷纷心胆俱裂的从床上滚下来,慌张的穿上甲胄跟上队伍,一路上炮轰雷鸣,可谓是惊天地泣鬼神,信长打马狂奔在最前方,像是一头发情的狮子,在日本的土地上放肆的流汗奔走,像风一样的奔袭一直到热田神社方才停止。
信长进入神社祈祷,并宣读了讨伐今川义元的檄文,从神社走出来,信长看着面前多了十倍的兵力,不知不觉间在一路上有如神助,已经集结了两千的兵力,信长仰天长啸,声浪传遍四海:“信长方才在神前得到了吉兆,此战将是我尾张国运势大增,织田家永载千秋的定名之战,各位将成为不朽的武士,这是无上的荣光啊!”军士报以他的是一阵又一阵的声浪,方才的颓废阴霾一扫而光,毕竟这是一个信奉神明的国度。
接着,织田信长马不停蹄,继续南下来到水野忠光把守的丹下砦,再到佐久间信盛把守的善照寺砦——这两砦都是为了进攻今川方的鸣海城而修筑的。他命令两将放弃砦子,全数跟上,继续向南驰去。“国主是准备弛援丸根和鹫津吗。”长谷川不解的冲着信长问道,今天信长一直是以一个进击的姿态去打这场毫无胜算的仗,这样下去所有的守军全部撤回,的确是有点背水一战的意味。
然而此时,那两个砦子已经尽数陷落了。“探子来报,就在方才六七个时辰,织田玄蕃等将全都战死,今川原大高守将鹈殿长照进驻丸根,朝比奈泰朝守卫鹫津,松平元康则至大高休整。此时今川那家伙占有地利,守备军三千,我们如果仓促前去的话,很可能遭到惨败,甚至全军覆没。”长谷川焦急的冲着打马前行的信长说着。
然而织田信长并没有过多的反应,现在的织田信长,是一个像风一样的男人,不断地集结自己所能够操纵的所有的脑袋,在马背上伴着阴霾的天气放肆的奔走,整个大军不断的壮大,在愈发浓重的天色中发狂般的暴动,像是一群饥饿的孤狼在放荡的莽原上尽情的释放。
“把今川那个死胖子给我撕裂!我要杀光所有挡路的人!只有我能够进驻京都勤王称霸!只有我!织田信长!只有我!我赢定了!嘻!嘻!”
沓挂城,山脚寺庙。
“轰——”
神明像被推倒,小樱从里面吃力的爬了出来,顾不上满身的泥土,她吃力的站起身子,活动着僵硬的筋骨,推开了寺庙那两扇厚重的红木门。
面前是怎样的一副情景那……
横横竖竖的尸身摆满了整个寺庙庭院,残肢断手遍地皆是,干涸的血水浸润干涸的土壤,血红色的大地上是一具具面目狰狞的武士,每一个人的死法都是简单利落,要么是动脉被一刀抹断,要么是直接将手脚剁了下来,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残存着临死前的精彩表情,血红空洞的瞳仁里似乎在诉说着昨夜的恐怖故事。在庭院的中央,是一把饮饱鲜血的血色长刀,斜斜的插在血红色的大地上,在寒风呼啸中猎猎作响,小樱认得那就是墨尧的佩刀。
在那把刀的身旁,一个身着武士甲胄的中原人倒在血泊中,早已经没了知觉。
“不要——”随着一声撕心裂肺的呼喊,小樱扑到墨尧的身上,抱起早已冰冷的身躯放肆的哭泣“你回来啊,不要丢下我啊,你怎么能这样啊……整座庙宇都弥漫着哀伤的情绪,墨尧任由小樱抱着,眼神空洞的望着天,不过嘴角却有着一抹微笑。
一个男人,挡住了整个东瀛。
一只素白的手搭上了小樱的肩头,小樱吓得一下子打开了肩上的手,抽出刀对着身后就是一阵猛劈。
“小姐别怕!是我啊!我是明智光秀!”明智光秀被这突兀的状况搞得也是糊里糊涂,当下按住小樱,制止着她的失态:“公主!请自重!到底发生了什么啊?”
小樱突然不再挣扎了,明智光秀见到她安静了下来,试探性的松开了手,谁知小樱再次举刀便砍,明智光秀是成名的武士,当下闪身急退,不过胸前的甲胄已经划出了一道口子,里面的肌肤上渗出了一层细密的血珠。他弓膝跪地,对着小樱大声地喊道:“阿市公主!属下救援来迟,害公主受惊了,属下甘愿受所有责罚!”
“你们要是早来一晚,他就不会死,就不会死,就还和我在一起……阿市呆呆的喃喃,明智光秀帮她擦泪,阿市一把手将他推开:“你走啊,你们走!我不想再见到你们啊!”阿市不再看他们,抱着墨尧的身子,温柔的为他擦拭着面庞上的血迹,手法出奇的温柔温婉。
明智光秀没有办法,他更加想不透这个被阿市抱着的男人是谁,竟然能够让素来知书达理的阿市公主变得如此无礼无度。突然,他的眼睛扫到了墨尧的身子上,眼神掠过一丝惊讶:“阿市公主,他……应该是还活着!”
阿市惊讶的转过头看他:“的,没骗我?”
“属下尽力为他续命就是。”明智光秀说着,将墨尧背起来,叫了军医,开始全力救助墨尧。阿市在一旁悉心照料,一直忙活了一个上午。
“禀报公主,他的命暂时是保住了,只是现在还处在昏迷状态,这期间不能动怒,尤其是不可再动武,至于这个……”军医禀报着,伸手去取墨尧身边的刀。
“谁都不许动!这是他的东西!”阿市死死地抱着墨尧和他的刀:“我哥哥在哪里?我要去找他。”知道了墨尧不会有性命之忧,阿市的情绪也开始慢慢地平复了下来,恢复了往日的淡定从容。
“我们刚刚收到了最新的军情,并且已经告诉了国主,估计国主会根据最新军情驻扎进桶狭间,我们到了那里就会见到国主。”明智光秀从旁答道。
“走吧,我要和墨尧坐一个车。”阿市安静的说着,望着墨尧的眼神是那样的温柔。
“不可啊公主,公主的香车怎么能够让一个凡人坐那?”明智光秀皱着眉头劝谏。
“这个不用你管,总之要是不这样的话我就不走,我就是要他和我在一起。”阿市依旧是坚持着说着:“话说,他是这辈子除哥哥外对我最好的男人啊。”
明智光秀望着满地的尸体,出神的说:“这些都是他干的吗?”
“我们只相识了一天,我就知道,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傻子了,这个甘愿为一个只相识一天不到的人拼命地男人,这才是哥哥说的我最需要的傻瓜啊。”阿市望着墨尧,声音清澈如水。
明智光秀将阿苏和墨尧安顿好,有些阴翳的面容再次浮现,身旁的随从在耳边悄悄地说着:“国主已经前往桶狭间。”
“嗯,看来我的军情起到作用了那,到时候撞到了今川义元的大本营,我让他们全军覆没!至于这个公主……”明智光秀望着香车,嘴角再次浮现出了一抹残忍的微笑。
“出发!”
桶狭间。
田乐狭山是一座小山,海拔五十六米,附近道路狭窄,即田乐狭间,又名桶狭间。织田信长的军队已经朝着这里逼近,不日便可到达,此时的织田信长,手下的大军已经如神迹般扩大到了五千之众。
“光秀的消息究竟是否准确那?”马上奔袭的信长询问手下。
“光秀君从豪族梁田政纲处得到了的情报,今川义元因为身体肥胖,并且上身长、下身短,所以不能骑马,坐轿领兵,本队五千人行军迟缓;当日午间,行至田乐狭间,并在此停了下来。”
“这个事情我也是听说了的那,我还听说了一些更加有意思的事情那。”信长对着属下提高嗓门,继续说道:“我在小时候就读过中土人的《孙子兵法》,这个今川,竟然给我摆了一个一字长蛇阵,这是要保证自己的兵力散步均衡还是故意示威那,其实在我看来,这是在自取灭亡啊。”
“属下也遵从国主的意思,先遣部队已经扮成平民父老,在今川到达时,他们就会趋奉新领主,箪饭壶浆前来犒劳“王师”,等义元大喜,加之天气炎热,就会命令原地休息,待暑热过后再走。这样子的话不留在桶狭间都不行了啊。”桥介恭敬的说着。
“嗯,做得好那。而且松平也很听我的话,真真是按兵不动,这下子没了先锋,看他怎么打!”
天上阴霾的乌云终于开始渗透出丝丝雨滴了,闷热的气候一扫而过,雨势越下越大,织田信长望着天空,任由冰冷的雨水轰撞入自己的瞳孔:“全军整备,今夜子时,直捣黄龙!不对,应该是切断蛇头才是,赢定了,嘻!嘻!”
午夜子时。
明智光秀的军队已经到达了桶狭间山口,只不过现在的桶狭间,已经成为了一片修罗地狱,惨状不可描述,到处都是不忍直视的战争惨状,阿市与明智光秀并排坐在前面的马上,带着雨蓑衣,望着面前的宿敌决斗。
肆虐的暴雨更加成为信长偷袭的利器,今川军迎风而立,睁眼都很困难,更别说挺枪厮杀了。信长举枪向天,大声吼叫,全军顺风直冲义元本阵。今川军已接近崩溃的边缘,义元在旗本三百骑的簇拥下向后退去。
信长在暴雨中看到了义元的旗帜,立刻舍弃残敌,急速追去,等赶上义元的时候,这位“东海道一弓取”的身边只剩下了不到五十骑。信长的马迴服部小平太春安舞动长枪,直冲义元,被义元拔刀砍伤了小平太的膝盖。另一名马迴毛利新介良胜急忙上前相助,两个打一个,终于取下了义元的首级。
拿着今川义元的首级,信长在狂风暴雨中披头散发,状若疯狂的放肆嘶吼,发泄着心内的闷燥。
“哥哥受了很多的罪的。”阿市在明智光秀身边悄悄的说道:“织田家和今川家的世代恩怨,在今天终于以哥哥的胜利告终了。”阿市激动的无以复加,也在那里开心的哭泣起来。
“是吗……明智光秀的表情阴翳的厉害,左手不经意的下摆,身后的部队里有一部分人悄悄地退下,散布在了附近的山林之中。
织田信长依旧在那里发着疯,拿着首级耀武扬威,放肆的仰天咆哮,雨越下越大,身边跑过来几名武士拿着蓑衣想要给信长披上:“请国主先回营寨避雨!”
织田信长朝他们摆了摆手,那几名武士依旧在试图给信长披上蓑衣,突兀的,信长感到腰间一凉,已经泄了力道,因为一柄手里剑已经准确的扎在了后腰上。
“有伏兵行刺!”
整片山林里一下子窜出来十三名身着黑衣的死士,围绕着织田信长一阵猛砍,由于是大战刚过,织田信长的部将都死伤过半,剩下的也大多有伤在身,一时间十三个人如虎入羊群,无人可挡,在他们的眼中,织田信长已经成为一只最为可口的羔羊。
“快去救我哥哥啊!”阿市在山口急得都快哭出来了,只是身边已经没有了明智光秀的影子,他的亲卫队也是丝毫按兵不动:“我们接到的命令是保护公主,请公主不要随意走动!”
阿市有些绝望的望着乱军群中的织田信长,那个一生孤独的哥哥现在正在那里一个人孤军奋战,逐渐密集的雨幕遮挡着视线,殊不知已经倾倒了多少泪水,阿市实在是觉得自己很没用处。
就这样看着哥哥死吗……
身后的香车里,一道高大的身影形如鬼魅,略过众人,在狂风暴雨之中冲进了织田信长的包围圈,手中的长刀银光霍霍,所过之处尽是惨叫声响起,死士的搏击术在大明朝功夫下毫无威胁可言,织田信长的压力顿消,纵声长啸一声:“天不亡我信长!”挺枪也加入了混战之中。
不远处的阿市不知道是该欢喜还是担忧,因为那个手使长刀的少年并不是别人,正是南宫墨尧,那个救了自己性命的男人,正在用同样的方法营救着哥哥的性命。
十三个人,在两位天纵英才的少年手上,无一幸免。明智光秀的初步计划败露。
“嘻嘻,真是想不到,竟然是你这个短命鬼!”织田信长冲着墨尧咧嘴傻笑。
“我也没想到啊,原来是你这个傻子,这下我们谁也不欠谁的了,傻蛋。”墨尧这才发现这个男人竟然是当初认识的傻蛋。
“你还是叫我织田吧,我是尾张国主织田信长。”织田信长正色道。
“不管你是谁,在我这里就是傻蛋!”墨尧似乎有些疲惫,拄着刀喘着粗气。
“嘻嘻,你说得对,除了妹妹只有你敢和我这么说话,不过我喜欢那。”织田信长也是心情大好:“今后和我一起打天下吧,等我入京后,尾张就归你掌管,这个天下,我们一起定!”
织田信长雄心满满的拍着墨尧的肩膀说道。
“你也知道我是中土人,这里不是我的天下,我只想不让我珍惜的人死掉就好。那边的是你妹妹吧,我把她带来了。”墨尧的呼吸越发的粗重,只是肆虐的暴雨掩盖了一切。
“嗯,的确是阿市那。”织田信长朝着那边望了望。
墨尧听到这话惊得如晴天霹雳,他不顾伤势抓着信长的衣服:“你说她是谁?阿市!她就是阿市?”
“对啊,家妹阿市,你们还不认识吗?”信长有些不解为何墨尧会这么冲动。
“不瞒你说,我这次来就是受人所托来杀她的,为了给我未来的妻子治好眼睛,她是筹码。现在你什么都知道了,怎么做你自己选。”墨尧说这话的时候感觉心在撕裂,阵阵的隐痛。
织田信长呆呆的看着他,这句话传递的信息的确需要时间来消解,身边赶来的随从纷纷掣出刀剑,前一刻的战友此时却刀兵相向。
“都给我退下!”信长暴喝道:“这个男人要做什么都可以,即便是杀了我也不允许有人追究!”
“可是国主……”
“这是命令!违令者斩!”织田信长望着墨尧,第一次声音哽咽。
墨尧望着他的神情良久,并没有再说什么,他已经能够听见阿市跑过来的声音,拄着刀走到信长身边:“谢谢,傻蛋,我会消失的,你和你妹妹是我所珍视的记忆啊,又怎么能亲手抹杀那,愿你安好。”
长刀一挥,墨尧用尽残存力气发足狂奔,跳到了一匹战马上朝着远方疾驰而去,身后是昏黄的雨幕阻挡了送别的视线。
“这就是你的信念吗……”织田信长望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独自喃喃。
“哥哥,哥哥,他……”阿市跑到信长身边,将一个瓶子放到信长手里,下一刻已经昏死过去,毕竟是受了过多的惊吓,再加上舟车劳顿,又淋了一夜的雨,以女孩子的体质能够撑到这一刻已经是奇迹了。她身边的军医跪在地上,并没有查探阿市的病情。
信长看了一眼瓶子上的字,眼神突兀的变得异常的凌厉:“这药是你给他吃的?”
“属下确实是给他吃了,毕竟这小子之前已经是油尽灯枯,方才是他说可以救国主,属下才让他吃这药续命的,虽然只有七天的命活,不过能救下您就是有价值的啊!”军医恭敬地回应着。
“啪嚓!”
信长凶猛的摔坏了瓶子,朝着四周的兵士大吼:“拖走,就地处斩!”
不顾军医撕心裂肺的鸣冤,信长抱着昏厥的妹妹,在这个暴雨肆虐的雨夜,似乎胜利所带来的喜悦荡然无存,毕竟从天气来看,这就不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他温柔地抚弄着阿市的发梢,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为什么啊……”
“为——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