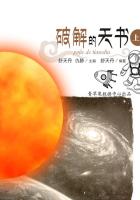奥蒂莉急忙赶回新别墅,叫来大夫,把孩子交给他抢救。这位先生见惯不惊的样子,按照常规对娇小的尸体一步一步地进行着救治。奥蒂莉始终守在他旁边,不停地找这个,取那个,忙着张罗一切,然而却神不守舍,因为极度的不幸一如极度的幸福,已改变了周围一切的模样。在试过所有的办法以后,那干练的大夫摇了摇脑袋,对她满怀希望的询问先是默不作声,最后才低声回答“没救了”。奥蒂莉一听便跑出整个抢救都在里边进行的夏绿蒂卧室,一踏进起居室就扑倒在地,连走到沙发边上的力气都没有了。
正在这时,门前已传来夏绿蒂的马车声。大夫恳请周围的人留在房里,他要单独去迎接她,让她思想上有所准备;然而夏绿蒂已经走进房来。她发现奥蒂莉倒在地上,府里的一个使女同时哭喊着奔到了她跟前。大夫接着也进了起居室,她一下全明白了。可叫她又怎能一下放弃所有的希望啊!老有经验而又高明、机灵的大夫请她千万别去看孩子,自己却回她卧室去,装着想其它办法抢救的模样。夏绿蒂坐到自己的沙发上,奥蒂莉仍在地上躺着,只不过已被抬到了女主人的脚边,美丽的脑袋靠在她的膝头上。友好的大夫走来走去,像是还在想办法救孩子,实际上却是为安抚两个女人。这样就到了午夜,叫人越来越感到四周一片死寂。孩子永远也活不过来了,夏绿蒂不想再欺骗自己,因此要求去看看他。他这时已经裹在干净、温暖的羊毛毯里,睡在一只摇篮中;人们把摇篮搬来放在了挨着她的沙发上。只有孩子的小脸儿露了出来;他安安静静躺在那里,模样儿挺可爱。
噩耗很快惊动了整个村子,跟即也传到了少校下榻的客栈。他沿着熟悉的道路摸到了山上,在新别墅四周转来转去,终于挡住一个跑去旁边的附属建筑取什么东西的仆人,从他那儿了解到进一步情况,并让他把大夫叫出来。大夫来了,一见眼前是自己过去的东家不禁吃了一惊,接着向他报告了目前的情况,答应帮助夏绿蒂作好见少校的精神准备。大夫进去了,先岔开了话题,把她的想象力一会儿引到这件事情上,一会儿引到那件事情上,最后才提起夏绿蒂的这位朋友,说少校肯定对她十分同情,说少校与她在精神和思想上本来就亲密无间,而他呢,将很快使她俩真正走到一起。够了,她已知道,她的朋友就站在门外,已经了解一切,只等她同意他进来。
少校跨进屋,夏绿蒂用以迎接他的是脸上的苦笑。他站到她跟前。她掀开盖在尸体上的绿色纱巾。借着一支蜡烛的黯淡光线,他看见一张毕肖自己的僵硬的小脸,不禁暗暗一惊。夏绿蒂指了指一把椅子,于是二人相对坐着,默默地一座座了个通宵。奥蒂莉仍然静静地靠在夏绿蒂的膝头上;她呼吸平缓;她睡着了,或者像是睡着了。
晨光熹微,蜡烛熄灭了,朋友俩恍若大梦初醒。夏绿蒂凝视着少校,情绪冷静地说:
“讲讲吧,我的朋友,命运怎么安排你来到这里,与我一道承受这份凄惨?”
“此时此地,”少校跟她问话时一样声音低沉地回答——好像不愿意吵醒奥蒂莉似的——,“此时此地,我不好含蓄矜持,转弯抹角,闪烁其辞了。您现在的处境是这样的严重,相比之下,那件我来找您谈的事本身固然也重要,却已失去了它的价值。”
接着,他不慌不忙而又简短地向她承认了自己此行的使命,告诉她爱德华派他来的目的,以及他本人此行的打算和希望所在。他把两件事情都讲得很委婉,然而十分诚恳。夏绿蒂平静地听着,既不显得惊讶,也未表现出不高兴的样子。
少校讲完了,夏绿蒂声音很低很低地回答,他不得不把椅子移过去听。她说:“我还从未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可在类似的情况下,我总是问自己:‘明天情况会怎样呢?’我清楚感觉到,现在大家的命运都掌握在我手里;至于我该怎么办,在我心里已不存在疑问,马上就可以说出来。我同意离婚。我本该早一些下决心这样做;我犹豫、抗拒,结果害死了孩子。有些事情命运固执地作好了安排。理性和道德也好,义务和所有神圣的誓言也好,都休想阻止住它:命运觉得是合理的事情就得发生,尽管在我们看来好像不合理;临了儿命运会强行贯彻自己的意志,不管我们怎么反抗都没有用。”
“瞧我说些什么呀!命运原本是在实现我自己的愿望,我自己的意图,我只不过是一时粗心,反其道而行之罢了。我自己难道不早就认为奥蒂莉与爱德华是天生的一对儿?我自己难道不曾企图把他俩撮合在一起?您自己,我的朋友,不也知道我这个计划吗?可我怎么会对一个男人的执拗与真正的爱情不加区分?我本可以作为朋友促成他与另一位女子的美满姻缘,又怎么会接受他的求婚呢?您只瞧瞧这个睡梦中的可怜虫吧!一想到她将从昏睡中苏醒转来,我立刻不寒而栗。她夺去了爱德华的孩子,夺去了一个奇异的偶然的造物,如果她没有希望以自己的爱情去偿还他,叫她怎么活得下去?怎么能不抱憾终生啊?她是那么倾慕他,热烈爱着他,因此也能把一切偿还给他。爱情既然能忍受一切,那就更能将一切替代。在这样的时刻,不容再考虑我怎么样。”
“您悄悄地离开吧,亲爱的少校。告诉爱德华,我同意离婚,我听凭他、您、米特勒去安排处理这整个事情,我对自己未来的处境毫不担忧,无论如何都不担忧。我愿意签署你们给我签的任何文件;只是别要求我参与其事,别要求我为此伤脑筋,别要求我想办法出主意。”
少校站起身。她越过奥蒂莉把手伸给他。他吻了吻这只可爱的手。“还有我呢?我希望如何?”他低声喃喃道。
“让我以后给您答复吧,”夏绿蒂回答。“我们虽没有什么过错该当遭到不幸,但也未干什么事情,配幸福地在一起生活。”
少校走了,心里虽为夏绿蒂深感悲痛,却对那丧了命的可怜虫惋惜不起来。在他看来,为了他们大家的幸福,这点牺牲是必须的。他想象奥蒂莉的手上已抱着一个亲生的孩子,完全补偿了爱德华因为她而蒙受的损失;他想象自己怀中也坐着个儿子,长相也和他一模一样,却比夭折的那孩子更加有此权利。
在返回客栈的途中,他心里充满美好的希望,脑海浮想联翩,不期然碰到了爱德华。他在野外等了上校一整夜,因为老没有礼花和礼炮向他报告喜讯。他已听到出事的消息,也没有为那可怜虫感到难过,虽然不愿完全对自己承认,却把此事看成命运的安排,这一下子,他幸福之路上的所有障碍可不都通通清除啦。也正因为如此,少校在迅速向他宣布他妻子的决定以后,就能够轻而易举地说服他先回到村里,然后再返回那座小城去作下一步的考虑,并且开始行动。
少校离开以后,夏绿蒂只是继续坐着沉思了几分钟;奥蒂莉已经苏醒,眼睛张得大大地凝视着她。她先从夏绿蒂怀里抬起头,随后从地上爬起来站在她面前。
“我这是第二次,”可爱的少女极其严肃而又温柔无比地开始了诉说,“第二次经历这样的事情。你曾经给我讲,人一生中常常以同样的方式碰上同样的情况,而且总是在重要的关头。现在我发现你的话很对,忍不住向你坦白一件事。我母亲刚去世不久,我还是个小姑娘,有一次就曾把小板凳移到你跟前;你也像现在似的坐在沙发上,我便脑袋靠着你的膝头,我似睡非睡,只是有些迷迷糊糊。周围发生的一切我都听得清清楚楚,特别是人们的谈话;可我却动弹不得,也说不出话,尽管我很想说,我甚至也没法暗示一下还能意识到自我。当时你和一位女朋友在谈论我,对我孤苦一人留在人世的命运深表同情;你描绘我寄人篱下的处境,说若无特别的幸运之星照临头上,那他我的前途将十分可悲。我曾认真仔细地,也许还过份严格地,领会你看样子是替我希望和要求我的一切;我以自己有限的见识,由此制定出了行为的规范。在你爱我,关怀我,把我收养在家的那段时间,以及后来还有一个时期,我都一直尊照它们生活,用它们指导我的所作所为。”
“然而我偏离了自己的轨道,破坏了自己的准则,甚至丧失了对它们的敏感。在这个可怕的事件之后,你重新使我看清了自己的处境,比以前还更加可悲的处境。头枕在你怀里,处于办麻木状态,我在耳畔再次听见了你像是从另一个世界里传来的轻柔的嗓音。我听见我自己是个什么样子,为自己感到不寒而栗;但就像上次一样,这次在半昏迷状态中,我又我自己画定了新的生活轨道。”
“我又一次下定了决心;你得马上知道我决心做什么。我绝不会成为爱德华的人!上帝以可怕的方式让我睁开眼睛,我看见自己陷入了怎样的罪孽之中。我决心赎补自己的罪孽;谁也别想使我放弃自己的打算!亲爱的,好朋友,你快想办法吧。让少校回来;写信给他,叫他别采取任何行动。在他走的时候,我一点动弹不得,真是太可怕啦。我真恨不得跳起来,大声喊叫:你不该让他带着如此罪恶的希望离去啊。”
面对奥蒂莉这个状况,夏绿蒂感到了它的严重严重性;但她希望随着时间的过去,再加以劝说,能使她回心转意。然而,她才讲了几句话,暗示未来会慢慢变好,痛苦会渐渐减弱,希望仍然存在,奥蒂莉便马上大声抗议:“不!别想再说服我!别想再欺骗我!一旦我知道你同意了离婚,我就跳进同一片湖水赎补我的过失,我的罪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