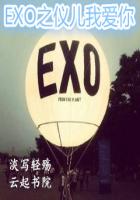受到上述事件以及与它相关的谈话的启发,第二天她们来到了墓地上;为了装饰这块地方,使其多一点生气,建筑师提出了一些很不错的建议。只不过,他所操心的范围一直扩大到了教堂上面;这座建筑,一开始便引起了他的注意。
教堂耸立在此地已经好几百年啦;按照德意志风格建造起来的,布局匀称,装饰也很成功。可以发现,附近一座修道院的建筑师在这座小小的建筑上,也表现出了自己的眼光和对事业的热爱。直到现在,它仍然给观赏者留下肃穆、美好的印象,尽管内部用于做新教弥撒的改造,使它失去了一些个宁静和威严。
建筑师没费多少力气,就从夏绿蒂那儿申请到了一笔相当数量的款项。用这笔钱,他不只要恢复教堂内部和外观的古朴,还想使其与前面那片充满生机的场地想协调。他自己手也很巧;还有几个参加建造别墅的工匠,他也挺乐意留下来,让他们一直帮着把这神圣的工程干完。
目前正处于对教堂本身及其周围环境和附属建筑进行勘查的阶段。这时建筑师异常惊喜地发现还有一个小侧堂同样值得注意,因为它设计布局更加富有思想和灵气,装饰更加繁多也更加悦目。而且,里边还藏着一些用于古老的礼拜仪式的遗物,有雕刻,有油画,都是作为不同宗教节日的标志,在纪念每一个节日时分别取出来,与其它圣像和圣器一起使用的。
建筑师忍不住立刻把小侧堂纳入自己的改建规划,特别想恢复这个小间的古老风貌,使其成为一座过往时代及其艺术趣味的纪念碑。他设想按自己的喜好装饰那些仍是空白的地方,以便展示自己的绘画天才。不过在家里的人面前,他对这件事暂时还保密。
首先,他遵照自己的诺言,给女士们看了他的收藏,即各式各样的古老墓碑、棺柩以及其它殡葬用品的临摹画和设计图。谈到了北方民族比较俭朴的坟墓,他便搬来自己搜集的一些陪葬器物和武器,供她们观赏。他有一些用木板条分成格子并且蒙上绒布的抽屉和匣子,他就把那些陪葬品井井有条地保存在它们里边,不但取放方便,而且使这些老气横秋的古董平添了几分色彩,让人观赏起来就像面对一个珠宝商的样品盒,心里禁不住喜滋滋的。既然已经开了头,既然寂寞需要排遣,他就每天晚上都搬一部分宝藏出来给女士们看。多数陪葬品都源于德国:中古时代的薄型铸币,厚型铸币,以及印章等诸如此类的东西。所有这些东西都把人们的想象力引向遥远的古代,而他最后拿出来提高消遣兴致的又是些最原始的印刷品、木刻和老古董的铜器,再加上日复一日,他都按照自己的设想,把教堂的色彩和其它装饰变得来越来越接近古老的原貌,这就差不多叫人不得不问自己,到底他们是不是生活在现代,是不是在做梦,是不是眼下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和思想信念都完全变成了另一个样子。
有了这样的精神准备,他最后拿出来展示的一个大皮包,就取得了最佳效果。里面藏的尽管多半只是些轮廓图,但都是直接蒙在原件上描下来的,完全保留了它们的远古特色,所以令欣赏者叹为观止!所有的形象都洋溢着纯净的生趣;尽管不能称它们都是高贵的,但得承认是善良的。乐观沉静,对我们头顶上的至尊者心悦诚服,无言而专注的爱和期待,流露在每一张脸上,表现在每一个姿态中。秃顶的老叟,卷发的儿童,活泼的小伙子,严肃的中年人,灵光环绕的圣者,翩翩飞翔的天使,所有人都显得纯洁、知足而幸福,都怀着虔诚的期待。即便是最平凡的事情,都带有天国生活的印记,祭典祈祷完全是自然的需要。
面对此情此景,大概多数人都会以外见到了一个已经消逝的黄金时代,一个已然失去的天堂。也许只有奥蒂莉一个人例外,她感觉画上的那些人才是自己的同类。
建筑师主动提出,要把这些古老的画面临摹在小侧堂的穹顶空白处,以为这个他过得如此美好的地区留下一个显著的纪念,对此有谁会表示反对呢。他在解释自己的意图时不无伤感;要知道根据现实情况,他多半已看出自己不会老是呆在这个完美的家庭里,是啊,也许他不久就不得不离开啦。
随后的一些天尽管没有发生多少逝去,却仍然有很多值得认真谈谈的理由。我们趁此机会抄录几节奥蒂莉有关这些谈话的日记;而在阅读她这些亲切感人的记述时我们不由得想起的一个比喻,正好成了理解它们的再适合不过的引导。
我们听说过英国海军的一条特殊规定:凡是皇家舰队的缆绳,从最粗的到最细的,在编绞时都得在中间贯串一股红线,不把整个绳子弄散就休想再把红线抽出来,因此即使缆绳断作了一下截一小截,其皇家的标记仍清晰可辨。
同样,奥蒂莉的日记也有一条倾慕和眷恋之线贯穿始终。它使所有的感想、看法和援引的格言以及其它种种文字,全都带上了记述者本人的特征,并且也对于她本人才富有意义。对这个说法,我们下边所摘抄的每一个段落,都可以提供有力的证明。
奥蒂莉日记摘抄
有朝一日长眠在自己心爱的人们身边,这是一个人在考虑生后事时所可能作的最美好设想了。“去与自己的亲人汇合”——这话听起来多么的亲切啊!
有各种各样的纪念物和标志,可以缩短我们与身在远方的和已故的亲人之间的距离;但是任何一种都没有画像那么有意义。与一幅心爱的画像谈心,哪怕是一幅并不毕肖的画像,仍旧有某种乐趣,就像与一位朋友争论,有时候也不无乐趣一样。你会感到快慰,你们是两个人在一起,而且没有办法分开。
有时候我们与一个面前的活人谈心,就像跟画像谈心一样。他无需开口,无需望着我们,无需关心我们的存在;只是我们看着他,感到自己与他有关系,是的,我们与他的关系甚至在不断发展,而对此他完全不用做什么,也没有丝毫感觉,他与我们的关系就好似一张画像一样。
对于一幅自己熟识的人的肖像,人们从来不会满意。因此我总是同情那些肖像画家。
我们难得要求他人作不可能做得的事情,却恰恰要求这些肖像画家。我们要求他们每画一个人,都在画中表现出他与其他一些人的关系,以及他的好恶;他们不能只画出自己对此人看法,而须画出人人对他的看法。因此我不感到奇怪,这些艺术家会越来越变得冷漠、固执和僵化。由此将出现什么结果都是无所谓的,只要不因此而少掉某些亲爱的、尊敬的人的画像。
是啊,建筑师所搜集的那些曾经紧挨着尸体埋在高高的土丘和石块下的武器和古老器物向我们证明,人为了保存自身而作的谋划都是枉费心机。而我们呢,却如此倔强固执!
建筑师承认自己也开启过先民的这种坟丘,可尽管如此,他仍继续忙着为后来的人建造纪念碑。
可为什么要如此慎重其事呢?难道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永远不变吗?我们不是早上穿好衣服,晚上又再脱掉吗?我们外出旅行,不是还归来吗?为什么我们不该希望长眠在自己亲人身边,哪怕仅仅只有一百年呢?
今天人们看见那许多倒掉的、被赶弥撒的人践踏的墓碑,看见那一座座倾圮在这些墓碑之上的教堂本身,总是有自己死后仍会获得第二次生命的感觉,以为自己会重新活在塑像和铭文中,而且还会活得比原本真正活的时间更加久长。可即使是这个塑像,这第二次生命,同样迟早会消逝。就像对人一样,对这些纪念碑,时间也坚持行使自己的权利。
1)菲力门和巴乌希斯是希腊神话里的一对白头偕老的恩爱夫妻。他俩为人善良,一次因帮助微服出行的天神宙斯而获厚赏,眼看着自家寒伧的小茅屋突然间变成了华丽的宫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