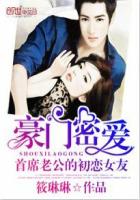有很多问题经常伴随着我。吃饭的时候,我常常会遇到下面的问题。
旁边的那个人为什么穿着红色的上衣?
是不是有一个人长得和我一样,刚在这里吃过饭,所以那个服务员露出惊讶的表情?
筷子掉在地上的时候我看到的那个女人的袜子上写了什么字?
要饭的那个人一天要说多少句哀求别人的话,每说多少句就会有一个人给他钱,会不会有数学规律可循?
一条鱼被我吃掉以后会不会找它的恋人?
我和一个不熟悉的网友上床是不是因为我们吃了一对正在谈恋爱的红薯?
我在饭店门口遇到的老同事喝了什么酒?
我有一次在吃饭的时候放了三个屁,一起吃饭的他们知道吗?
我为什么不太喜欢吃火腿肠?
我为什么喜欢边吃饭边听音乐?
工作的时候,也有一些问题伴随着我。
那个模特的脖子上的印记是做爱时留下的吗?
我该不该相信程东说的那句关于爱情的话?
摄像机拍到的影像在夜里会跑吗?
我为什么喜欢用漂亮的女孩子拍广告镜头?
女人的内衣广告播出时,为什么有男人打进电话说不喜欢?
我在楼梯口接电话的时候鲁北为什么看着我笑?
我办公室里的台历上记的那个电话号码是谁的?
我坐在办公室里发呆的时候,会被几个同事看到?
我给吴翠芝打电话,电话不通。我的脑子里会产生这样的问题。
她在洗澡吗?
她在商场里换衣间里换衣服?
她在和一个陌生男人约会?
她正在给我打电话吗?
她的手机没电了?
她在公交车上的时候被小偷偷了手机吗?
她遇到了一个男病人,看病时阴茎勃起了,于是她用手机砸了人家的弟弟,结果手机摔坏了?
她难道突然在街上遇到绑费或者强奸犯了吗?
我睡不着觉的时候,老会思考人生,会有这样的问题:
我刚才数的羊群中有没有一只羊是披着羊皮的狼啊?
我尿尿完了以后洗手了吗?
我的一本书的第一百零六页的第一个字是不是一个顺利的“顺”字?
我昨天和哪个女人握手了,洗完了手为什么还有她的香味?
我有一天过桥的时候绊倒了,回头看了吗?
我第一次坐公交车的时候有没有碰到过女人的身体?
我一直沿着一条乡下的小路走的话,会走到哪里?
我的人生如果有一千万句话,那么我现在写了多少句话了,有多少句是废话?
我累的时候,会不会刚好遇到一个椅子,而且那个椅子上还有一个枕头?
我坐在一个公园的广场上等人,会遇到这些问题:
留胡子的那个人为什么一直看我?
牵手走路的那对男女是情人吗,他们能走多远?
卖饮料的那个老板对买矿泉水的孩子说了什么?
一直躺在地上睡觉的那个是外星人吗?
打扫卫生的那个老人是书法爱好者吗?
我发呆的时候会不会有人突然叫我的名字?
公交车路过的时候有几个人站在了一起却没有看对方一眼?
我如果喜欢上对面椅子坐的女孩,要修多少年的缘才能亲她的嘴?
马舒适用了香水,味道很好闻。
于是办公室里鲁北和其他几个女人在那里讨论男人的味道。
鲁北说咱们办公室里的男人都是臭男人。
李若说,是的是的,程东有一次喝醉了酒,吐了一地。张强爱放屁。马舒适的白衬衣老是领子不干净。胡三刀的胡子老是刮不干净。主任倒是没有什么坏毛病,可是他的头发每天总有那么几根朝天阙。
鲁北说,朝天阙?还酹江月呢,你背宋词啊。
李若就笑。
李若看着我,那样淡淡地笑,让我感觉有一阵香味袭来。
她马上用手指了指马舒适,然后用手拼命地朝鼻子处扇风,于是我知道,一定是马舒适的身上有了什么不该有的味道。
我路过马舒适的身边时就闻到了那股淡淡的香味。马舒适竟然堕落到用香水的地步了,这让我很吃惊。
马舒适凑过来,让我闻,说,这种香味是皮革烟草香调,含有烟草味、皮革味和动物香的香调,很可以吸引女性,适合男人。
我也感觉到那种不俗的香味,一边想着该如何讽刺马舒适,一边却又忍不住问马舒适,这种香水的价格。
马舒适说,价格这种事情太俗了,不能说。不过我可以给你讲一下你适合用哪种风格的男用香水。
我?算了吧,我现在还不至于靠香水吸引女人。说完我就回到办公室了。
我出来的时候,鲁北和李若以及程东和马舒适还在那里讨论男人女人。
我问他们,你们讨论这么久,有没有把男人分清楚类别。
鲁北说,分清楚了,一种男人是用香水的男人,另一种是不用香水的男人。
李若说,一种男人是有肚子的男人,另一种男人是没有肚子的男人。
鲁北说,对了,还有一种男人是好色的男人。
程东说,男人都好色。
马舒适说,我有时候就不好色。
鲁北说,有时候不好色,你有时候还不吃饭呢。
李若说,有时候不能算,你如果一秒钟不好色也叫做不好色吗。
我听他们说得差不多了,补充道,男人只有两种,一种是好色,另一种是十分好色!
吴翠芝来找我吃饭。李若正好在我的办公室里找资料。
我说,你那天的衣服很好看。
吴翠芝说,有一个酒楼刚开业,好像是广东人开的。
我说,朱卫呢,赚钱太多了,该休息一下了。
吴翠芝说,对了,我新买的手机不太会用,你教我一下。
我说,头痛的时候多喝白开水有作用没有。
吴翠芝说,我们医院最近在治理大处方,你知道吗,我前天正好开了一个处方的医药费超过了两百,现在被卫生局监视上了,我的手机都被监听了。
我说,那你们家里的那扇窗玻璃换了吗?
吴翠芝说,我们科室里的小金刚生了一个孩子,生下来不哭,打屁股才哭了呢,真奇怪。
我说,报纸上说,今年进西藏的火车不在郑州停啊。
吴翠芝说,你这里有水喝吗。
我说,有苹果。
李若在那里翻资料翻累了,说,你们两个神经病啊,马头不对驴唇的,你们说得不累,我听得累了。
于是,我和吴翠芝哈哈大笑。
这已经是我们第二次这样捉弄别人了。
李若大概每隔十分钟就进来我办公室一次,我和吴翠芝开始不说话。
我在QQ上和一个叫做“拍拍我的肩我就会和你上床”的女孩聊天,我说,拍拍你的肩。
她回答,等一会儿,你排第十五号,我今天夜里只接街十五个男人。
我说好吧,不收挂号费吧。
她说,挂号费不收,但陪你说一句话要收一百万。
我说,一百万太少了吧,我加一毛。
她说,好吧,收账。
我说,那你等我唱首歌好了。
她说,不会吧,你上床前都是要唱歌的啊。
我正要回答,吴翠芝对着手机笑了,哈哈地笑。
我和李若都被她弄得莫名其妙。
李若跑到吴翠芝身边偷偷地看她写的短信息内容,然后小声对我说,她在骂人呢。
然后又看我和“拍拍我的肩我就会和你上床”的聊天内容,又跑到吴翠芝那里小声说。
我不知道她和吴翠芝说了什么,两个人一起出去。
办公室里突然安静,而我的QQ也突然掉线,孤单布满了我的房间,我突然很饿。
分管广告的副台长兼职我们部门的负责人,是我的师兄,叫童去非。
吃饭的时候,给我一把钥匙,然后指着停车场的一个大屁股的本地产尼桑皮卡车,说,这辆车借给你好了。
我有些迟疑,问台长,借多久。
他拍拍我的肩说,是分给你的,听说你的车子丢了。
我有些惊喜,但那一瞬间语无伦次,说,台长,我车子丢了你都知道,你不会知道我内裤的颜色吧。
台长转身就走,然后回头说一句,知道,黑色的,还掉色,对吧。
台长进入办公室,我才听明白,他一定收到过在我们台里来回传递了多个轮回的黄色手机短信。
我开车去就近的家世界超市买一盒牙膏和一些生活用品。
一楼有一个促销活动,我一眼在那么多围观的人中挑中了她。
我心想,这个女人的屁股这么熟悉啊,还有那肩膀,两只胳膊的位置,如果她回头一眼,我一定能在记忆中搜寻到她出现在哪条路上。
是的,我的记忆是一部情节复杂的电影,里面的人物经常忘记自己的名字。
然后,就在我发呆的一瞬间,她已经来到我身边了,牵起我的手就走。
拐角处的凳子上坐着为数不多的几个男女,一个男孩子拿着飞机模型在那里来回飞,他的母亲在那里打电话,声音很低。
我和吴翠芝坐在那里一句话也不说。
我看着吴翠芝脖子里的项链,竟然是我送她的那条,甚至链挎包也是我们一起买的那个特大号。
我心里想,不会有预谋在这里等我吧。
我们在那里各自发呆的时候,一个男人坐在了吴翠芝的旁边,碰到了吴翠芝的包。
那个男人忙着给吴翠芝道歉,然后忽然说,吴医生,你穿上衣服我真是认不出是你了。
吴翠芝没有说话,向他笑了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