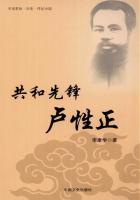李靖沉吟半晌,才道:“其实孝恭大夫已有主意,不必李靖再多饶舌了。”
侯君集急道:“靖公,你就别绕弯子了!到底要如何做,才能破局?”
李靖见无法推托,便往西南方向一指:“山南是此局破解之处。山南之地,山高路远,地广人稀,钱粮薄弱,所以豪强皆不屑争夺,只有朱粲聚集乌合之众,难成气候。然而正是这片土地,创造了很多奇迹。山南东接荆楚,西抵陇蜀,南控大江,北距商华,若派大将攻占,进可以出峡江,进伐萧铣,收复岭南;退可以保长安,攻陇西,牵制王世充。昔年汉高祖发巴蜀之人定三秦,刘皇叔也据此而建蜀汉,曹操虽善于用兵,也奈何不得。再者,古来征战,钱粮第一。近两年来,北方大旱,百姓又因战乱四处逃离,军需成了困难。因此,兵出山南,攻其不备,一来可另辟蹊径,开疆拓土;二来可取巴蜀钱粮,供关中大战所需。”
李靖一气讲完,众人连连颔首。侯君集道:“靖公讲得在理!末将请秦公来日奏明唐王,让末将率部去山南吧,保证不辱使命!”
李世民摇摇头:“君集忠勇,打仗我是放心的,但你性如烈火,弄不好会坏大事。听刚才靖公所言,我认为这步棋关系我们义师的出路,得派一位有胆略但个性温和的人去招慰才好。我看,还是孝恭兄去最合适。”
李孝恭起身道:“多谢秦公信任,孝恭当竭尽所能,办好这趟差使。”
侯君集心头有气,但一想,人家是哥俩,我毕竟是外人,争也没用,就老实坐下喝酒了。
就在这时,有斥候到府门前,说有军情要报。家丁拦着。李世民放下酒杯,怒斥家丁:“军情如火!以后凡有情急军情,就算我在床上睡觉,也得叫醒!”于是命斥候入见。
那斥候行礼报告:“禀秦公,陇右薛举号称三十万大军,派遣其子薛仁杲围扶风郡,欲向长安杀来。”
众人一惊。李渊驻长安兵马号称二十万,实际只有十几万,还要派守已占郡县和防止河南、河东等反王的袭击,加之粮草不济,应付当下局面已十分困难,如何能应对薛举大军?
李世民让斥候下去后,问李靖:“靖公,若论知兵,在座各位均不如公,你看该如何料理此事?要不,孝恭安抚山南的事放一放,先应对薛举,如何?”
李靖道:“秦公,当今之势,咱们刚才已分析过,倘若集中力量攻战薛举,一来兵力不足,胜负难料;二来给了各路豪强可乘之机。山南之行,刻不容缓,我军急需钱粮补给,不可因一隅之地而乱了方寸。”
房玄龄、李孝恭等深表赞同。李世民沉吟片刻,道:“好!明日我就禀明父王,请孝恭兄率军三万,抚慰山南,随时报与父王,伺机而动;请王世子守长安抵御来犯之敌;我亲率大军征讨薛氏父子,也请靖公随行。”
于是席未尽欢,宾主就散了。李世民是个讲求实际的人,但凡有紧要军务,自己的私事完全顾不上。
李世民忙着要向父王禀报,就委请李孝恭送李靖回府。
李孝恭性情温和,接人待物,颇为得体,不像其他贵族子弟那样趾高气扬。李靖再三推托,阻止他相送,但李孝恭借口道:“送靖公是假,到贵府拜访是真。孝恭到靖公府上,还真有两件事,一件是拜见尊夫人,一件是看看阴世师的遗女阴月漓,靖公不反对吧?”
李靖一愣,当即明白了:拜望夫人也是假,看月漓才是真。莫非这李孝恭,对阴月漓有意?
二人乘着酒兴,沿街奔驰,很快就到了李靖府上。
李孝恭拜见完张出尘后没有告辞的意思。李靖道:“夫人,你去把月漓叫出来吧,李大夫想见一见。”
张出尘正要去叫,却见李孝恭起身道:“夫人不用去叫了。若得夫人允许,孝恭想与靖公单独谈谈。”
张出尘会意,叫下人收拾了内堂,请李孝恭入内奉茶。
李靖道:“孝恭,现在只有你我二人,有什么话,请直言吧。”
李孝恭道:“不瞒靖公,秦公让我相送,实际上我身负重任。那日,秦公到贵府相救靖公时,见了阴家小姐一面,回去后就请我做媒。我耳闻,阴世师在世时,也请靖公为当今天子做媒,但靖公没有做,所以我请靖公再做一次媒。”
李靖心头咯噔一声,心想这事你们也知道了,好在当时杨侑没答应。于是说:“实言相告,我不赞成阴世师的功利想法,但当时确实也跟皇上讲了。天子年幼,认为不大合适,因此我才将月漓领到家中。这是件好事,月漓能嫁秦公,是阴家修来的福分。我没有意见,但也得私下问问月漓的意思。”
李孝恭抱拳道:“谢靖公成人之美。阴家小姐是靖公义女,靖公之言,必然相从,我也好回去交差了。”
他口头说是回去交差,但屁股丝毫没有挪动。李靖看出端倪,问道:“孝恭,咱们也算老相识了,你还有什么话,就直说,不要见外。”
李孝恭又行了一礼,道:“实不相瞒,孝恭此去山南,能否完成使命,心头没底。是以公事办完,想私下在靖公这里讨个主意。”
李靖见他如此,便问:“孝恭莫非不想去山南?”
“若有王命在身,孝恭哪敢推托?”李孝恭道,“我也知道,山南是我们的出路,但比起与秦公征战中原之地,恐怕其功绩就差得远了。”
李靖摇摇头,道:“孝恭啊,自古以来,帝王将相莫不将中原视为必争之地,但中原是王者之争,非将军用武之地。再说,中原以及北方,物产欠丰,远不及巴蜀、岭南和江南。这些地方人民殷富,盛产粮食、丝绢,朝廷用度,多出于此。倘若不用兵占据,等于丢掉半壁江山,物资无法畅达长安,所以孝恭此行,关系到国运兴衰,不在中原攻城略地之下。秦公虽年少,但有四海之志。他先考虑到你,是将千钧重担交给你啊!”
李孝恭一听,避席而拜:“靖公一席话,拨云见日,让孝恭茅塞顿开!若孝恭能取得成功,靖公当立首功!”
“孝恭不必客气!”李靖扶起他,“人,贵在相知。秦公与你,皆是人中龙凤,李靖能与你们共事,深感荣幸。”
李孝恭浑身来了精神,又问道:“还请靖公指点:此去山南,我须如何处事?”
“宜用怀柔之策。”李靖道,“山南首要之敌,是号称‘吃人魔王’的朱粲。朱粲每下一城,必将儿童分发给将士煮而食之,极不得民心,虽有十万之众,但不足为虑。你引兵前去,先不开战,而是遍传檄文,称新帝初立,将大赦天下,减免赋税,凡是归顺朝廷的人,论功行赏。朱粲靠残暴统御军兵,手下将士,只因无枝可依,不得已才跟着他打仗,但军士出自百姓,谁愿荼毒乡亲?孝恭将军出义师,当以仁德治军,宽恕敌人,亲近百姓,朱粲手下必然弃暗投明,山南及巴蜀之地,会很快平复,从而打开缺口,挥师直下,占据岭南,建不世之功。”
李孝恭叹道:“靖公深居长安,却对天下人事了如指掌,孝恭敢不从命!”
李孝恭走后,李靖缓步到了阴月漓窗前,但听内室有人啜泣。李靖轻敲窗棂,轻声问:“是月漓吗?”
里头的哭声停止了。月漓推开门,低首拭泪道:“义父,天色已晚,你还不歇息吗?”
“我来看看你。”李靖进屋,把门关上,“我们家清寒,你可还住得惯?”
阴月漓点点头:“义母待我,胜似亲生,请义父不必挂怀。”
李靖道:“刚才,李孝恭来为秦公李世民提亲,义父说要问问你的意思。”
阴月漓沉吟半晌,才说:“义父为了月漓好,女儿自然知晓。但李渊杀我父亲,与我们阴家有不共戴天之仇,我如何能嫁他的儿子?”
李靖叹道:“孩子,冤仇宜解不宜结。阴将军也杀了唐王的儿子李智云,这都是争权夺利种下的恶果。你是女儿家,不应该卷入是非之中。秦公李世民,仁义贤达,将来必有前程。他救过你和你弟弟的命,杀你父亲的是唐王,非秦公之过。你好好想想吧,若是不愿意,义父这就回了李孝恭。”
阴月漓放声大哭。李靖安慰良久,才起身出门。
刚刚跨过门槛,身后的月漓道:“女儿身世孤苦,全凭义父做主……”
李靖叹息一声,心知月漓其实喜欢李世民,就回到自己的卧室去了。
张出尘在灯下做女红。一针一线,柔婉动人。见李靖进屋,微笑道:“谈完了?”
“这么晚,还不睡?”李靖爱怜地看着她。
“我得把这些衣服都缝好。”张出尘道,“现下正值隆冬,战场上天冷,怕你冻坏了身子。”
“原来夫人知道我要出征了。”李靖道,“这些衣物,可以让丫头缝嘛,何劳夫人亲自动手?”
“夫君,你身体虽健,但你恐怕再无休养生息的日子了。我不亲自缝,将来想着你在战阵中经风历雨,会心疼得要命!”张出尘蛾眉低锁,幽幽地说,“这几个月来,夫君报国无门、忧心如焚,但对妾身而言,因有夫君相陪,可能是妾身此生最为快乐的日子……”
“夫人何出此言?”李靖笑道,“天下虽乱,但能人辈出,我李靖现在无官无职,怎么能说没有休养生息的日子?我还想多陪陪你和青鸾啊。”
“夫君,你满腹兵法,又遇明主,怎么能偷得清闲?”张出尘道,“夫君的生命,是为平息天下战乱而生,是为苍生福祉而生。天下纷乱如斯,唯有以战止战。从这一点上来说,没有人比夫君更清楚自己的职责。”
“明主?你是说唐王?”李靖问。
“不,是秦公。”张出尘道,“那日秦公前来相救我们一家,我就感觉到这位少年俊杰,身上有一种无坚不摧的力量。唐王虽有肃清天下之志,然而德行只能做霸主,尚不能称为明主。秦公与你有旧,十分看重你,你切不可因其年幼而怠慢了他。以妾身的浅见,不出十年,秦公必为天下之主。”
李靖一惊,赶紧察看门窗,见皆已闭合,才稍稍放心。“夫人,这样的话,咱们夫妻说说无妨,切不可让外人知晓。”
“夫君放心,妾身只对夫君讲。”张出尘道,“我观秦公,龙行虎步,气度非凡。若妾身所料不差,将来平定天下,征服四夷,能与夫君比肩之人,唯有秦公。”
李靖来了兴趣,笑问道:“夫人何以知晓?”
“我观秦公,天赋神武,与你之所学,异曲同工。”张出尘道,“然而更令人敬佩的是,秦公心怀天下,广布仁德,是大乱而大治的贤明之主,其文韬武略,千古一人而已。”
李靖肃容道:“夫人眼力,当真洞悉世态,明察秋毫,是李靖万万不能及的。”
张出尘扑哧一笑:“若无一点眼力,当年怎么会看上你这个落魄书生?”
一句话,把李靖逗乐了。他一把将张出尘抱起,吹灭了蜡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