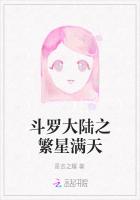我历来认为文学史的分期应该以历史朝代或社会性质划分为好。我主张一般意义上的“中国现代文学”叫“中华民国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中又分为“社会主义时期文学”(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文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文学”(即新时期文学)。前者包括建国“十七年文学”和“文化大革命文学”,后者也可分为两个阶段,从粉碎“四人帮”到1992年左右为第一阶段,叫做“拨乱反正期的文学”,从邓小平1992年的“南方谈话”到现在为第二阶段,叫做“社会转型期文学”。
新时期以来三十年的文学,既有相同的一面也有相异的一面,共同的特征其一是书写改革开放进程,关注社会发展与人的生存;其二是文学意识的繁复多变,审美范式的多样与多型。拨乱反正时期的文学和社会转型期的文学都可以得到佐证。拨乱反正时期的文学以粉碎“四人帮”后,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为目标的新启蒙主义文学为主,有三个特点:一是回归理性,二是呼唤人性,三是社会叙事。社会转型期的文学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形成以商品经济为中心的世俗主义文学,精英文学大都世俗化,通俗文学汹涌澎湃。它的特点,我也对应归结了三点:一是表达欲望,二是凸现娱乐,三是消费叙事。可以看出新时期文学从主导方面说,是由新启蒙主义文学转向世俗主义文学。这两个时期文学尽管前后相连,前者中有后者的萌芽,后者中有前者的延续,但两者的相异之处非常明显。究其原因有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方面,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朦胧诗”“先锋小说”等新启蒙主义文学发生的根本原因。而社会转型期的文学发生的直接原因是90年代初邓小平“南方谈话”后,中国开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商业化大潮逐渐席卷中国大地。由此文坛大兴“新写实主义文学”“新历史小说”“新生代文学”“反腐文学”“女性文学”等。也由此“通俗文学”盛行,占据文坛半壁江山。
我想新时期文学的经验主要有:文学理念相对开放,审美空间相对自由,形式表达相对多样。由于文坛的相对开放、自由和多样,作家创作思接古今,文同中外,学习西方,发掘传统,面向民间,创作空前活跃,成就有目共睹。当然三十年文学也有值得反思的几个倾向:第一是由学习西方导致的文化殖民化倾向。从“朦胧诗”和“伪现代派”开始就有人提出质疑。西方各种思想文化的普泛影响,带来价值观念的偏颇也是事实。虽然有些批评观点未必准确,然而新时期文学在西学东渐的潮流中,确实存在崇洋媚外和食洋不化的殖民化倾向。第二是由继承传统导致的民粹化倾向。文坛学界消解“五四”以来中国对现代性的追求,掀起复古主义浪潮。一些作家的创作过分迷恋倾心于儒、道、释文化,作为救治某些弊端的灵丹妙药。“寻根文学”“新历史小说”等都存在这种倾向。第三是由面向民间而导致的媚俗化倾向。社会转型期带来的市场化商品化,使文学不可抗拒的走向媚俗化,通俗文学显而易见,就是精英文学比如余秋雨的“文化散文”也逃不脱媚俗的指责。
关于文学的“死亡”与新生。我认为,文学的“边缘化”促使文学从非正常的意识形态化向文学的正常本体归位,文学并非“边缘化”,而是确立了文学的自主自立自尊的地位。文学的“死亡”促使文学从小众文学走向大众文学,从小众文化走向大众文化。文学的“泛化”带来的是文学的繁荣。人人都是作家,人人都是读者;人人都是制作者,人人都是消费者。文学成为大众的多样多型的精神享受与文化消费,文学已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我对未来文学抱有积极乐观的态度。我想中国未来的文学应该是:在中国特色的现代文化的主导下,以读者为本,以民族、民生、民权为要义,以创新为基点,吸纳古今文化文学要旨,融通中外审美艺术质素,创作多元、多样、多型的文学成果。
2007年11月
要继续朝“新、短、通”努力
1960年,著名作家马烽写了一篇题为《谈短篇小说的新、短、通》的文章,提倡短篇小说要做到“新、短、通”。所谓“新、短、通”,就是“这些作品大都是描写当前现实生活的;一般说来篇幅都不算长;写得也比较通俗易懂”。这段话概括了50年代中后期山西短篇小说创作的基本特点,也是“山药蛋派”作家短篇小说创作的鲜明特色。马烽同志的这篇文章,在当时产生过积极的影响。今天,要搞好文艺创作,特别是农村题材的短篇小说创作,我们认为,还要继续提倡“新、短、通”。
短篇小说坚持“新、短、通”,是由文学的职能、人们的欣赏习惯和普遍欣赏水平、短篇小说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以农村题材的短篇小说来说,它的读者对象主要是八亿农民,农民很喜欢看到反映自己生活的新作品,他们的劳动是分散的紧张的,他们的文化水平相对要低一些,他们又大都喜欢民族形式和大众化的东西。短篇小说做到“新、短、通”是完全符合农民的实际和需要的。
文学是生活的镜子,时代的声音。我们正处在一个新旧交替、除旧布新的伟大时代,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各个部门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农村更是形势喜人。三中全会以来,党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得到认真贯彻落实,广大农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空前高涨,农村已出现“农家乐”的大好局面。高尔基说,文学是跟着生活的脚步走的。作家处在这样伟大的时代,面临这样壮阔的新生活,必须跟上时代的步伐,反映新的生活,为人民鼓与呼。
短篇小说的优点是能较迅速地反映生活中“新”的东西,能较快地引起社会效应。“新”,要求在内容上“大力表现新的时代,新的生活,新的人物。”只有这样,“才能反映出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精神面貌。只有这样的作品才能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使人们精神振奋,斗志昂扬,鼓舞起人们前进的勇气和胜利的信心”。
文学作品是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文学家首先应该是政治家和思想家。他们对于社会生活,具有敏锐的观察能力,透辟的分析综合能力,能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站在人民群众的利益的基点上,从新的角度,对生活提出独到的新的见解。赵树理就很提倡“问题小说”。他在《当前创作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说:“我的作品,我自己常常叫它是‘问题小说’。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就是因为我写的小说,都是下乡工作时在工作中所碰到的问题,感到那个问题不解决会妨碍我们工作的进展,应该把它提出来。”只有对新的生活提出新的问题,才能有新的看法、见解,不断写出新作品,引起社会的共鸣,满足人们的欣赏欲望。
农村题材的短篇小说首先要反映农村的新变化,农民为“四化”建设而努力奋斗的献身精神和动人情景。塑造各种类型的典型形象,让人们认识、思考、觉醒、奋斗,生活得更幸福,更理想。首要的是塑造社会主义的新人形象。近年来写农村题材的短篇小说,已塑造出一批引人瞩目的新人形象,但远远落后于农村新人的不断涌现,农村形势的发展变化。塑造农村的社会主义新人,既包括在“四化”建设中作出宏伟业绩、重大贡献的英雄,也包括扎扎实实、埋头苦干、默默无闻的普通人,他们都具有新时代的新特点。我们反对那种脱离生活的“高、大、全”的“英雄形象”,坚持一切从实际生活出发,写出有血有肉,使人心服口服的人物形象。占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农民,是我们社会主义的主人。我们应该多写他们,把他们的生活、劳动和情绪生动地表现出来。通过他们,反映出生活的矛盾,展示社会的风貌,辉映出时代精神的闪光。
反映新生活,要求作家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人民是作家的母亲,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作家必须到新生活的海洋中,扎根于农民群众的土壤里,汲取营养,充实自己。必须同农村保持密切的联系,在生产劳动、日常生活中同农民搅在一起,同甘苦共命运,从而理解农民,熟悉农民,懂得农村新时期的风土人情、风俗习惯。
反映生活,还要求具有新的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随着时代的变革,生活的演变,作品内容随之而变,艺术形式也必然引起革新。我们既要继续发扬我国古典文学的优良传统,又要借鉴外国行之有效的艺术技巧和手法,也要吸收姊妹艺术和兄弟流派的长处。生活是以一定的方式存在的,艺术技巧说到底也是源于生活的。要在艺术上有所创新,适应新的内容,就应该尽量做到这几个方面的高度融合,否则,是不会很好地反映生活,教育人民的。对于新的艺术形式的探索、尝试,要充分注意我国的民族传统,不能不顾社会效果而一味追求洋化。写给农民看的作品,更要照顾农民的欣赏习惯、欣赏水平和审美趣味。
短篇小说,毋庸置疑首要的特点就是“短”。当然,不能以篇幅的长短论其思想艺术的成败得失,但毕竟是以“短”为存在前提的,否则就是中篇、长篇小说了。小说的精练、简约,与篇幅的长短、字数的多少,不是不无关系的。郭沫若就曾以“黄金”和“牛粪”为例,强调要写短而有质量的文章。中国历来有写短文章的传统。《古文观止》很少有超过一千五百字的,司马迁和蒲松龄更是写短文的圣手。“山药蛋派”作家们的短篇小说,大部分是短小精悍的。赵树理的《田寡妇看瓜》仅有一千一百多字,非常简短、生动、活泼,内容丰富,蕴藏量大,不失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颗明珠。马烽同志的许多小说,也大都在四千字左右。
就现实而言,人民群众战斗在“四化”建设的第一线,社会处在剧烈的变革之中,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人们希望有更多短小而够味的作品。以前出现的“小小说”和最近出现的“微型小说”“一分钟小说”等,适应了人们的这种心理需要。农村题材的短篇小说,主要目的是为农民群众服务,作者更应设身处地考虑农民的环境,想到他们的生产劳动方式和生活习惯。作品要求文字越简练越好,一切从塑造人物和表现主题思想出发,尽量做到像鲁迅所说的那样,“宁可将可作小说的材料缩成速写,决不将速写的材料拉成小说”。
通俗化,也是个民族化的问题。一个民族的大多数人都看不懂的作品,能说它体现了民族化吗?文学作品,只有做到通俗化、群众化,才能体现出自己民族的特点、风格,才能以此为前提自立于世界文坛,久盛不败。我们必须坚持群众观点,作品写得通俗顺当,让农民群众看得懂。不能脱离农村的实际情况和农民的文化水平去追求洋化。赵树理的成名之作《小二黑结婚》就是非常通俗易懂的,当时在太行山即发行三四万册,在今天还是广为传诵。马烽同志的《张初元的故事》,在通俗化方面也作出成绩,受到群众一致赞扬,获得“七七七”文艺奖金。著名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也是如此。
有人担心提倡通俗化会降低艺术水平,岂知通俗化是为了更好地实现艺术化,两者并不矛盾,应该很好结合。我们提倡的通俗化,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发展而发展变化的,“山药蛋派”的作家就是这样做的。赵树理后期的作品比前期的作品,无论在人物塑造、结构安排、语言运用,还是表现形式和技巧上都有新的进展。比如,《互作鉴定》等小说,就突破了以前表现手法上很少心理描写的局限,而大量采用了心理描写的手法来刻画人物,表现主题。马烽同志后来的书信体小说,第一人称的叙述手法,截取生活中横断面的构思技巧等,都比过去大大迈进了一步,同时做到了通俗化和群众化。
提倡通俗化,要避免出现庸俗化。确实也有一些作品,内容上的因袭化、雷同化,塑造人物的概念化、脸谱化,结构以及表现手法上的落套蹈俗,都不免有庸俗化的感觉。没有通俗化,就没有群众化,也就没有民族化。
我们提倡“新、短、通”,是为了让农村读者喜欢看,看得懂,作用大,达到像赵树理说的“劝人”的目的,使农民逐步认识自己、认识生活,从而改造自己,建设生活。所以,并不意味着排除历史题材、较长篇幅和典雅的作品。我们希望在“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指引下,出现各种不同的艺术风格和流派,进一步繁荣社会主义新文学。
眼下,农村的文化生活远远赶不上农民群众的需求。农村已发生和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农民的物质生活显然逐渐富裕起来了。相比之下,农民的精神生活有闹“饥荒”的现象。短篇小说也为数不多。立志于为农民写作的作家和文艺工作者要创作出更多更好的短篇小说,满足人们的精神生活需求。这是时代的要求,历史的重任,农民的愿望,是文学家的神圣职责。
1981年11月
山药蛋派与荷花淀派的起源
山药蛋派与荷花淀派虽形成于共和国建国初期的五六十年代,但都产生或起源于20世纪40年代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是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体现的文艺思想在中国北方农村结出的硕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