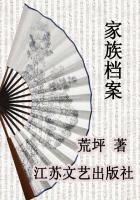儿子毕竟只是刚成人的毛头小伙子,对父亲还是有些惧怕的,但现时被母亲的疼爱包围着,便忘记了弄堂口老王那张铁青的脸,香喷喷地吃起来。
老王在外面溜达着,想着刚才儿子神抖抖地跨下出租车甩着胳膊走过来的样子,越想越生气,一生气,就没有心思散步了,没有心思散步了,他就急匆匆地往回家路上走去。老王回家的脚步很快,坐在弄堂家门口的小板凳上结绒线的张家好婆说:老王介快就回家了?
老王面上露出一个勉强的笑点了点头,脚步不停也不说话。
坐在弄堂家门口藤椅上看报纸的李家老先生说:老王儿子回家了,没心思散步了?
老王面上露出一个更加勉强的笑点了点头,还是不说话。
刚到家门口,老王就闻到一股油烟味,想想中午吃的是豆腐汤,没有开油锅啊。踏进厨房,只见人高马大的儿子正在把碗里的香肠用筷子夹着往母亲嘴巴里送,那碗里,还有黄灿灿的两个荷包蛋。
这一眼,可差不多把老王看得气晕了过去,儿子坐出租车的事情还没有摆平,老婆又自说自话煎荷包蛋蒸香肠。自己连一个荷包蛋也舍不得吃,老婆这一下子就煎了两个,还有,说过多少次了,香肠留着过国庆节的时候吃,死老太婆就是不听,我省吃俭用地,都要被他们这些败家子作践光了!
这样想着,老王的眼神顿时严厉得象两把利剑一样射向老婆。老婆终究是有些怕的,竟然不敢正眼看老王,闪缩着眼神拣起一块抹布擦起了桌子。儿子起先也有些担心,但看到母亲在旁边低头干活大气不敢出的样子,就有些看不过眼,说:爸爸你这又何必,我也已经工作赚钱了,以后我来养活你们也不是什么大事,不要这样逼妈妈。
儿子是从来不敢顶撞自己的,今天居然也和自己较量起来,这是老王万万没有想到的。老婆尽管站在一旁不说话,但分明是一定站在儿子一边的,这么一来,老王就有些势单力薄了。他指着儿子说:你先给我说清楚,回家为什么不坐公共汽车要坐出租车?
儿子干脆有些豁出去地大声说:我一直是坐公共汽车回家的,今天公交车开到半路抛锚了才叫出租的。
老王一步跨到儿子面前,手指头几乎要点到儿子鼻子上:出租车是我们这种人家坐得起的吗?你一天赚多少钱?你说呀!
儿子被老王伸上前来的手指逼得往后退了一步:我和同事合叫了一辆出租车,才起步价,我们每人摊一半车费,我才付了五元。
老王一巴掌拍在饭桌上说:你不能等下一班车吗?五毛的车钱你白白多花了四块五角。
儿子嘟哝着:坐出租也是难得的,这么小气干吗?钱赚来不就是花的吗?我也有工资了,我花的是自己的钱……
老王气得有些发抖,竟然一下子说不上话来。
儿子还在继续着:爸爸你的老脾气好改一改了,我看你是有了一百万也舍不得坐出租车的,你去大街上看看,谁还象你这样一顿饭只吃一个豆腐汤的?现在国家号召多赚钱多消费,你也该去市面上领领行情……
小孩子要么被老子吓得不敢出声,一说话却是这样没大没小不分轻重,这话可真把老王气得不轻。老王截断儿子的话,厉声吼道:你懂个屁!
吼完对着老婆骂到:你这个死老太婆,你看看吧,都是你宠出来的,我不管了!
一扭头朝家门外走了,咚咚咚的脚步声在弄堂里回荡了很久也不散去。
大街上的人群熙熙攘攘,小贩子的叫卖声,踏三轮车的吆喝声此起彼伏、连绵不绝。人行道上不断地钻出几个脏脏的小孩,缠着老王问要不要擦皮鞋。老王挥手赶开那些小孩,心烦气乱地粗声喘息着,胸口有些隐隐作痛。老王低着头走路,看见自己脚上那双已经很有一些年代的皮鞋,因为好久没有擦,蒙了一层白灰,显得更为破旧。再看路边,还真有人坐在藤椅上或闭目养神或看风景,一边让那些小孩擦着皮鞋。
活了五十九岁的老王忽然有些悲伤,从小到大,老王几乎没有穿过皮鞋,今天的这双皮鞋也已经穿了有八年了,前八年,这双皮鞋是只能在做客喝喜酒的时候才出现在老王脚上的,直到过年的时候儿子给买了一双新的,老王才舍得经常把这双旧的穿在脚上。
老王想想自己那样俭省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儿子?自己是浴室里的钎脚工,虽说一样工作一样拿工资吃饭,终究让人看不起,老王不希望儿子将来也和自己一样没出息,因此,老王把一分一毛节俭下来的钱给儿子存了起来,至少,老王要让儿子讨上老婆,体体面面地娶进一房媳妇。
可是儿子竟然那样不理解自己,说自己逼老婆,说坐出租是花自己的钱,还说要多赚多花,这于老王来讲,实在是一件十分委屈的事情,做了一辈子钎脚工,终年捧着那些臭脚丫子伺候别人,低头哈腰做牛做马,临到老了,连钎脚工的活都要给年轻人抢了去,哪里还有多赚钱的机会?没有了赚钱的机会,哪里还能说什么多消费的话?想起这些,老王就伤心,再看看坐在街边藤椅上那些抬起脚让人伺候着擦皮鞋的人,越发地觉得自己怎么就活得那么窝囊。
钎脚师傅老王给别人钎了一辈子脚,自己的脚却从未让人伺候过,想到这里,老王顿时倍感冤枉,眼睛里几乎要掉出一些咸涩涩的水来。正在此时,一个半大男孩背着个擦鞋箱追了上来。
爷叔你擦鞋吧,很便宜的,包你满意!
老王回头看了一眼这个脏脏的男孩,想起自己在浴室里也是这般低头哈腰,询问客人要不要钎脚,恻隐之心加上肚子里窝的那股子火,于是,竟然跟着那男孩子走到了一只棕色的藤椅边坐了下来。
男孩把老王的一只脚托起来轻轻放到木架子上,擦净鞋面上的灰,挤上鞋油,用刷子涂开黑色的油膏,然后再换一只脚同样涂上鞋油。接着,男孩从箱子里拿出一块布条子,在老王的皮鞋上开始来回擦拭起来,速度很快,但却没有把鞋油染到袜子上一点点,动作娴熟到让老王觉得这样的擦拭尽管是在擦皮鞋,但腿脚却感到放松惬意之极。老王搁着脚让男孩擦着,一边心里就感慨起来,一直以来是自己伺候别人的,第一次花钱让别人伺候自己,怪不得那些老板总经理喜欢桑拿按摩和钎脚,原来这被人伺候的感觉的确是相当不错的。
老王眯着眼睛看着大街上匆匆赶路的人流,再看看自己这么人模人样地坐着,很有些派头的样子,心头的气就稍稍地消散了些。二十分钟后,男孩抬起头说:爷叔,擦好了。老王低头看,原来破旧的皮鞋,被这么一弄,旧貌换新颜了。老王登着这双锃亮的皮鞋,顿时也年轻神气了不少,脸上的皱纹也似乎舒展了好些,怪不得都说人靠衣装佛靠金妆。可不知道擦这样一双鞋要多少钱,刚才一生气忘了问价钱了。
老王对男孩说:鞋擦得挺好,要多少钱啊?
男孩伸出一根食指说:一块钱。
老王以为自己听错了,现在这世道,一元钱还能做什么?擦一双皮鞋只要一元,自己为客人钎一双脚起码也要收十元,看来,这世界上比自己活得辛苦的人多得多呢。
比起擦鞋男孩来,老王觉得自己简直就是大富翁了,他从衣袋里掏出两个一元的硬币给男孩,男孩子说:爷叔,一共一元,不是每只一元。
老王说我知道,那一元是给你的小费,奖励你擦得好。
男孩子连连道谢,老王心里徒然膨胀起一股豪气来,摆了摆手,抬头挺胸神情自若地站起身,抬脚离开。他记得给那些老板钎好脚后,他们也是那样给一点小费,然后在自己的千恩万谢中神气活现地离开浴室的。
老王似乎忘记了出门前和老婆儿子的怄气了,他登着闪亮的皮鞋,气宇宣昂地走在大街上。今天,老王算是让人家给伺候了一回,也给了人家小费了,这就是做老板的感觉,原来做老板这么简单,从小教育儿子“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其实做人上人也不难啊!
老王边往家走边想着,一歇歇时间就走到了弄堂口的菜场。拎着小菜篮头的张会计远远地看见老王走过来,撩一下那头齐耳革命短发,笑呵呵地叫着他:老王啊,侬今朝嘘头好来,一双皮鞋锃锃亮,跑亲眷去了吗?
老王冲张会计笑笑说:没有没有,买小菜去,买小菜去。
老王有些不好意思地缩了缩那双亮闪闪的脚,避开张会计,转身进了菜场。想着干脆就把晚饭的小菜买好了吧,就径直地往豆腐摊子走去。老王是习惯于向着豆腐摊子走的,这豆腐,便宜又好吃,营养又好,价廉物美的好东西。老王走近摊子,老板就说:老王,老规矩,称一块钱的豆腐吧?
老王点头,手伸进口袋摸钱,袋袋里本来有三个硬币,可现在,只有一个了,把这一个硬币交给豆腐老板,口袋里就空了。那两个硬币,本来是明天一日的菜钱,现在让自己擦皮鞋擦掉了。要是光擦皮鞋也只要一块硬币,可老王给了人家小费,这一块钱小费给掉了老王明天晚饭的菜钱,这样一想,老王的心顿时揪了起来,那两个硬币,毕竟是两元钱呢,刚才自己怎么就不把那钱当钱了呢?
豆腐老板说:老王豆腐要称吗?
儿子从出租车车门里跨出来时那副大大咧咧无所谓的样子和他碗里那两个黄灿灿的荷包蛋又出现在老王眼里,脑门轰地一下再次热了起来,豆腐老板见他发呆,大声吆喝着:老王,一块钱豆腐还要不要啊?
老王醒觉过来,一跺脚说:不要了,今天晚上我喝西北风去!
说着一扭头,走了。
为了那回擦皮鞋的两块钱,老王心疼了三天,那几日,老王招揽客人钎脚特别卖力,好似在拼命赚回被人伺候后白白扔掉的那两个硬币一样,当然,还有儿子坐出租车花的那些冤枉钱,老王一样要去赚回来的。
老王还是老王,偶尔擦一次皮鞋,那仅仅是偶尔而已。老王的皮鞋更多时候是灰尘仆仆地套在他那双脚上的,每天,他就穿着这双布满灰尘的旧皮鞋离开家,走出弄堂去浴室上班,见到结绒线的张家好婆和看报纸的李家老先生打个招呼,下班了,走同样的路回家,拐进菜场买一块钱的豆腐或者白菜,日子过得依然节俭,可他并不在乎这些,他家的水电费依旧低得所向披靡、无人匹敌。张会计,自然也已经放弃了与老王的竞争,任由老王一个人自己较真着过自己的小日子,这种日子倒也是自得其乐的。
老王的日子,是别人学不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