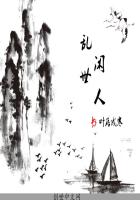“父王,是你让人捉住银麟母亲的吗?”菲尔开门见山地问道,她的脸部轻微地抽搐着,看起来十分激动。
帝焰王不紧不慢地站起身子,双手背在身后,走到窗前,轻轻挽开窗帘。
窗外,通向凤凰要塞的王者之道上,错列有序地散布着巡逻的卫兵和零零星星的清道夫。他的鼻息变得沉重起来,眉头也稍稍皱起。“难道父王作什么决定,还要先取得你的批准?”他缓慢而有力地说道。
菲尔往前两步,“不,”她说,“只不过,那是银麟的母亲啊。父王既然把银麟的母亲带来凤凰城,就该命人悉心照料啊。然而,前些日子若不是我,身有肺疾的她不知道要过得怎样痛苦,而如今,父王却又命人把她带走,这恐怕……恐怕有不妥……”
帝焰王转过身来,严肃而认真地瞪着身前急切万分的菲尔,一脸的失望。
“银麟的母亲,又关你什么事?银麟不过是雷洛的随从,更何况,身为重刑犯的他,还在被通缉,我又有什么义务替他照看母亲?”
“被通缉?父王不是已经决定撤销对他的通缉了吗?”菲尔想起前些天从卫兵那里打听到的消息,而仅仅是这样一条简单的信息,便让她为之开心了一整个晚上。而如今,父王嘴中所说的,则完全颠覆破灭了预期中的希冀。
帝焰王轻轻地摇了摇头,“孩子,你要知道,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他略一停顿,一连串早已准备好的说辞,像是上好了发条般在嘴边就绪,“你我都知道,他便是当日刺杀夜羽王的人,尽管未遂,却也是战争的主要起因之一。更何况,如今雷洛被俘,也是他的失职。”
“哥哥被俘?”菲尔一时间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她甚至宁愿刚才听到的只是幻觉,“怎么可能?”
帝焰王紧张的双眉松弛下来,颓然而又无奈地点了点头。他步伐沉重地走到沙发上,坐了下来,像是在让紧张的神经得以舒缓和放松。他闭上双眼,拇指和食指扶在鼻翼两侧,轻柔而富有节律地上下揉捏。“雷洛他,是被抓去了。帝焰国之所以没有选择将此公之于众,是担心影响了军心。”
像是被一道晴天霹雳击中了一般,刚才还一脸怨气的菲尔,此刻却如同没了方向的小鸟,茫然无助地站在那里。她一声不吭,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不知道还有什么可以继续往下说。
“回去吧,孩子。让为父冷静一会儿。”帝焰王沉下了头,深深地叹了口气。
过了几秒钟后,通向长廊的房门方向便传来了清脆的开启、闭合声,还有菲尔离去的脚步声。
“出来吧。”随着帝焰王的一声呼唤,起居室连同卧室的房门也传来声音,与之相伴的,是鞋跟“喀哒、喀哒”触碰地板的声响。苏菲娜步态婀娜地走到了帝焰王的身边,慢慢坐了下来。
“哟,看来是小公主生气了哦!”苏菲娜一边口气轻佻地评论着刚才所听到的内容,一边用手抚摸着帝焰王宽厚的前胸。而此时的帝焰王,则像是变了个人似的,全无了刚才的懊丧和愁闷,反倒是一副悠然的快活嘴脸。
“那又有什么办法?翡翼的兵败对帝焰军的打击如此之大,我又怎能坐视不理?”他扬扬自得地捋着长须,微眯的双眼,仿佛在散发着狡黠的光。
苏菲娜略一斟酌后,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原来如此,果然是步步为营,一石二鸟。”她自顾自地感慨着,像是洞察出了什么。
“哦?”帝焰王颇为好奇地端详着身旁的苏菲娜,“你难道又看穿了我的心思?”
苏菲娜轻声哼笑着,妩媚的姿态尽显无疑,“帝焰军大败翡翼城,军心急需大振。陛下一方面准备以银麟母亲诱出重犯银麟,以他祭旗,鼓舞军心。
另一方面,误导菲尔雷洛被俘,其一可以让她转移注意力,其二是为进一步控制菲尔的活动做铺垫,以此来为杀死银麟扫清障碍……如此精妙的布局,简直是,绝妙!”
帝焰王毫不收敛地哈哈大笑起来,一把将苏菲娜揽在怀里,“当今世上,能把我看穿的,也只有你了!”
苏菲娜温柔而驯服地依偎在他的怀里,内心的算盘悄然打好了最后一粒算珠。
自从阿瑞斯的事情过后,费多便像是遇到了魔障一般,成日身居家中,与世隔绝。尽管表面上如此,然而真实情况却并非大多数人所想。
此刻的他,正斜倚着沙发,自斟自酌着。酒瓶扔了一地,立着的、倒着的、空着的、满着的……各式各样。
他的脑海中时刻回想着同一句话,“回家,等我,这一次哪里都不许去,否则……”正是这句未完结的话,让不可一世的他举步维艰、寸步难行,只得回到凤凰城后,于家中郁郁终日。就连领兵出战这等事情,都要一并拒绝。
“可恶。”他将酒瓶中的最后一滴倒入口中,掂了掂后,将酒瓶重重地砸向墙面,“哐啷”一声响,酒瓶散作一团碎片。他的嘴里依然咒骂着,然而,即使肮脏污秽的字眼从他的嘴里倾泻而出,他的郁结却依旧越来越严重。
“凭什么,凭什么那个该死的黑袍家伙的一句话我就要听!他不就是给了我一块破石头么!”站起身来,醉醺醺地走到酒柜前,顺手又拿出一瓶来,指肚轻轻一弯,便将酒瓶密封的瓶盖轻易推开,大口大口地痛饮起来。
就在他喝得起劲时,黑袍在扭曲的空气中出现在了偌大的起居室中间,纹丝不动地盯着眼前俨然成为醉汉的费多。“怎么?几日没来看你,就这德行了?”
“哼!”费多负气地扬起头来,继续饮酒。
“呵呵……”黑袍发出尖锐的笑声,难听至极。“明天你就可以出门了。”
他像是在宣布一个巨大的恩惠一样,语气之中都掺杂着布施恩泽的味道。
“说吧。”费多将手中的酒瓶一饮而尽后,眼圈通红地看着黑袍,等待着对自己来说,不知是好是坏的新任务。
“洛珈马自从帕斯托鲁后,就一直没立新王,时隔不足百日,他们终于打算拥立新王,而新王,则由半个月后,在洛珈马盛会的最终胜者来担当。”
“你是让我……去当洛珈马的国王?”费多问。
黑袍发出赞许的笑声,像是在褒奖费多的心领神会。“没错。更何况,洛珈马对你来说,应该也有另外一番意义。”
“不用你说我也知道,你就干脆等着我称王吧。”他随手扔掉手中的空瓶,旋即一个挥手,一道火光骤然包围起那透明的酒瓶,而下一个瞬间,酒瓶就连同火苗一同消失在了空中……4{帝焰国·王都·凤凰城}
三天后。
浩浩荡荡的军队,井然有序地从凤凰城门一点点向外驶出,声势浩大。
壮行的呼喊声不绝于耳,这一方面源于凤凰城居民自古以来对英雄的向往和崇拜,而另一方面则是源于对战争尽早结束的企盼。
银麟匍匐在一处隐秘的山丘,以树丛为掩护,远远地观望着军队出城。
对他来说,这样的一幕场景让他很是费解。一来,毕竟由于辛德梅尔和堪萨斯军的存在,凤凰城的皇家军队还从未出征过;二来,若要带领皇家军队,那必然是帝焰王,御驾亲征这种事情,以他对帝焰王的了解,恐怕怎样想都是难以成行。不过,这些困惑对此时的他来说,只能搁置一边。他的心里,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带着他那被帝焰王软禁起来的母亲远走高飞。
时间和耐心互相拉扯着,随着最后一个兵卒从城门中走出,银麟总算是舒了一口气。他缓缓站起身来,如一阵疾风般,轻盈地飞掠过城前的平原草野,一瞬间便来到了城门的一侧。
巍峨的凤凰城城门高耸、宽敞,却只有两名卫兵把守。这样的安排并不是由于疏忽或者大意,而是因为过了大门以后,还要经过几十余米、纵贯护城河、且有卫兵把守的石桥,才能到达内城,而内城的门,则颇为窄小,只容六七人并行,高度也只有一层楼的高度。这样的“双保险”给了帝焰国的人足够的自信,让他们有理由相信凤凰城足以拦阻不速之客。
银麟背身倚在城墙上,一点点向城门的方向挪动着。门前的卫兵不知道正颇有趣味地谈着什么,丝毫没有注意到银麟的存在。他抓准时间,腾身一翻,须臾间突破了第一道防卫,潜伏在了大门内侧的阴影里。
“不好啦!”门外传来了卫兵的呼喊声,银麟屏住呼吸,攥紧双拳,蓄势待发。然而,透过城门与城墙的间隙,他所看到的后续,却着实让他松了口气。
“我的金甲大王找不到了!刚才那阵阴风哪里来的啊!赔我的金甲大王啊!”卫兵甲“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哭爹喊娘地寻觅起来。
“哈哈,我看你是骗人的吧!什么金甲大王、银甲小鬼的,就算是铁甲小宝也没我的大元帅厉害!”卫兵乙挥舞着手中装蛐蛐的盒子,一副小人得志的模样。银麟不屑地吐了口气,转身继续前行。
菲尔走在军队的最前面,一脸阴郁。她将挂在胸前的坠饰取了出来,攥在手心里,仿佛祈祷着什么,然而她心中的矛盾,却丝毫没有因为她的祈祷而削弱。她的脑海里不断回响着同一段对白:
“你是怎么得来这个的?”
“你无须知道,你只需要选择使用与否。”
“我不能……请你拿回去,将它还回它本应存在的地方。”
“哈哈哈哈,傻孩子。若你不使用,它必为他人所用,到时候的后果,我可不敢向你保证什么。”
她把手摊开,墨色的魂晶像是新生的婴孩一般,卧在她的掌心中。
“我这么做,对吗?”她一边喃喃着,一边将魂晶放回领子里。旭阳初上,晴空一碧万里,温煦的微风拂过草野,草叶摇曳的“沙沙”声,却早已湮没于行军的脚步声中。
{夜羽国·王都·霜月城}
休德迦系好了战甲上的最后一粒纽扣,然而他的面部表情却在告诉大家,他的内心并没有像他的装备一样做好了准备。鲜有的担忧,出现在他那张冰山脸孔上,格外不搭调,就连坐在一旁的笛妃都这么觉得。
“你还有机会反悔。”笛妃叹了一口气,说道。
休德迦摇了摇头,一本正经地说:“帝焰国大军将至,我又怎么会在这时出尔反尔?”
笛妃双手抱在胸前,蓦地站起身来,身上的佩饰叮当作响,“你怎么就知道过会儿兵临城下的不是堪萨斯将军?”
“如果我不知道他会来,我也不会留在这里。”他进一步解释道,“父亲是个正义感极强的人,倘若由我来阻止他,帮他理清真相,兴许整个战局都会迎来转机。”
笛妃思忖着休德迦的话,觉得言之有理,便不由自主地连连点起头来。“我去求莫里大哥,让我跟你一齐出战,也好相互有个照应。”说罢,她便朝门前走去。
“我以为,莫里先生是不会让你去的……”笛妃刚要伸出去开门的手缩了回来,转过身来,一副不明所以的表情,休德迦继续说道,“莫里之所以不允许你参加之前的那些战役,目的已经很明确,就是保证你的安全。那些所谓的夜羽王牌、救命稻草之说,不过是对你施用的缓兵之计罢了。”
“什么……”笛妃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心里虽然有被糊弄后的不甘,却也马上就理解了莫里的良苦用心。毕竟与莫里对夜羽的付出相比,笛妃的牺牲只是沧海一粟,又有什么资格去指责莫里的选择呢。
休德迦走到门口,“我先走了,你保重。”当他伸手去拉门把手的时候,腰间传来温柔的触感,是一双纤细的手臂,从身后将他搂住。
“答应我,一定要平安回来。”笛妃将脸颊轻轻地贴在他的后背上,轻柔的声音像是温热的泉水般沁入他的胸腔,蔓延进他的血脉,整颗胸腔仿佛都在沸腾。
“好,我……答应你。”他的心脏扑通扑通地直跳,面红耳赤的他,此刻竟像是一个受到褒奖的腼腆小孩。
笛妃的双手从他的腰间缓缓滑落,“保重……”
她一路目送着他远去的背影,直至他消失在长廊的尽头。
当距离霜月城只有十余里的路程时,堪萨斯下令停军,进行着最后的整顿。
休德迦叛变的消息,刚在不久前传至堪萨斯军。令人意外的是,堪萨斯对此事的反应并不强烈,甚至还不如军中的其他士兵激动愤慨。
此刻的堪萨斯,正盘膝坐在一块巨大的磐石上,饮着水。壶中的清泉水已在风雪载途的行军中冻得冰凉,甚至结满了冰碴。他回过头去,上万人的大军如同蜿蜒的长蛇般,一眼望不到尽头。冰天雪地尽管让路程变得漫长而艰难,对堪萨斯军来说,这些都不在话下。然而,堪萨斯的脸上却时而显露出忧愁,凹陷的皱纹在风雪中愈加沧桑地呈现。
他轻轻抚摸着肩上的剑伤,伤口除了轻微的刺痒外,疼痛感已然全无。
至此,他站起身,挥手示意大军出发,不消几秒,全军便整装待发,再次上路。
苍茫的风雪之中,霜月城的轮廓,宛如海市蜃楼一般若隐若现。目之所及的一片皑皑中,正飞旋着累世的冰屑和雪雨,透着彻骨的寒。而那凛冽的风,在苍茫无际的白野里,仿佛正奏响着献给末世的悲怆挽歌。
{帝焰国·王都·凤凰城}
银麟双手扒在石桥的底部,一点一点地向凤凰城内城的方向移动着。在这之前,他已经等待了许久,直到卫兵一齐背过身去的片刻,他才觅得机会。
只要再过了桥前的石拱门,便能顺利地进入到内城,目的地在望,银麟加快了速度,双手双脚交替着伸缩,尽管一个失手就会令他掉入护城河中,他仍然保持着很高的频率。
终于,他到了石桥的尽头,他单手扣住桥墩,轻轻一荡,身子便平移到了陆地的边缘。他的手指紧紧地扣在绿地上,生怕多露出一点头皮就会被人发现。而他的身前,则是几乎没有斜度的峭壁,直通护城河底。
泥土嵌入他的指甲,拉扯得生疼,但愈是疼痛,他便多用一分力。生怕自己的一时脆弱,浪费了自己的努力。他咬着牙,拼命地坚持着。
正在这时,一只飞鸟呼啸着从天空中飞过,银麟没有犹豫,抄起草堆中的石子便朝飞鸟掷去,随着一声凄厉的鸟鸣,飞鸟如同一颗急速坠落的陨石般,狠狠砸入护城河里。
嗅觉敏锐的卫兵们,自然不会放过这点风吹草动,他们纷纷向银麟所在位置的反方向跑去,想一探究竟,直到发现不过是飞鸟变成落汤鸡的戏码,才一脸丧气地重归岗位。殊不知,在他们凑热闹的当儿,银麟早已潜入了内城。
今天的内城,氛围似乎有点不太对劲。原本刚刚还在夹道相送出征军队的人们,此刻都不知道去了哪里,街道上,虽然仍有行人来来往往,比起往常,却显得有些过于冷清。甚至连理应热闹的集市方向,都没了往日嘈杂的动静。
他以右手遮在嘴前,佯作咳嗽的样子,走到了一个行路老妪的跟前。“这位夫人,能否告知,城里发生了什么事?”
老妇人转过脸来,粗略地打量了一下咳嗽不止的银麟,脸上并未露出什么异常的神色,“哦……你是问,城里发生了什么事吗?哎哟,发生了那么大的事情,你这个小伙子居然都不知道哟!真是不应该、不应该,按理说年轻人……”她自顾自地喃喃起来,银麟根本无法理解她在说些什么,他礼貌地点了下头,转身便要走开。身后传来了老妇人的叫喊声,“喂喂喂,小伙子!你回来!你刚才问我发生了什么,是吗?”
看到银麟转回身来,老妇人倒颇为不好意思地朝他笑了笑,“帝焰王出兵的消息,你应该知道吧?你们年轻人的消息,应该比我们灵通的。”
银麟想起刚才在山丘之上所看到的画面,点了点头。“帝焰王为什么要御驾亲征呢?”尽管,他并不寄望于眼前这个有些糊涂的老妇人能够回答他,他还是把问题付诸言语。
老妇人连忙摆手,“哎呀,不是不是,小伙子看来消息还真不够灵。”
她有些得意地笑了笑,大概是在为自己的“与时俱进”沾沾自喜,“领兵的是帝焰国公主啦,就是那个很漂亮的公主。”老妇人手舞足蹈地比画着,银麟却像是窒息了一样,六神无主地立在了她的身前,一动不动,像是灵魂出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