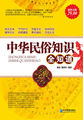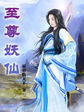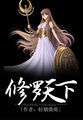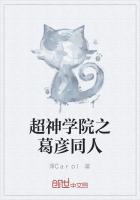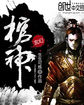东汉以来,中国南方,即在今湖北、湖南、四川、广东、广西、安徽、江西境内,散居着被统称为“南蛮”的一些少数民族和部族。到南朝时,“南蛮”名称虽然繁杂,但从分布来看主要是蛮、俚、僚、傒四族。
先来看蛮族的分布。
南朝蛮族的分布,除今湖北、湖南全境外,还包括四川、河南、安徽、江西的部分地区,大约计有:
峡中蛮,居四川、湖北之间。《宋书·沈攸之传》中有“巴东(今奉节东)、建平(今巫山)为峡中蛮所破”,其后攸之“遣军入峡讨蛮帅田五郡等”的记载;《梁书·阴子春传》中有梁秦二州刺史阴子春曾“讨峡中蛮,平之”的记载。
丹淅二川蛮,居河南、陕西、湖北交界处。《宋书·张邵传》中有“丹浙二川蛮屡为寇”的记载。
雍州蛮,居湖北沔水(今汉水)两岸。《宋书·沈庆之传》中有“大破缘沔诸蛮”的记载;《末书蛮传》中有“随王诞又迟军讨酒北诸蛮”的记载;《南齐书·高帝本纪下》中有元嘉十九年“文帝遣太祖领偏军讨沔北蛮”的记载;《南齐书·张敬儿传》中有“伐襄阳诸山蛮”的记载,凡此等等记载很多。
荆州蛮,居湖北境内长江两岸及江北的沮水、漳水之间。《宋书·蛮传》中有“江北诸郡蛮所居”和“南郡临沮(今远安南)当阳蛮反”的记载,《南齐书蛮传》中有“汉阳(今远安西北)本临沮西界,西北接梁州新城,东北接南襄城,南接巴、巫二边,并山蛮凶盛,据险为寇贼”的记载。
西阳蛮,居湖北东部的五水流域。除《末书·文帝本纪》中有“江州刺史王骏统众军伐西阳蛮”的记载外,在《宋书·沈庆之传》、《宋书·柳元景传》、《南齐书·刘怀珍传》等均有攻打西阳蛮的记载。
湖阳蛮、南阳蛮,居河南西南。《南齐书·张敬儿传》中有“击湖阳(今唐河县南)蛮”,“南阳蛮动,复以敬儿为南阳太守”的记载。
弋阳蛮、汝南蛮,居河南东南,弋阳即今潢川县西,汝南即今汝南县。《宋书·殷琰传》中有“弋阳西山蛮田益之起义”的记载;《宋书·臧质传》中有“伐汝南西境刀壁等山蛮”的记载。
晋熙蛮、庐江蛮,居安徽西部晋熙(今潜山)、庐江(今舒城)两县。《宋书·蛮传》中有“晋熙蛮梅式生亦起义,斩晋熙太守”的记载;《陈书·宣帝纪》中有“台州庐江蛮田伯兴出寇枞阳,刺史鲁广达讨平之”的记载。
江州蛮,居江西九江一带。《南齐书·曹虎传》中有“江州蛮动”的记载;《宋书·庾悦传》中有“寻阳接蛮”的记载。
湘州蛮,居今长沙一带。《南齐书·柳世隆》中有“湘州蛮动,遣世隆以本官总督伐蛮众军”的记载;《南齐书·吕安国传》中有“湘川(川为州之误)蛮动,安国督州兵讨之”的记载。
莫徭蛮,居湖南零陵、衡阳等地。《梁书·张缵传》中有“州界零陵、衡阳等郡,有莫徭蛮者,依山险为居,历政不宾服,因此向化”的记载。
巴陵蛮,居今湖南岳阳。《梁书·太祖五王传》中有“巴陵马蛮为缘江寇害”的记载。
凡此种种,归纳起来南朝蛮族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据称为“盘瓠之后”,崇拜犬图腾的“荆、雍州蛮”。他们在东汉时主要居住于湖北西部与湖南西部交界的武陵地区,故又称为“武陵蛮”;“至晋之末,稍以繁昌,渐得北迁”,至于荆州(今江陵)、雍州(今襄阳),故史称“荆、雍州蛮”。另一类是据称为廪君后人,由东汉时的江夏蛮演变而来的,祟拜白虎图腾的“豫州蛮”。由于西阳蛮是其核心部分,而西阳郡又包括在东晋侨治的豫州范围之内,故史称“豫州蛮”。其分布范围比较广,《宋书·蛮传》云:其“北接淮、汝,南极江、汉,地方数千里。”
蛮族人口据有关史料的祖赂统计,约有140万左右。正如史书所说,北齐时豫州境内“蛮多华少”,蛮人输租赋的有“数万户”。刘宋王朝镇压蛮人,“系颈囚俘,盖以数百万计”,其言虽过其实,但仍可见蛮族是南朝人口最多的一个少数民族。
次看俚族的分布。
俚族,本称“里”;而“里,蛮之别号,今呼为俚人”。故《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中所提之珠崖儋耳、交趾、九真、日南、合浦的“蛮里”;日南、象林的“蛮夷”,九真缴外夜郎的“蛮夷”;苍梧的“蛮夷”;郁林、合浦的“蛮汉”;交趾、合浦、乌浒的“蛮”等,均为俚人。
俚族主要分布在岭南地区。东汉时,岭南交州的南海、郁林、苍梧、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七郡,除南海郡外,其余六郡都有俚人。南朝刘宋时的广州包括南海、苍梧、晋康、新宁、永平、郁林、桂林、高凉、新会、东官、义安、宋康、绥建、海昌、宋熙、宁浦、晋兴、乐吕等18郡,都是俚人的分布区,故《宋书·夷蛮林邑国传》云:“广州诸山并俚、僚,种类蟹炽”。此外,湘州的南部也有俚人,《宋书·良吏·徐豁传》载,徐豁为姑兴太守,表陈三事,第一件说到剥削太重,“年及应输,便自逃逸,既遏接蛮、俚,去就益易”;第三件说到“中宿县俚民课银”问题。始兴郡则属湘州。
俚族人口,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记载,仅东汉末被称为“合浦蛮里”的台浦乌浒人,一次“内属”就有十万余而“开置七县”,即高凉郡。可见俚族是岭南地区最主要的一支少数民族。
再看僚族的分布。
僚族是由汉代的板循蛮以及一部分巴人和濮人溶合而形成的,后由南向北迁移,到魏晋时已分布在北至陕西汉中、甘肃南部,西及建南高原、岷江上游,几乎遍布整个四川盆地,故《华阳国志·李特雄寿势志》云,僚人“自巴至犍为、梓渔,布满山谷”。《魏书·獠传》亦云:“自汉中达于邛、笮,川洞之间,所在皆有”。
僚族人口,益州部分的布在山谷,十余万落;梁州问他的约20万户。以1落为1户,1户5口计,僚人共约30万户,150余户万人。
最后看傒族的分布。
傒族,南朝时亦作“溪”族,是与东北的奚族完全不同的一个南方少数民族。其主要分布在鄱阳、庐江、豫章、始兴等郡,即今江西赣水流域一带。历来学术界对傒族论及甚少,其实魏晋南北朗时傒族中出了下少名人,仅东晋南朝的将帅就有陶氏、胡氏、黄氏、周氏、余氏、熊氏、侯氏7姓10人如着名诗人陶渊明的祖先,东晋名将陶侃就是鄱阳郡的傒人,胡杨晖称之为小人,温峤嘲之为溪狗。又如南齐将军胡谐之就是豫章南昌的傒人,“上方欲奖以贵族盛姻,以谐之家人语傒音不正,乃遗宫内四五人往谐之家,教子女语。”
这样,在整个南朝,蛮、俚、僚、傒等族分布在东起安徽.西北达陕西,南到广州,西极四川的广大地带,涉及了南朝的大部分地区。南朝国家掌握的最多人口数,据《宋书·州郡志》记载是大明八年(公元464年),人口数为546万多。而蛮、俚、僚、傒四族人口的极不完全的统计,人口数共约300万人左右,占了南朝国家掌握的总人口的一半以上。
二、汉民族向南方的大迁移
东汉末年以来,当北方少数民族和部族掀起了向内地大迁移的运动之时,北方的汉族人民也开始了向南方的大迁移。
北方的汉族人民为何要向南方大迁移呢·前已提及,东汉以后,中原大乱,从黄巾大起义开始,经三国鼎立的分裂。十六国的混战,直到南北朝的对立,在蔓延全国的大变乱之中,在国家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下,田园既停止了生产的机能,战乱又增加了人民的恐饰,特别是北方少数民族相部族的大规模内迁,十六国的大混战,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交织在一起的时候,故乡虽好,但却变成了难居之地,汉族人民为了生存,也开始向四处迁移逃亡,正如古语所云:“老弱转诸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而当时相对来说变乱比较小的南方,由于甚少北方兵燹之灾,加之地广人稀,历来政府控制不严,所以成了汉族人民迁移的主要方向。
汉族人民大规模的南迁,在汉魏之际,中原大动荡时形成了第一个高潮。
首先,东汉末年黄巾起义,中原开始动乱,汉族人民纷纷避难江南,史载:
沛郡人桓晔,献帝“初平中,天下乱,避地会稽,遂浮海客交趾”。
汝南人袁忠,献帝初平中客会稽上虞,“后孙策破会稽,忠等浮海南投交趾”。
汝南南顿人程秉,“避乱交州”。
沛郡竹邑人薛综,“少依族人避地交州”。
《释名》的作者,北海人刘熙也及往交州,曾为程秉、薛综的老师。
苍梧广信的士燮,其先祖于两汉之际从山东迁来,因“谦虚下士,中国土人往往避难者以百数”。
顾野王《舆地志》云,“葛姥者,汉末避黄巾贼,出自(至)交趾,于此筑城为家”。
黄巾起义失败后,中原地区的汉族人民更是大量逃亡,除部分向西、向北外,主要是向南。南移的汉族人民以益、荆、扬三处为集结点。大约关中一带的人,多移往益州和汉中,《后汉书·刘焉传》就说:“初南阳三辅民数万户流入益州”。《三国志·魏志·张鲁传》也说:“韩遂、马超之乱,关西民从子午谷奔从者万家。”关中一带的人移入荆州的也很多,《三国志·魏·卫觊传》说,“关中膏腴之地,顷遭荒乱。人民流入荆州者十万余家。”诸葛亮就是从山东琅琊避难移入荆州的;鲁肃则因“中州扰乱”而率男女三百余口南徙江东的。徐州及淮河流域的人则多移入杨州,《三国志·吴志·张昭传》即说:“汉末大乱,徐方士民多避难扬土。”山东青州的人也有移徙扬州的,琅琊阳都人诸葛瑾“汉末避乱江东”。凡此等等,更是不胜枚举。
汉族人民大规模的南迁,在西晋永嘉之乱以后,又形成了第二个高潮。
西晋虽然使中国暂时得到了统一,但随之而来的“八王之乱”给中原人民又带来了新的灾难,长达十六年的兵祸战乱,使田园荒芜,屋宇倾记,天灾凶年接踵而来,中原人民或死于血泊之中,或流离失所。更不幸的是祸不单行,“八王之乱”招致的“永嘉之乱”,由于具有民族斗争的性质,入主中原的匈奴人刘聪和羯人石勒等率领部众,大肆屠杀汉族人民,尤如雪上加霜。永嘉七年(公元313年)刘曜攻陷洛阳,纵兵屠杀焚掠,洛阳化为灰烬。中原的汉族人民在这种残酷,血腥的民族斗争面前无法忍受,别无它择,只有向比较安定的江南逃亡。史称“永嘉之乱……幽、冀、青、并、兖五州及徐州淮北流人,相率过江淮。”又称“胡寇南侵,淮南百姓皆渡江。”《晋书·王导传》亦云:“洛阳倾臣,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由于南方不少地方“地广人稀,且少陂渠,田多恶秽”,南迁的汉族人民可以按原籍聚居在一起,所以他们在南方建立了大批的侨郡、侨县。据《宋书》记载,仅长江下游,即今江苏一带就有33个侨郡和75个侨县。在东晋初年的几十年中,据《晋书》的组略统计,
从雍州迁出的约四、五万户;
从并州迁出的约四万户;
从梁、益二州迁出的约二十万户;
从冀州辽出的约万余户;
从宁州汪出的甚众。
合计30余万户。
西晋时雍、并、梁、益、冀、宁诸州合计约68万户,可见南迁的户口已占其半了。若和西晋全国户口比较,则全国245万户中有八分之一南迁;若户以5口计,则南迁者约150余万人,占全国1600亲万人口之1/10,占刘宋时南方人口的1/6。
三、南方各民族的大同化
从黄巾起义到隋的统一,在3个多世纪的动荡之秋中形成的一次又一次汉族人民南迁的冲击波,一次又一次地冲击着南方少数民族地区,使南方少数民族也被卷进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大同化的激流之中。
在北方汉族人民不断地大规模南迁的冲击下,原来居住深山,少与汉族交往的蛮、俚、僚、傒等族闭关自守的状况披打破了。
以蛮族为例,原来住在今湖南、湖北境内的蛮族,乘西晋末年战乱之隙,向长江以北的淮水、汝水、沔水流域迁移,占据了东晋、南朝统辖区域的腹心地带,加强了与汉族封建政权的联系,加强了与汉族人民的往来。历经魏晋,相当多的蛮族已与汉族杂居,有的则已编入郡县地方行政体系。汉族人民进入蛮区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因刘宋规定“蛮人顺服者一户输谷数斛,其余无杂调”,这比汉族农民的负担轻得多,所以汉族人民因“赋役严苦,贫者不复堪命,多逃亡入蛮”,以避繁重的赋役。此外,又有汉族经商入蛮者,也有逃入蛮区为蛮族首领者。这样一移一迁,汉族与蛮族相互渗透,形成了交错杂居的局面。
俚、僚、傒等族的情况亦如此。汉末至东晋,中原汉族人民也纷纷避难至交、广地带,加上东汉常以罪人徙于岭南地区,避役的汉人“年及应输”,也往往逃入俚人村落。于是,在岭南珠江流域也逐渐形成了汉族与俚族杂居的局面。俚族人民,也有许多被人掠卖为奴婢,所谓“小婢从成,南方之奚”。更多的则被抓当兵,进入汉区,与汉族人民杂居。而本来比蛮族还要落后的僚族,在李成统治后期也逐渐向平地移居。东晋后,僚族人“与夏人参居者,颇输租赋”。南胡刘宋时则置三巴校尉,治荆、益2州的蛮僚,肖齐时立平蛮校尉,专管梁、益2州僚人,这表明在这字地区也终于出现了汉族与僚族“参居”的局面。
本来,在中国南方,经过两汉以及孙吴的经营和开发,直到两晋时,汉族及汉族文化的发展,还只是限于长江流域的沿岸,限于从荆州南下,经湘州越五岭至广州的交通线上,限于沿海以广州为中心的一些点线。而长江和珠江流域的广大地区,特别是山区,都是由蛮、俚、僚、傒及其他一些少数民族或部族(甚至还有氏族、部落)居住着。汉族的地狭人少,与少数民族的地广人多形成对照。但是,经过南朝宋、齐、梁、陈四代,从北方南迁的大批汉族人民,与土着的汉族人民汇合在一起,与南方的少数民族在广大的地区内犬牙交错地杂居在一起了。除今江西西南部沿赣江流域,四川中部和北部沿嘉陵江和岷江流域,长江以北的淮河、汉水流域外,还从长江中游向南,沿湖水、赣水、郁水流域,向两岸地区伸延扩展,并波及钱塘江、瓯江、闽江流域,汉族及汉族文化的发展在南方出现了由点、线联结成面的新局面。
汉族同化南方少数民族的情况与北方有着不同的特点。北方的民族同化,是在汉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政权崩溃以后,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纷纷建立割据政权,汉族处于被征服、被统治地位的形势下发生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文明程度较高的被征服民族同化了文明程度较低的征服民族。南方则相反,魏晋南北朝时期,局处南方的汉族封建王朝,特别是南朝时,由于土宇日蹙,人口日少,为了巩固和扩大统治区域,扩大劳力来源,增加财富,必然对居腹心地带,人口众多,对封建政权征收赋役,提供从略、物力有重要意义的南方各少数民族加强统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文明程度较高的统治民族同化了文明程度较低的被统治民族。
蛮族,在南方少数民族中还是比较先进的,但其乘西晋之乱,从湖南、湖北扩展而出时,仍处于奴隶制社会。至刘宋时还是“衣布徒跣,或椎髻,或剪发。兵器以金银为饰,虎皮衣,
便弩射,皆暴悍,”而且“言语不一”。而俚族在东汉时代,由于汉族封建官吏“教其耕稼,制为冠履,初设媒娉”,才“始知婚娶,建立学校,导之以礼义”。有的在刘宋时还“皆巢居鸟语”。可见俚族最早在东汉时才进入阶级社会。向居山险,少与汉族人民交往的僚族则过着“略无氏姓之别,又无名字,所生男女,唯以长幼次第呼之”的原始社会生活。晋、宋时才进入“父死则子继,若中国之贵族”的奴隶社会。显然,与汉族先进的经济、文化相比,南方的这些少数民族或部族是大大落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