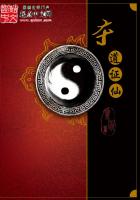我一下忘了自己要了什么东西,脑子里盘旋着别的事情,我没有理由为这号事面红耳赤……这个侍者(他好似侍候一个野蛮人)弄得我没有主张,我感到十分恼怒。归根到底,我不需要有自卑感。我干工作,并不是追求虚荣要成为一个发明家,但是像拿工程师开心的俄亥俄州那个浸礼会教友的能耐,我也是有的,我相信:我们这种人干的事情更有益,我负责过价值数百万的安装工程,我也负责过整个电力站的工程,我在波斯,在非洲(利比里亚),在巴拿马,在委内瑞拉,在秘鲁都工作过,我并不是像侍者显然认为的那种没有见过世面的人。
“先生,请用吧!”
这是表演,他们指指酒瓶,然后就拔去瓶塞,接着试喝一口……问道;
“味道不错吧?”
我憎恶自卑感。
“行啊,”我说道,并且不给人吓唬住,我清楚地闻到瓶塞的气味,但不想争辩,“行啊!”
我脑子里思量着别的事情。
天擦黑时,我是饭店里唯一的客人,完全是对面的金色边框镜子刺激了我;我每次抬头就看到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几乎可以说是一副祖先的遗容:金色边框镜子里的瓦尔特?法贝尔怎样在吃色拉。我眼睛下面有黑圈,如此而已,此外我晒得黑油油的,上面谈到过,已经很长时间不像往常那样憔悴,相反,我看上去气色很好。我是眼下正得意的一个男人(这没有镜子我也清楚知道),双鬓斑白,但像运动员一样棒。我谈不上是美男子。我在发育期间老是焦虑,自己的鼻子略微长了一点,此后就没有再为此而烦恼;此后为很多女人所倾心,她们消释了我不必要的自卑感,独有这家饭店叫我恼火:望到哪儿净是镜子,叫人厌烦,再加上我要的那盘鱼,等得都没有个时间,我决意训斥一顿,我尽管闲着无事,但感觉到侍者对我的态度怠慢,我不明白,为什么在这么家空荡荡的饭店里,有五名侍者。他们在交头接耳,并且只有我这个独一无二的客人,我抬眼看到,金色边框镜子里的瓦尔特?法贝尔在啃面包,我要的一份鱼终于送来了,烧得不错,但我吃不出一点味道,我不知道,我是怎么啦。
“你看上去像是……”
我只是由于威廉斯讲了这句含含糊糊的话(我明白,他喜欢我!),而一再照照叫人好笑的镜子,没有心思吃鱼,在这些镜子里一下出现了八个影像。
人嘛当然都会变老的……
自然不用多久就成秃顶了……
我过去不习惯看医生,除掉割过一次阑尾外,生来还从未闹过病……我照照镜子,完全是因为威廉斯说过:休息几天怎么样,瓦尔特?而我晒得黑油油的程度还是少见的。我在一个想成为空中小姐的年轻姑娘心目中,可能是一个稳重的先生,但是对于生活尚未厌倦,相反,我甚至忘记了原先想好到巴黎看医生的打算……
我觉得自己的身体十分正常。
第二天(星期天)我去参观卢浮宫,虽然我在那里逗留了整整一个小时,但是没有看到一个披着一束略带红色的马尾姑娘的踪影。
我跟最早一个女人的往事本已忘怀,这就是说,要是我不愿想起这件事情的话,我就根本不会想到它。也就是说,要是我不愿意的话。她是我老师的妻子,当年在我高中毕业考试前不久,有几个周末,我的老师拉我上他家里去。我帮他校对重版书挣一点钱。我极其渴望获得一辆摩托车,一辆老得只要凑合着还能开的车子。我不得不用水墨画绘人物像、毕达哥拉斯定理图例和诸如此类的玩意儿,因为我是数学和几何学方面成绩最优秀的学生。我当时那么个年纪,在我的心目中,老师的妻子当然是一位稳重的太太,我以为,她四十岁光景,患有肺病,她在吻我这个小伙子的躯体时,我觉得她像是一个疯子或是一条母狗;在这期间我仍旧称呼她为教授太太。这实在荒唐。我一再不去想这件事情;只不过在老师踏进教室并且一声不吭地将练习簿朝讲台上一搁的时候,我生怕他已知道了这件事情,并将闹得满城风雨。他往常分发练习簿都是第一个叫我的名字,使我不得不在全班级同学们面前露脸??唯一一个作业没有任何错误的学生。她在这一年的夏天离开了人世,我就像口渴时在一个什么地方喝过了水一样,忘却了这件事情。当然我忘却了这件事情,心里觉得有点不好受,我不由自主地每月上她坟上去一次;趁四周没人看到的时候,我迅速从皮包里拿出一束花朵,献在她的墓前,墓前还没有一块石碑,只有编的号码;这时我感到羞愧,因为我时时刻刻都为这事已成为过去而额手称庆。
只有跟汉娜在一起的事情从来就不荒唐。
春天,但下着雪,我们坐在杜勒里宫的时候,蔚蓝天空骤然风雪交加,我们差不多已有一个星期没有见面,她因邂逅重逢高兴得不得了,我看,她是由于抽烟,已经身无分文。
“我从未相信过您决不去卢浮宫……”
“总之很少去。”
“很少去!”她笑着说,“前天我看到过您,昨天也看到过您??在陈列古希腊罗马的艺术品那儿??”
她即或是一支接着一支地抽着烟卷,也还确是个孩子,她认为我们在巴黎再度重逢,可真是巧事。她仍穿着那条黑裤子,那双草鞋底帆布鞋,再加一件带兜帽的大衣,当然没有戴任何帽子,而只是束着略带红色的马尾,上面已谈到过,天下着雪,几乎可以说是从蔚蓝色的晴空中落下来的。
“您不觉得冷吗?”
“不冷,”她说,“但是您呢?”
我下午四点钟还有会议……
“我们喝杯咖啡吧?”
“啊,”她说道,“非常高兴。”
我们越过协和广场时,一个宪兵鸣笛催人,她伸出胳膊挽着我。这种举动出乎我的意料。由于宪兵举起了白色警棍,一群汽车冲着我们驶来,我们只好拔腿奔跑;我们手挽手逃到人行道上,我发觉帽子丢了??落在褐色的雪浆里,已给车轮辗得一塌糊涂。我嚷道:算啦!我挽着姑娘的手臂又往前走去,在暴风雪中头上没有一顶帽子,倒像是个小伙子。
莎白肚子饿了。
我对自己说不要弄迷糊,她对重逢感到高兴,是由于她身上差不多分文不名了;她狼吞虎咽地吃着精美糕点,几乎顾不上抬头说话……没法劝说她打消搭顺风车上罗马去旅行的主意,她甚至还安排好一份详细的旅程计划:阿维尼翁、尼姆、马赛不是非去不可的,但是比萨、佛罗伦萨、锡耶那、奥尔维耶托、阿西西是一定要去的,我知道她在那天上午就试图拦顺风车,但显然是跑错了通往郊区的大街。
“您妈妈知道这些吗?”
她斩钉截铁地说:知道。
“您妈妈不担心?”
我由于要付账还坐着,但已作好要走的准备,把皮包放到膝盖上;眼下赶巧威廉斯这样阴阳怪气,我可别太晚到会。
“她当然担心,”姑娘说道,这时她用匙刮着剩下的一点糕点屑,她只是由于受过教育才没有用舌头去舔盘子,她笑着说,“妈妈一直担心……”
后来她说道:“我不得不答应她,不跟任何男人同行??但这个道理很明白,我可不是傻瓜。”
在谈话的时候,我付了账。
“谢谢您。”她说。
我没有敢问:您今天晚上到底干什么?
我越来越闹不清楚,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姑娘。满不在乎地怀有什么样的念头?也许她会接受任何男人的邀请,这种想法并没有使我感到愤慨,但却使我嫉妒,简直是感情用事。
“我们是否还再次相见?”我立时又接着说,“如果不能再见面,那我祝福您一切都好……”
我确实不得不走了。
“您还在巴黎逗留吗?”
“那还用说,”她说,“我有的是时间……”
我已站起身来。
“要是您有空,”我说,“能给我帮个忙……”
我在寻找实际已经丢掉的帽子。
“我想看歌剧,”我说,“但是我还没买到票……”
我对自己随机应变的本事感到惊讶,我还从来没有上过歌剧院,这是不用说的,但是很懂事的莎白连一秒钟也没有犹豫,就接过买戏票的钱,准备帮我的忙,尽管我连歌剧院上演什么节目还闹不清楚。
“要是您有兴趣,”我说,“您就买两张,七点钟左右我们碰头……在这儿。”
“两张?”
“那敢情太好啦!”
我听到过威廉斯太太说这样的话。
“法贝尔先生,”她说,“可是我不能接受……”
我开会迟到了。
O教授突然站到我面前时,我确实没有认出他来。这样急匆匆上哪儿去?法贝尔,究竟上哪儿去?他的脸从不变色,但是完全变了样;我只知道:我熟悉这张脸。我熟悉他的笑声,但是怎么会熟悉的呢?他一定已经觉察到这一点。您难道不认识我了吗?他的笑声变得十分吓人,可不是,可不是,他笑了,我是见过一些世面的!他的脸不再是一张脸,而是蒙着一张皮的头颅,甚至还贴着肌肉,这些肌肉使他的面部表情发生变化,这种面部表情的变化使我记起了O教授,但这是一个头颅,他的笑声过于洪亮,使他的脸变了样,跟他深深凹陷的眼睛相比显得太大。教授先生啊!我说,并且留神不说出这样的话来:我知道,人家告诉我,您已经死了。我说:您一直很好吗?他从未像这样亲切,我过去敬重他,但是他从未像眼下这样的亲切,这时我拉着出租汽车的车门,他笑着说,巴黎的春天啊!我吃不透他干吗总是不住地笑,我认识他是瑞士工科大学的教授,而不是一个小丑,但是他一张开嘴巴,看上去就像是在笑。可不是,他在笑,眼下又略微好一点了!因为这时他根本没有笑,也不像是一个骷髅头在笑,只不过给人这种感觉而已,我请他原谅匆忙之中没有立时认出他。他大腹便便,过去可不是这样,肋骨下面隆起的肚子,像圆滚滚的气球一般,其他的部位却都很瘦削,他的皮肤像皮革或是黏土,双眼炯炯有神,但深深凹陷。我胡诌了一点什么事情。他竖起两只耳朵。如此急急忙忙上哪儿去?他笑着问我,是否来喝一杯开胃酒。像上面谈到过的情况一样,也是出于衷心,当年在苏黎世,他是我的教授,我十分敬重他,但是我确实没有工夫去喝一杯开胃酒,亲爱的教授先生!这种话我平常可从来没有说过。亲爱的教授啊!我说,因为他抓住我的胳膊,而且我知道别人都知道的事情;但是他似乎并不知道。他笑了起来。他说,那下一次多待一会儿!我知道这个人早就死了,于是说道:好的!我跨进了出租汽车……
这次会议跟我丝毫没有关系。
对我来说,O教授曾一直是一种典范,他虽然不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也不是苏黎世的瑞士工科大学里享有世界声誉的教授,不管怎么说,他是一个具有真才实学的专家……我永远不能忘怀,我们这些穿着雪白绘图工作服的大学生团团围着他,他给人的启迪,逗得大家哄然大笑:一次蜜月旅行(他一直这么说)就完全够了,此后你们会在书刊中找到一切重要的东西,您们将学习外语,我的先生们,但是旅行,我的先生们,是中世纪的事情,我们今天已有通讯工具,更不用说明天和后天了,那时通讯工具会把全世界的情况传送到我们家里,从这个地方乘船搭车到那个地方,这是一种返祖现象。你们笑了,我的先生们,但是情况就是如此,旅行是一种返祖现象,将会有一天,根本不再要乘车搭船来往,只有新婚夫妇去搭一部出租汽车周游一下世界,除此以外就不会有任何人……你们笑了,我的先生们,但是你们还会活着看到这个事实的!
他突然出现在巴黎。
他不住地笑也许是这个缘故。(据说)他得了胃癌,也许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而他感到好笑,是因为两年来人人都说医生认为他活不了两个月。他在嘲笑我们;他如此有把握地认为,我们下一次能重新相见……
会议持续近两个小时。
“威廉斯,”我说道,“我改变了我的主意。”
“怎么啦!”
“嗯,我改变了我的主意……”
威廉斯驱车送我回旅馆,路上,我谈到还想作一次短期休假,因为是春季,去作一次短期旅行,两个星期左右,或是到阿维尼翁、比萨、佛罗伦萨和罗马跑一趟(旅行)所需的时间,威廉斯并没有感到突然,相反,他跟过去一样慷慨:立即表示把他的雪铁龙轿车给我使用,因为隔天他就要飞往纽约。
“瓦尔特,”他说道,“祝您过得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