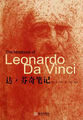有一天提奥邀温森特一块去出席一个宴会,是一个叫亨利·罗酥的画家发出的请帖。亨利·罗稣40岁之前曾是地方海关的收税员。和高更以前一样,常常星期天作画。几年前他来到巴黎,定居在巴士底附近的工人区。他一辈子没有受过一天的教育,或者受到什么指教。但是他画画、写诗、作曲,教工人的孩子拉小提琴、弹钢琴,教老年人绘画。他喜欢画一些稀奇古怪的动物,它们从更加怪异的热带丛林中朝外窥视。他去过的最近的丛林就是布隆巴森林中的动物园。他是个农民,而且天生是个原始派,高更经常笑话他。在别人眼中他同样是个疯疯傻傻的家伙。
罗酥是巴黎最穷的画家之一,他教课用的小提琴都是租的,因为他买不起。他开宴会是另有目的,无非是廉价出售他的新作,换来一些法郎,供他买烟草、食物和画布,继续画下去。
罗酥说他在提奥那里看过温森特的画,他认为那些画荷兰农民的作品很好,比米勒的还好。“你知道他们管你叫疯子吗,罗稣?”温森特说。
“是的,知道。而且我听说在海牙时他们也认为你疯了。”罗酥笑着回答。
他们俩人相视大笑。过了一段时间,提奥在公司很忙。这样高更就经常光顾温森特的公寓,高更看到了温森特在布拉邦特和海牙画的一些油画,他很惊讶,甚至想不出准确的语言把自己的感觉表达出来。
“恕我问一句,温森特,”他终于开了口,“你也许是个癫痫病患者吧?”“我是什么?”温森特大吃一惊。
“癫痫病患者。是一种患有阵发性精神病的人。”
“没有那回事,高更。你干吗这么问呢?”
“哦!因为你这些画,它们看起来仿佛就要从画布上跳出来。当我看着你的作品时,我就开始感到一种无法控制的兴奋,并且你的每幅画都似乎要爆炸。总之,不像一个精神正常的人画的。”这就是高更对温森特的画的印象。
高更和温森特两人在外面转了一圈,正当他们口沫四溅地争论一些作品的看法时,碰见了保尔·塞尚。塞尚也是貌似落魄的艺术家,殊不知他父亲是个银行家,相当有钱。
塞尚正在生气。因为爱弥尔·左拉刚写了一本书《作品》,而里面的主人翁,那位画家正是塞尚。左拉把塞尚描绘成一个空想家,是一个误入歧途的可怜虫,自以为在革新艺术。之所以不因袭传统的画法,是因为压根儿缺乏应有的绘画才能。并且最后左拉还把这个以塞尚为原型的画家安排这样一个结局:自缢在他的杰作的脚手架上,原因是他最后认识到自己错把疯子的乱涂乱画认作才华。
高更感到很有趣,因为爱弥尔·左拉是第一个支持爱德华·马奈在绘画方面的革命的。在世人眼中,爱弥尔是对印象派绘画尽力最多的人。左拉崇拜马奈,因为马奈打倒了学院派。但是塞尚一旦想要超过印象派时,左拉就把他称作傻瓜和白痴。
左拉和塞尚两人都来自同一个城镇,童年时就是好朋友,可是左拉居然想到写这样一本书来出塞尚的洋相。
塞尚的油画也不受人欢迎,在巴黎,惟一愿意把他的画放进橱窗的画商是佩雷·唐古伊。塞尚不想在巴黎待下去,他准备回埃克斯,在那里度过余生。在普罗旺斯有着明亮而辉煌的阳光和色彩,他想在山顶上买一块地皮,过与世无争的隐士生活。
巴蒂格诺莱是克里希林阴大道路口的一个郊区。就在这儿,爱德华·马奈把巴黎那些在艺术上与其志趣相投的人物聚到自己的周围。这个巴蒂格诺莱画派习惯上每周在咖啡馆聚会两次。勒格罗、库尔贝和雷诺阿都是在那儿结识,并搞出他们的艺术理论的。但是如今这个地方已被更年轻的人们所接管。塞尚看见了左拉,他避开人群坐在一个角落。高更把温森特介绍给左拉,接着就和劳特累克坐在了一块。
左拉和温森特交谈了起来,他们谈到了左拉以前写的一本书《萌芽》,这本书已经在法国的矿区引起四次罢工和反抗,销售额非常好。左拉当初到过博里纳日为《萌芽》收集素材,听那些煤矿工人讲述一个基督式的人物,但左拉没想到这个人会是温森特。劳特累克那边的讨论很激烈,他正和修拉关于用色方面的问题争论不休,高更和罗稣也加入进去了。后来,大家又聚在一块听左拉高谈阔论:艺术是不能用道德标准来评判的。艺术是超道德的,生活也是如此。在我看来,淫秽的画和书籍是没有的,有的只是想像力贫弱和技巧拙劣的作品。劳特累克笔下的妓女是道德的,因为她表现了藏在她外表下面的美。而布格罗笔下的贞洁的乡村姑娘是不道德的,因为她显得矫揉造作,而且甜腻腻的令你不忍看第二眼。提奥很赞成左拉的看法。
温森特看得出来,这些画家之所以尊重左拉,并非由于他已获得成功——他们鄙视那种普通涵义的成功——而是由于他是用一种在他们看来即神秘又难于掌握的手段进行创作的。他们仔细地听他讲话。他们大谈了一通道德与超道德。温森特开始说话了:“我的画至今为止还没有人认为是淫秽的,但是总有人指责我犯有一种更为严重的不道德罪,那就是丑陋。”
大伙都认为温森特说到点子上来了,因为刚刚出的《法兰西信使》称这伙画家是一伙丑陋的狂热信徒。劳特累克还找出一张旧报纸,里面有一位批评家对他在上届《独立沙龙》展出的油画的评价:图鲁兹·劳特累克也许会因其描绘粗俗无聊的寻欢作乐以及“下流主题”的嗜好而受到谴责。他看来对于美丽的容颜、漂亮的体型和优雅的姿势毫无兴趣。确实,他是用充满爱意的笔去描绘那些畸形、矮胖、丑得让人恶心的人物的,不过这种反常有什么益处呢?
大伙哄堂大笑,左拉、温森特、德加、劳特累克和高更被提名为丑陋的狂热信徒。
“让我们把我们的宣言确定下来吧,先生们,”左拉说。“首先,我们认为,一切真实的东西,不管其外表看起来多么丑,都是美的;我们接受大自然的一切,不得有任何否定;我们相信,触目的真实比漂亮的谎言要美,泥土之中比巴黎所有的沙龙中有更多的富于诗意的东西;我们认为痛苦是有益的,因为在一切人类情感中它是最为深刻的;我们把性格看得比丑陋更重要,把痛苦看得比漂亮更重要,把赤裸裸的严酷现实看得比法国全部财富的价值更高。我们全盘接受生活,无需在道德上加以评断。我们认为娼妓和伯爵夫人,看门人和将军,农民和内阁部长都是一样的,因为他们全部符合自然的要求,都是生活的组成部分。”
6月初,提奥和温森特搬进了蒙马特尔的勒皮克街54号的新寓所。这所房子离拉瓦尔街很近,他们只要走上蒙马特尔街,过不了几个街区就到了克里希林阴大道了。
他们的那套房子在三楼,里面有三个房间,还有一个小房间和一个厨房。这样温森特就可以不必再去科尔蒙那里画画了。
第二天一早,温森特起床就开始画画了。提奥给温森特买来成批的画布和颜料,让他潜心作画。但是很快,温森特的情绪又变得烦躁不安,变化无常,又开始和提奥争论起来。炎热的夏季来临,火辣辣的太阳灼晒着街道。温森特每天上午都肩背画架去寻觅他要描绘的景物。在荷兰,他从来不知道会有这样火热,这样久久地照射大地的太阳,也从未见过这样纯而浓烈的颜色。
提奥决定为温森特的朋友们举行一次宴会。他们忙乱了一阵,这些朋友们陆陆续续到齐了。房间里充满了慷慨激昂的气氛。在这儿的人全都是个性很强的人,是狂热的自我中心主义者和激烈反对因循守旧的人。提奥管他们叫做偏执狂。他们喜欢争论,爱斗好骂,捍卫他们自己的理论,诅咒其余的一切。他们的嗓门又高又粗,世上遭到他们厌恶的事物多得很。即使是一间相当于提奥居室几倍大的大厅,也还是容纳不下这些正在激战中的粗嗓门画家们那种充沛的活力。房间里那种使温森特激动得手舞足蹈、口若悬河的骚乱,却使提奥头痛欲裂。这样刺耳的喧嚣与提奥的性情完全不符,但他却非常喜欢房间里的这些人。不就是为了他们,他才去同古比尔展开这场无声的、没完没了的斗争的吗?然而,他觉得他们这种粗野的大声吵闹的性格与他的本性格格不入。
他最后看了一眼这间充满叫嚷声、争论声和腾腾烟雾的房间,悄悄地溜出了前门朝高坡走去,在那儿他独自一人凝望着展现在面前的巴黎灯火。
高更大声嚷着塞尚,说他的油画冷冰冰的,一点感情都没有,只会用眼睛去画他所看到的苹果和风景。“别人是用什么画的呢?”塞尚反驳道,“难道不用眼睛画吗?”
“用各种各样的东西。”高更迅速扫了一眼房间,“劳特累克,是用他的怨恨画;温森特用他的心;修拉用他的头脑,这和你用眼睛画一样糟糕;而罗稣则是用他的想像。”
诸如此类的争辩没完没了。事后他们只有一点共同的地方,那就是他们想合伙办一个展览,名称就叫做“小林阴道俱乐部”首届展览,地点选定在由佩雷·唐古伊推荐的诺文饭馆。第二天,他们找到了诺文饭馆,那是个很简朴的房子。在房子里挂满了他们各式各样千奇百怪的油画。佩雷·唐古伊在墙上贴满了告示:廉价出售绘画,请与老板接洽。
来诺文饭店吃饭的大多是些普通工人,他们对墙上这些画毫不感兴趣,只管吃他们的饭,然后付钱走路。
一个多月的时间,温森特连想他的调色板的功夫都没有。他草拟了无数的计划、章程、预算、募款请求、法规和条例,撰写了报纸的声明和向欧洲介绍共产主义艺术科勒尼的宗旨的小册子。他是那样地忙,忙得把作画都忘了。
开春时,资金已经凑齐了,提奥准备通知古比尔公司,他已经买下了一个店面。提奥、温森特、佩雷、唐古伊、高更和劳特累克拟出了科勒尼开张时的成员名单。提奥也开始从成堆的油画中挑选出准备在首次画展中展出的油画。
一天早晨,温森特醒来,他突然想起了他的画室,他走了进去。画架上绷的画布还是好久以前的;调色板上的颜料已经干裂,蒙上了一层灰尘;颜料管被踢到了角落里;扔得到处都是的画笔上干结着变硬的旧颜料。他心中有声音在问他:温森特,你到底是个画家,还是个组织家?
他把自己的作品摆在一边,凝视着他们。是的,他取得了进步。很慢,很慢,他的色彩提亮了,他的画再也不是模仿品了。画布上也找不到他朋友们的痕迹了。他第一次领悟到,他已经形成了一种很独特的技法。这和他所见过的一切都不同,他甚至不明白这是怎么做到的。
他按照他的性格适当地汲取了印象派的手法。并且已经接近于获得一种非常奇特的表现手段。他和提奥深谈了一次。提奥很吃惊他怎么一下子来了这么大的转变。
温森特决定告退,他不想做其他艺术家的管家,他有他自己事业,并且他意识到他不是个城市画家,他不属于巴黎,他是个农民画家,他想回到他的田野上去,他要找个独处的地方。温森特又开始画画了,尽管他的画布上的颜色已经和他的朋友们一样清晰明亮了,他还是不满意,他屡屡感到自己正在摸索出一种绘画的语言。他画了大量的自画像,他发现自己已经掌握了必要的新技术,如老一辈印象派的光色,分色主义的点彩法,甚至日本浮世绘的奇特构图等等,而且经过淘汰,已能融入自己的作品。
他发现巴黎已没有适合他画的东西了。巴黎曾使温森特感到兴奋。他喝了太多的酒,抽了太多的烟,参加了太多外界活动,他被塞得满满的。虽然巴黎还给予了他许多许多,但他迫切地希望离开,独自去某个安静的地方,在那儿他可以把汹涌充沛的精力倾注到他的绘画上。他仅仅需要有一个炽热的太阳促使他成熟结果。他有一种感觉,他一生的最高峰,他为之奋斗了漫长的八个年头的那种创作力的全盛时期已经离得不远了。
他知道,在他已经画出的东西中迄今还没有一件是有价值的,也许就在今后一段不长的时间中,他可以创作出那为数不多但无愧于他的一生的作品来。在巴黎两年中,他过着有保障的生活,有友谊,有爱。在提奥那里永远有个为他准备好的温暖舒适的家。他弟弟从不让他挨饿,也不要为绘画用品的缺少而担忧,尤其不吝惜给予他最深切的同情。
他知道,只要他一离开巴黎,麻烦事就来了。离开了提奥,他的生活费就安排不好,他就得有一半的时间勒紧肚皮过日子。他不得不住进肮脏的小饭店,由于买不起颜料而苦恼,并且没有一个人可倾心交谈。但是他去意已定,他不能贪图一时安逸而背叛他的事业。
他给提奥的墙上挂满了画,其中包括那张戴圆顶草帽的佩雷·唐古伊的肖像、一幅盖莱特磨坊、一幅淡红色的虾、一幅从背部看去的女人裸体和一幅描绘爱丽舍宫的习作。他想让提奥一看见这些画就想起他。
温森特就此告别了巴黎。这时是1888年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