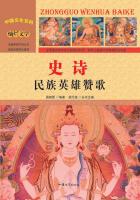对于儿孙辈久困场屋,文徵明有时吟哦祖父文洪的《除夕》诗以自解:
“……梅渐有香因得煖,竹能无恙为禁寒,一杯莫道贫非幸,且得团圆共笑欢。”(注一)
文洪赋此诗,时在中乙榜不就,自北京南归家居,含饴弄孙,有感而发。近时每届年节,孙曾绕膝,徵明想起祖父诗中所谓不幸之幸,得享天伦团圆之乐,他的心中,倒有了层更深的体会。
他也记得正德晚岁和长子文彭一起到南京赴试的往事;江西宁王造反的消息频传,城内一夕数惊。在长夜细雨声中,百无聊赖地喚醒文彭,闲话半生的得失。
一次他在玉兰堂中置酒,已是送长子文彭和长孙肇祉赴试金陵。当他正想嘱咐几句笔砚和南都起居之事,肇祉却口吟五律一首:
“吾祖已垂白,堂开聚德星,衣裳动云气,杯酌吐玄音。喜共趋庭日,那堪驾远临,欧公倘相遇,苏氏慰初心。”——大父玉兰堂小酌时将奉侍家君应试南畿(注二)
这种三年一度地送儿孙赴试,无论离别的惆怅,别后的悬念,遥远的祝福,以及父子叔侄铩羽而归的沮丧;似乎都成了一种固定不变的循环模式。丹阳、焦山和金山,均属必经之地,首先,他会在家书中,读到他们纪游之诗,和满怀的信心与斗志。寓邸的夜读和应酬的景况,他不但知之甚详,更仿佛身临其境。锁院的煎熬,中秋后的焦虑和等待,不仅应试者,更是全家人心之所系;这期间儿孙媳妇对他的饮食和照顾,都显得格外地审慎。
如果收到肇祉《雨花台》或《出场月色如昼侍家君至顾尚书园登见远楼》一类的诗篇,其用意一方面为抒解入试者的心理压力,一方面也为松弛家人紧绷的心弦。接着,就是出现在里门,包括书童在内的一张张沮丧的面孔。
“一秋惭失意,九日废登台,菊为佳辰发,怀从浊酒开。哀蝉犹夕响,征雁向南回,时序愁中改,城高砧杵催。”——《九日不出》(注三)
文徵明看到长孙肇祉失解后的重阳诗,想到自己集中的类似诗篇,心中真是别有一番滋味,许多往事,纷纷浮现在眼前。
同样潦倒而归的文彭,稍事休憩之后,便手不停挥地书写起来。他不同于乃父的,是性情随和;徵明晚年,索书者如非其人,或是在情绪上不乐于书时,虽权势富贵者,亦无法强求。文彭却使求者无不如意;因此,堆积在其斋中的楮素,反而是他屡试不售后,消除心中块垒的良方。
虽然少承家学,但年已五十三岁的文彭,无论篆、分、真、行、草、都已渐渐摆脱父迹,自成家法。有人认为其才胜过乃父;而功力精熟,比文徵明则稍嫌不足。也有人认为其小楷肉而圆,行、草有怀素、孙过庭法,在临摹双钩方面,则有明以来,无人能及。而文徵明始料未及的,是长子篆刻方面的成就,已开一代之先河。
文徵明治印,不知始于何时,也不知以那家为法,大概是以秦汉为师吧!论者认为文徵明印章雅而不俗,清而有神,颇得六朝遗意;比秦汉玺印,也许缺少几分苍茫古朴。宋元以来,王诜、米芾、钱选、赵孟頫、王冕,皆能治印;以前文人的“诗书画三绝”,逐渐转向诗书画篆刻四美,似乎成了一种必然的趋势。尤其王冕以花乳石为印材,突破了古代铜铁金玉等印材的限制,治印时不但下刀容易,且别具神韵。
文徵明治印,知者不多,其印作也鲜有流传,就愈发凸显出文彭在此道的历史地位。
“为善最乐”,白文长方印,文彭作于嘉靖九年;由此以观,到了嘉靖二十九年,文彭治印起码已经历了二十年的岁月,或许更为久远。文徵明的名、字、“停云”诸印,莫不出于文彭之手。
文彭的治印习惯,于印背以真书释印面篆文,以行书为边跋;字迹潇洒流畅,有一气呵成之感。
“琴罢倚松玩鹤”,嘉靖二十六年,为好友唐顺之(应德、荆川)作的朱文印,就是最好例子。款为:
“余与荆川先生善,先生别业有古松一株,畜二鹤于内。公余之暇,每与余啸傲其间,抚琴玩鹤,洵可乐也。余既感先生之意,因检匣中旧石,篆其事于上,以赠先生,庶境与石而俱传也。时嘉靖丁未秋,三桥题识于松鹤斋中。”(注四)
文彭早期篆刻,并非以石,而是以象牙为材。写好印文之后再请南京李文甫操刀为镌。李氏善雕扇边花卉,玲珑有致,极为生动。他为文彭刻印,颇能把握文彭的笔意。及至以石为材,自然不必假手于人,也就愈能表现出其独步当代的风韵。
此外,文彭在绘画方面,亦非吴下阿蒙,写墨竹,老笔纵横,可入文同之室。山水苍郁,颇近吴镇。对于花果写生,风评也大为可观。
至于在闱场中同属难兄难弟的文嘉,倒也能借艺文创作来平复失意的心绪。其小楷轻清劲爽,山水疏秀似倪瓒;但无论书画,较之父兄,都稍逊一筹。人们认为,他鉴古和石刻的功夫,可为有明之冠(注五)。
诗文草隶大有父风的文肇祉,虽然也是屡试失利,比起年逾半百的父叔,文徵明总觉得肇祉来日方长,得失之间,不会过分萦怀;然而他读过肇祉的《览镜》五律之后,则不能不予以格外的关怀。
“览镜对愁颜,西风秋雨,惭看新白发,犹着旧青衫。酒醒难成寐,诗裁不用芟,辞巢双燕子,空自语喃喃。”(注六)
“清朝揽明镜,元首有华丝,怆然百感兴,雨泣忽成悲。……”伯虎赋《白发》诗时,年仅二十六岁,不但徵明可以体会他那种父母妻子相继死亡后的哀伤,及功名无成的焦思,连父亲文林也赶紧和韵,加以劝慰。算来肇祉不但年逾而立,连其子文周,也渐渐长大成人,看来“五世同堂”当非空想。难怪肇祉揽镜自照,悲头上之白发,也悲那袭难以摆脱的秀才青衫。
文徵明的《千岩竞秀》轴,完成于嘉靖二十九年三月十日;共历三年岁月。比起他为王宠所作的《关山积雪图》——历时五年,为陆师道画的《千岩万壑图》——历时十三年;为王穀祥所画的《千岩竞秀万壑争流》卷——始于嘉靖二十四年,已经六载,尚不知成于何日?为时三年完成的《千岩竞秀》不能算是太久。但他年岁愈高,愈感到光阴之可贵;他忍不住在识中自责:
“……昔王荆公选唐诗,谓‘费日力于此,良可惜也’;若余此事,岂特可惜而已!”(注七)
七十九岁那年冬天,长夜无眠,取纸戏写此图,当时仅成一树而已,以后屡作屡辍,以致拖延到八十一岁的暮春。
此轴纸幅狭长,位置奇特,结构紧密。首先,以山溪和树梢,断断续续地形成一条斜线,右上左下,把画面分成两部。这条分割线的起讫,是由右边的中点伸展至左边五分之三处;在分割比例上,异常优美。
上部山岩结构极为繁复,有矾头远峰、光滑的石坡、蜿蜒起伏的岗岭,以及可予人憩息登眺的平台;千岩竞秀的繁复中,却布置得井然有序。山以浅绛色染成,一簇簇的远树和盘旋纡曲的泉流,使奇岩巨石,顿时显出一片生气。图的下半,在偏左侧的枝叶掩映中,众流汇聚成垂瀑,直泻而下。瀑底岩石略呈弧形,远视清潭,仿佛一具银瓶,承接着万斛明珠。近处一座小小石峰,突兀而立,与垂瀑上下呼应。伸向潭中央的一个石坡,顺理成章的连贯了山峰和落瀑之间的气脉。在潭岸、峰顶和左缘的树干之间,微露携琴童子和两位相对清话的高士;这瀑布、明潭、高士,就是千岩之外令观者瞩目的另一个焦点,也是人与自然和谐圆满,融合一体的所在。而上下两个焦点之间,也安排得恰到好处,在“竞秀”、观瀑间,呈现出一片馨宁。
又是初夏时候,停云馆蝉声四起,闻知长洲茂才张凤翼(伯起)病卧石湖僧舍,文徵明心中不觉怃然。
张凤翼父亲张冲,贾而侠,性情与当年唐伯虎父亲唐广德有几分相近。张冲育有三子,凤翼、献翼(幼于)、燕翼(叔贻),气质俱各不凡,而凤翼更有奇童之名。
童年的张凤翼与文徵明幼时颇为相似,到了五岁犹不能言语,人以为鲁钝。一天,见祖父张准扫除庭院,张凤翼突然开口指着乳娘说:
“汝当代扫!”闻者莫不啧啧称奇。
另一传扬一时的佳话是,童年的张凤翼不知何故触怒父亲,张冲一把抓住他的头发,凤翼忙说:
“徐之!是中有簪,末锐,惧伤大人手。”父亲的怒意因之而解;所以凤翼的孝名,也传闻远近。
他像文徵明一样,自少便耽于二王的法书,年纪虽仅二十有三,却已退笔成冢;在文徵明眼中,他像周天球一样,倘然投入门下,又是一位书道传人。而其专心治易的精神,则像亡友蔡羽。这一切,似乎都加强了文徵明对这位同邑张凤翼秀才的关怀与厚爱。
那天夜晚,当彭年把张凤翼卧病消息带到玉磬山房,文徵明又是疼惜又是感叹,随即剪烛命笔,作水墨《古柏图》。
图中古柏虽仅一株,但情态、笔致,和那种偃仰蛣屈,孤高凌云之势,使人自然想到他六十三岁那年,为石门王氏所摹的赵孟頫《虞山七星桧图》。画在千年古柏后面的湖石,雄奇丑怪,颇有与天地同生共存的气概。这幅古柏图,对年轻的张凤翼,既是激励其求生的意志,更是祝祷他寿比贞石古柏。最令门生子弟称羡的,是文徵明题诗中对张凤翼的奖誉:
“雪厉霜凌岁月更,枝虬盖偃势峥嵘,老夫记得杜陵语,未露文章世已惊。徵明写寄伯起茂才。”(注八)
图后,和者十余人,茲举三首,可见文徵明门生、好友和儿子对此图诗的珍视,对张凤翼蒙其垂爱的羡叹:
“书法翩翩近率更,诗才未儗让钟嵘,郑公三绝亲题赠,一日声名艺苑惊。”——陆师道。
“翠柏星霜阅变更,仇池风骨自峥嵘,文翁为爱张衡赋,片纸图成满座山。”——袁。
“秉烛挥毫仆屡更,虬枝香叶斗峥嵘,知君卧病无聊赖,寄向空山神鬼惊。”——文彭。
年寿日高的文徵明,无论体力、目力,常有日益不济之感,对于所作书画,也往往不甚满意。
“感君意趣犹如昔,顾我聪明不及前”;类似题《千岩万壑图》的句子,远自二十年前就屡见不鲜。
这年五月二十六日,有客索书《赤壁赋》,当时他觉得兴致尚好,随于烛下连夜作行草书《赤壁赋》轴。次日悬壁自视,愈看愈不满意。数日之后,又觉得意兴勃发,颇得苏长公文气之助,乃秉笔挥毫;结果依旧不尽如意,他题:
“……逾数日再为书此,而卒不佳;岂老人气弱,不可强也!”(注九)
由此一跋,足见文徵明晚岁之虚怀若谷及自我要求之严。两个月后的七月二十五日,有客持唐伯虎的《赤壁赋图》来谒,文徵明览图怀人,感慨之余,为书小楷《赤壁赋》。
不知何时,价如珙璧的唐画文书,却失其图而存其赋,使人见了,不禁生出感伤。五六十年后,文嘉的长孙,徵明曾孙文从简,感伤之余,以浅设色,补绘《赤壁图》,使曾祖遗泽免于孤零。此一艺坛佳话,当为文徵明始料所未及。
“曾王父楷书《赤壁赋》,图失而书存,简追摹此纸。前贤名迹,加于人数等,何物小儿,敢为邯郸之步;多见其不知量也。曾孙从简拜书。”(注十)
在五月的行草《赤壁赋》、七月的楷书《赤壁赋》之间,又有七月十六日所书《阿房》、《赤壁》两赋(注十一);文徵明对《赤壁赋》之喜爱,书写之勤,于此可见一斑。
年已知命的王穀祥,不仅愈来愈少交游,连那渲染有法,意致独到的写生花卉,也鲜有新作。每日杜门却扫,焚香默坐,并手录古文,多至数百千卷。他录古文的书册、仿晋的字迹,精致美好,令人不忍触摸。
此外,他像文彭一样,篆籀八体及摹印,无所不善;满室之内,琳瑯金薤,宁谧温馨。他有咏《绣毯》诗二首,无论用以形容他敏颖的才思,修洁的姿容,乃至那种清静优雅的生活情调,都很恰当:
“朵朵冰镂就,团团玉簇成,水晶帘影外,相映太分明。
朵朵玲珑玉,团团簇不开,天风苦无赖,推月下瑶台。”(注十一)
文徵明的长孙文肇祉,对王穀祥的人品风范,一如对王宠般景仰,那如诗如画的生活境界,更使他流连忘返。一次,王穀祥邀饮于宅内,使他有种当年置身陈淳浩歌亭的兴奋:
“吏部声名久,堂虚客到稀,举杯留夜酌,邀月弄清辉。露沃天香袭,谈霏玉尘挥,清朝思报答,明主正垂衣。”《秋夜王吏部录之丈招饮》(注十三)
不过,言及当年在吏部所见所感,这位乞归奉母不准,反被谪为真定通判的文选员外郎王穀祥,只是不置可否地淡然一笑。
大约深秋时分,多时不见的王穀祥,冒雨造访停云馆,手携赵孟頫所画兰竹。文徵明自谓嗜古书画成癖,闻有名书名画,甚至不远几百里,扁舟往访,一展为幸。尤其赵孟頫的书画,是他上追晋唐的桥梁,为复兴古代书画的重镇,展卷之际,其内心的快慰,可想而知。文徵明感觉中,赵孟頫飘逸的笔墨,疏篁幽兰相看不厌的情态,仿佛眼前冲寒冒雨,翩然而至的嘉宾。他对赵氏兰竹、心领神会之余,也搦管挥洒一幅,以报良友的美意:
“纤纤小雨作轻寒,最好疏篁带雨看,正似美人无俗韵,清风徐洒碧琅玕雨中禄之携松雪画兰竹过访,即为作此。徵明,时年八十有一。”(注十四)
对于一生荣辱,不管看得何等澹泊的人,内心中总有一些萦怀不去的往事;文徵明自不例外。
他抄录予人最多的诗篇,则为当年赴试入京后的《午门朝见》、《奉天殿早朝》、《实录成蒙恩赐袭衣银币》……这是他生命史上最辉煌的一页。比之金殿传胪,进士及第虽然未可同日而语,然而能蒙优旨除授翰林待诏,也是多少读书人梦寐难求之事。次为怀归诗和游苑诗;怀归诗一方面反映权臣当道、朝政混乱,多少老成谋国的元老重臣,多少胸怀理想,不为身家性命与前途计的新锐,纷纷挂冠求去,或遭受杀害、斥逐。另一方面则表现出他的风骨和志节,不为威迫和利诱,宁可牺牲那得来不易的荣宠,毅然致仕出京。
《西苑诗十首》,记录着他离京前的一次奇遇。御苑之美不亚于蓬莱仙境,历代高官显宦,终老金台,倘无特殊机缘,恐怕也难越雷池一步。他所以能留下这十首诗作,不能不感谢亡友陈侍讲鲁南和守苑官王满。
从他当日的《西苑诗》后记中,即可见出那种机缘不再的感喟:
“窃念神宫秘府,出天上,非人间所得窥视。而吾徒际会清时,列官近禁,遂得以其暇日游衍其中,独非幸与!然而胜践难逢,佳期不再……因尽录诸诗藏之。他时邂逅林翁溪叟,展卷理咏,殆犹置身于广寒太液之间也。”(注十五)
尽管时光流逝,这令人难以想象的人间仙境,不但时时呈现眼前,更一遍遍地抄录,与好友共享。然而每抄录吟哦一次,也往往引起他内心的感慨。
嘉靖二十九年十月十六日,他再次以行书录《西苑诗》,看着镜中白发;岂仅“胜践难逢,佳期不再”,一切都像南柯一梦;遂加小叙于后:
“……于是去游苑之岁二十有七年,而余八十有一矣。回首旧游,恍若梦境,可慨也。徵明识。”(注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