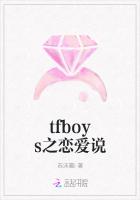但是,昆德拉把刻奇无限放大,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悖论。他认为“无论我们如何鄙视它,刻奇都是人类境况的一个组成部分”。他把人对意义的追求都看作是刻奇。然而,刻奇与崇高是不同的:崇高产生于自我以外的意义,而刻奇产生于自我内部。昆德拉看到建立在主观价值上的刻奇的危害,这是他的思想贡献,但由于他不承认客观价值,忽略了集体审美与个人审美的区别,从而将崇高与刻奇等同起来,将雪莱、拜伦、莱蒙托夫、兰波与郭沫若等同起来,最终导致对一切价值和意义的否定。要么刻奇,要么虚无;要么自我崇高,要么犬儒主义。可问题在于,意义世界真的是虚无的吗?就像米沃什所说,我们不能赤裸裸地活着,如果我们只是痛并快乐着地活着,任人宰割,我们会快乐吗?
昆德拉向往启蒙理性,怀疑一切;哈维尔却坚信意义世界,坚信在人类头上,还有一个更高的存在。哪种是正确的?或者说,你选择哪种?这个提问可能又会陷入一元论思维。我个人目前倾向于一种中道的立场,即在内心中保留超验的背景,同时又重视常识经验和怀疑精神。假如这个世界真有一个整全的真理,那么这个真理也是由无数的侧面组成的。无论是昆德拉,还是哈维尔,都只是表现出一个侧面。他们的声音不是给我们答案,而是让我们思考。
苏格拉底说过,未经思考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人生。这话听上去可能又有点刻奇。但许多人仍然关注中国的现状和未来,这至少说明,在今天市场潮流的裹挟下,我们大家仍在思考。归根结底,我们都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
活下去,并且要记住
1992年4月,美国纳特格大学举办了一次国际研讨会,讨论的题目是苏东剧变后的局势,参加者中有许多苏联和东欧的作家。捷克当代著名作家伊凡·克里玛也在会上作了发言。他说,人们常向他提出这样两个问题:他的童年是怎样从纳粹集中营里熬过来的,他作为一个作家又是怎样从苏联的长期占领中熬过来的。对此他没有直接作答,而是讲了一段不相干的经历,说他在抵达肯尼迪机场后,丢失了随身的钱财和讲稿,尽管他很沮丧,可最终还是幸运地熬过来了。“只要熬过来,不幸的经历总是值得的。”
《我快乐的早晨》封面他说。这番话使我想到克里玛的小说《我快乐的早晨》,一部面对生活的荒诞而显得轻松快乐的作品。
对克里玛来说,
伊凡·克里玛(IvanKlima,1931—),捷克著名作家,和哈维尔、昆德拉并称捷克文坛的三驾马车。将重大历史事件与日常生活细节相提并论,这并不是我们常说的“向前看”,而是将两个全然不同的范畴联系起来的存在隐喻,正是这个纯粹卡夫卡式的回答,为我们提供了理解这位作家及其作品的关键。
克里玛1931年生于布拉格一个犹太家庭,父亲是位电机工程师。他十岁时就随父母被关进纳粹集中营,在那里度过三年多时光,一直到“二战”结束。悲惨贯穿了他的童年,他的所有儿时伙伴都死在了毒气室,这段经历无疑渗透到了他后来的创作中,形成了他的个人风格。1956年,克里玛从著名的布拉格查理大学语言学院毕业,任一家出版社的编辑,并从1960年开始发表小说和戏剧。自1964年到1968年期间,他一直在当时最负盛名的一家知识分子周刊任文学主编。作为一位曾在纳粹集中营中待过的作家,克里玛对自由的敏感必然会与现实社会发生冲突。最初他感谢新政权带来的解放,但随着经验的增长,他越来越意识到,基于反抗压迫的革命并不一定就会导向自由和正义的社会,所以在“布拉格之春”中,他表现得相当活跃。当这一改革运动随着苏军坦克的入侵而告结束后,克里玛去了美国密执安州一所大学,在那里做了一年访问学者。之后他谢绝了朋友的劝告并回到捷克,但随即就失去了工作,为了生计,他做过短期的救护员、送信员和勘测员助手,同时仍作为一个自由撰稿者继续写作,这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是很普遍的事。
有二十年时间,他的作品在捷克国内完全遭到禁止,只能以萨米亚特(地下出版物)文学的形式在读者中私下流传。这些作品与哈维尔、瓦楚利克、昆德拉等人的作品一道,构成了当代捷克的另一种文学史。1989年发生“天鹅绒革命”,他的作品重新得以出版,此后他开始担任国际笔会中心捷克分会主席,后改任副主席至今。接踵而来的是,他的文学声誉日隆,在捷克的读者群甚至超过昆德拉,成为90年代捷克的代表作家,一部作品的销量在国内就达十余万册。除了其作品本身的艺术成就外,这大概也是因为他不像昆德拉那样最终移居国外,而是一直坚持留在国内写作,所以更能与当代捷克人的情绪相通。用克里玛的话说,他的作品试图表现的是一种“布拉格精神”。在这个意愿的驱使下,他写出了《我快乐的早晨》及其他许多作品,如《我的初恋》、《爱情与垃圾》、《被审判的法官》、《我金色的贸易》、《等待黑暗,等待光明》以及随笔集《布拉格精神》等,这些作品都已被译成了多种文字,并受到世界文坛愈来愈多的关注和好评。
对任何一名捷克人而言,“你是怎么熬过来的”这问题都不仅是属于个人的,也是属于一个民族的。克里玛的创作就很清楚地表明,他的作品植根于他个人的命运,而他个人的命运又植根于民族的命运。在历史上,捷克民族属于古斯拉夫族的一支。早在公元9世纪,他们的祖先就建立起自己的国家,笃信天主教及以后的新教。16世纪捷克并入奥匈帝国,成为哈布斯堡王朝治下的一个属地。在20世纪的大部分岁月里,捷克又先后经历了德国纳粹占领和苏联占领,尤其在东西方冷战时期,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它长期属于分裂的欧洲的一方,丧失了国家的特性。但无论有多大的压制,民族和个人的特性仍然能借助于文学,穿过重重的政治帷幕传达出来。相对于捷克的政治地位,它的文学无论其成就还是影响,都早已是世界性的了。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捷克人在斯拉夫民族中是最古的人民,也有着最富的文学。”这话并不过誉。对中国读者来说,这块波希米亚的土地富饶而迷人,似乎特别适合于文学的生长,从这里走出的作家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如群星灿烂,凸现在我们远眺世界的视野中。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读者今天大概还能记得哈谢克的名字,《布拉格精神》封面他的《好兵帅克》曾在我们心里引起过长久的回响。到20世纪下半叶,又有一些捷克当代作家,如捷克前总统哈维尔,被称为先锋派重要代表的赫拉贝尔,以及中国读者已经非常熟悉的昆德拉等,更是由于其作品描写了极权社会中人的异化和荒诞,同时又处处表现出独特的波希米亚人文精神,而为世界文坛所瞩目。可以说,大多数捷克作家的作品其实都是在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在一个缺乏自由的社会中人们是怎样活下去的。
捷克人的气质里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退缩,这是一种讲究现实的人文精神,从哈谢克到克里玛,都可以寻绎出它的一脉相承。这种精神渗透了捷克人的生活,造成了一个非常大的现实空间。比如,在散文随笔集《布拉格精神》里,克里玛就曾指出,不同于周围国家,布拉格市中心的建筑都有一个不起眼的外表,这里的人在上世纪末还曾仿造过一座埃菲尔铁塔,但比例却要小得多,看上去就像是对伟大的一个幽默。
原因大概是悖谬的。一方面是饱受蹂躏的大陆民族有着对故土的挚爱和对苦难的敏感,一次次卷入大国之间的霸权争夺,经历了不同时代的极权统治,难以掌握自己的命运而充满对这个世界的荒诞感;另一方面则是经受过文艺复兴的理性的洗礼,融合了捷克、德意志和犹太三种居民的文化传统,在长期的兼容并包中也学会了妥协和适应。但退缩还不是完全因为这些,而是因为他们经历得太多,由于意识到生活和人性的全部本质,任何社会进步的政治神话都不能让他们轻易相信。事实上,20世纪无数人为的灾难往往都是源于这种政治神话。由这种怀疑而来的,则是对一切绝对和崇高的事物都本能地反感,所以捷克人的一大特色就是不喜欢张扬和激情,热爱生活本身而不是生活的意义,面对生活中的荒谬,他们从不会让自己燃烧起来,而是宁愿用幽默的顺从来消解。正是这个特征创造了捷克的艺术和文学。捷式的埃菲尔铁塔是这样,克里玛也如此。他的许多作品都有一个基本的情节,往往是一个被剥夺了工作权利的知识分子沦落到社会底层,为了物质和精神的需要,不得不从事各种低下的职业,接触到各种普通的人。这是一种沉默之后的生活,属于日常人生的一面,它也许有很多卑微之处,但却是实在的,所以值得一过。
回想起来,我们也曾有过英雄主义的时代,青春被豪情满怀地表演,想要奔向美好未来的崇高感觉占据了全部心灵,而同时身边的真实生活却被遗忘了,激情的浪潮退去,留下的是一片荒芜的沙滩。退缩其实是从各种绝对的价值观中的退出,它是一种生活的均衡感,一种消极而深刻的理性。退缩的结果不但产生了哈谢克,而且还产生了卡夫卡。
在《我快乐的早晨》这部小说中,克里玛以他惯有的从容和平静,讲述了一个世俗而没有激情的故事。小说作于1978年,恰好是“布拉格之春”十周年之际。它采用的是一种散漫的结构,有点类似今天的电视系列剧,在一个星期的时间长度里,叙述七个各自独立的故事,每个故事都以叙述者所从事的不同工作为基点,把周围的人物统摄进去。比如,《一个黑市的故事》、《一个感伤的故事》、《一个小偷的故事》等等,而以一个中心人物即叙述者本人贯穿其中,将每天发生的故事联缀起来,成为一部既松散又紧凑的中长篇。由于不像传统小说一个故事情节发展到底,喜欢新颖的读者可能会觉得别致。它与《我的初恋》和《我金色的贸易》组成了一个三部曲,都是通过一个叙述者的视点,讲述几个相对独立且带有自传性的故事。这种形式大概更能体现出克里玛的创作理念,即真正的生活不是暂时决定人们命运的政治,而是在这种政治下普通人广泛的源远流长的日常生活。
小说以60年代末那场举世闻名的政治动荡后令人窒息颓唐的时代为背景,其中的主人公身上可以看出克里玛本人的影子。第一人称的“我”即作者本人是一个作家,在苏联军队入侵捷克后失去了工作(这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事),迫于生活,他混迹于社会底层,干过鱼贩子、护理员、建筑工等活,小说通过他的视点,勾勒出一幅世俗社会的群体景观:黑市商人、护士、经理、牧师、店员、教授。各色人等,面目不一,各有各的活法。作者笔下的世俗生活自在而生动,处处见出他对植根于波希米亚土壤的这种生活的理解和同情。在他看来,那是一片只与个人生活有关的广大水域,尽管政治常常也会侵入其中,但它最终不过是浮在表面的泡沫,不会改变生活延续了几千年的基本流向,甚至也改变不了它本质上的无意义。读克里玛的小说,人们会想到昆德拉的作品,他俩都同样表现了极权制度下的意识形态话语对生活和人性的扭曲,以及处在一个封闭社会中的人们所面对的悖谬。但如果说,昆德拉更偏重于对伪崇高(他称之为Kitch)的批判,克里玛则更倾向于对世俗的认同。而且,克里玛似乎也不喜欢观念的东西,他注重的是生活中的形象,对于昆德拉总是将人物分成抽象的各种类型,他颇不以为然,认为昆德拉笔下的捷克人没有个性,肤浅得像外国记者的分析报道。比较起来,克里玛的写作风格或许更像19世纪的俄国作家契诃夫,更关注日常存在中的凡人小事,那些属于私人性领域的自在和无意义,比如人生的劳苦、贫穷和粗鄙,不负责任的自私,图谋钱财的欺诈,以及放纵的情欲,等等。单纯的人物,单纯的事件,正是格雷亨·葛林所谓“通常的人生的回声”。
但这种通常的人生仍然是这个时代的,所以政治和性爱一直是当代捷克作家的两个主要题材。在克里玛的小说中,前者属于人们的公共生活,代表非人性的一面,阴暗而压抑;后者则属于人们的私人生活,代表人性的一面,真实而放松。小说里作者曾与他的情人在树林里做爱,可他们之间却几乎没有什么了解。要不是发现一个卖鱼女人贪图他的钱(她并不在乎他是一个人民敌人),作者还差点与这个刚刚认识的女人春风一度。作者的笔触是恣睢的,但单纯的性爱描写却显然不是他的目的。两三年前,一个捷克人曾告诉我,在过去的捷克,在政治无孔不入的那个年代,一切有思想的言行都会遭到禁止,没有书没有电影,唯有男女间的性爱是自由的,但捷克人在这上面并不就是那样随便,随便到没有任何过程和交流。捷克的作家对此津津乐道,道理恐怕还在于,性爱是生活中最基本的东西,为了抗拒令人窒息的社会现实,人们总得抓住一点实在的什么,比较长久的,作为他们的庇身之地,尽管这种实在往往仍属于虚幻。在读者看来,其实是将一个希望破灭之后的社会压抑着的气氛和弥漫着的肉欲展示给人们。小说里,作者与多年前的情人久别重逢,可他们却找不到过去幽会的地方,结果旧梦难圆。克里玛对悲剧人生的感觉是敏锐的,正由于有虚妄做人生的底子,书中对世俗生活的描写才不显得庸俗,那些没有名目和结果的挣扎,才表现了现代人普遍的存在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