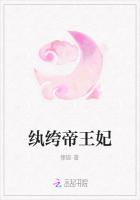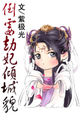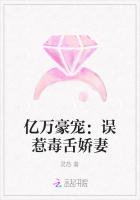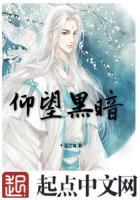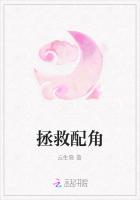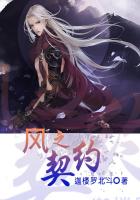黑海地区拥有悠久而璀璨的文化,是多个民族的发源地,希腊、波斯等古国的殖民地,黑海北面的大草原是罗斯国发源地,而东正教源国拜占庭则隔黑海相望,这里又是俄罗斯向西南部扩张的前线和俄罗斯各民族文化的冲突点,同时是俄罗斯文学中许多著名作家的出生地或灵感来源地。普希金、果戈理、莱蒙托夫、托尔斯泰、高尔基等著名作家都曾从黑海沿岸地区获得灵感,写成了传承千古的优秀作品。
从地理概念上讲,黑海地区指西起希腊,东至高加索,南达土耳其,北括乌克兰南部的广大地区。由于本文选择俄罗斯文学作品作为文本,文中“黑海”具体指黑海东部和北部沿岸地区,包括乌克兰南部、克里米亚半岛和高加索地区。这三个地区民族众多,政权更迭频繁,似不应统一到“黑海地区”这一概念之下,但相对于俄罗斯,这三个地区曾具有同样的意义:帝国南部边疆、异族文化(伊斯兰教、多神教)区、流放地。这三个意义使得这些地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相对于俄罗斯腹地都是“异域”的形象。因此把它们合并为一个概念有合理性。
根据文化地理学理论,地理空间不仅是自然地貌,还包含着在此地理环境中扎根的文化。本文即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黑海”这一概念:其中既包含黑海地区的自然环境,又包含在此自然环境中发源的文化。
阿鲁秋诺娃认为,形象属于认知概念,是意识形成过程中的一个关键环节。被知觉感知的客体对象的形式在人的意识中与其实体分离后,与精神和思想的范畴结合在一起,在此基础上复制再现出它的形象。由此看来,俄罗斯文学作品中对黑海地区的再现,必然与俄罗斯民族世界图景中的精神范畴结合在一起。
张冬梅认为“形象是对客体对象的完整再现,其完整性不仅在于对事物外部特征的综合,还在于它包含了事物的内容特征;也就是说,除了必须具备事物的外形,还必须有意义”[2](36),她同时认为,形象是观念的隐含形式。这样,就有可能从形象的特征中析出形象的内在涵义,特别是形象中所隐含的观念。
“观念作为文化的基本单位,其内涵中民族因素的总合构成了民族的世界观、世界形象乃至图景。”[2](25)因此,某民族的世界图景可以通过若干超个体观念来体现,而这些观念又是通过具体形象,尤其是该民族文学作品中的形象来体现的。然而,形象是复合性的,虽然在一定时期内其中蕴含的观念相对稳定,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形象与观念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这就使得形象内涵的观念可能随着形象被再次创作而产生变化。同时,虽然观念本身的意义保持不变,但它在具体形象中的表现形式也可能发生变化。最终该形象有可能转而表现其他观念(或观念体系)。这时,该形象在文学作品中的作用就改变了。
根据洛特曼的观点,“家园”和“道路”这两个基本观念在认知空间范畴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们对立共存,缺一不可。它们之间的张力是运动和发展的根本原则。俄罗斯民族世界图景给予“家园”和“道路”以重要地位,它们在卡劳洛夫编纂的《现代俄语联想大辞典》中列居第一位和第十二位。
“家园”代表定居、安全、内部;“道路”与“家园”相对,代表自由、危险、外部。早期文学作品中描写黑海地区的时候几乎都把它当做旅地来处理。黑海形象内涵的观念在俄罗斯作家的眼里首先是“道路”观念:这一地区隔离于俄国腹地,是“异己”文化区域,是隐含着未知、处处危险的待垦地。在这片土地上,俄罗斯文化是“外来”文化。然而,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黑海形象中蕴含的观念又有了变化,所表现出的“道路”观念特征逐渐弱化,甚至有逐渐向“家园”方向转变的趋势。这样,可以通过分析黑海形象所内涵的观念之变化,来分析黑海形象在俄罗斯文学中含义的变迁,推导出俄罗斯文学的发展态势。
经过19世纪的征讨,黑海地区在十月革命前基本全部划入沙俄国土。[1](地图4)苏联时期,这一地区完全被划入苏联版图。虽然历史上该地区中许多民族曾争取民族独立,但都或未成功,或未被广泛承认,只是直到苏联解体之后才获得被广泛承认的独立。同时,俄罗斯文化与各少数民族独立文化间的关系问题也渐渐浮现。因此,苏联解体是一个转折点。
本文即是基于上述观点,以苏联解体作为分水岭,对比两段时间内黑海形象内涵的演变。
一、苏联解体前文学中“黑海形象”的观念特征黑海地区在文学中的形象首先表现了“道路”观念。“道路”观念有许多特征。根据张冬梅的研究,在俄罗斯民族世界图景中它最鲜明的特征是:危险、自由、朝圣。笔者认为,“道路”还有一个特征——“相遇”。
“道路”观念特征的表现
(1)危险
这一特征出现得较早。它最初表现在《伊戈尔远征记》中伊戈尔王公对黑海北岸波洛夫齐人失败的征讨中,后来又表现在神秘的黑海自然风光中。风光的神秘性是通过运用神话传说实现的。普希金在《高加索的俘虏》中把厄尔布鲁士山峰比作可怕的双头巨人;在果戈理的《可怕的复仇》中,喀尔巴阡山下镇压着可怕的巨尸,巨尸一翻身,山区就地震;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中,时时出现对高加索地区险恶的自然环境的描写。
危险不仅体现在神秘而未知的自然中,还体现在该地区与俄罗斯东正教文化对立的“异己”文化中。作为东正教“神圣骑士”化身的鲁斯兰所遭遇的危险来自魔法师黑海王,虔诚的玛丽亚所遭遇的危险来自她那不信东正教的魔法师父亲,《当代英雄》中毕巧林遭遇的危险来自黑海上的不法走私分子。
黑海形象从最初就被这些创作赋予了危险的“异己”内涵。需要注意的是,虽然黑海形象意味着“危险的道路”,但这些危险最终被俄罗斯的代表所克服:鲁斯兰战胜了黑海王,魔法师父亲被东正教苦修僧所灭,毕巧林破坏了走私者的生活并迫使他们离开塔曼。
(2)自由
相对于“家园”,“道路”意味着自由、无拘无束。对于被流放的诗人,黑海地区意味着脱离监视的自由。在普希金的《致大海》中,黑海是“自由的元素”,是通向关押拿破仑的圣赫勒拿岛的道路。而莱蒙托夫写道:
别了,满目垢污的俄罗斯,
奴隶的国土,老爷的国土,
你们,卖身于权贵的人们,
还有你们,天蓝色的军服。
或许在高加索山岭那边,
我可以避开你们的总督,
避开那无所不闻的耳朵,
避开那无所不见的眼目。[3](152)
“自由”还指当地流浪民族(尤其是茨冈人)追求自由、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追求个体自由的流浪民形象起源于普希金《茨冈人》中的金斐拉,在高尔基的《马卡尔·楚德拉》中得到了详尽的阐释。流浪民族文化本身是没有“家园”、一直在“路上”的文化。选择流浪民族作为黑海地区居住者的形象代表,这本身就是把黑海作为“道路”空间来塑造。而且,在塑造当地非茨冈居民的形象时,也经常着重表现他们追求自由的决心,对其他方面的特征并不强调。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俄罗斯诗人对黑海形象的描述与其自身的追求是密不可分的。
(3)相遇
在传统文学作品中,相遇主要指的是原住民文化和俄罗斯文化的“相遇”。这个“相遇”是以冲突的形式来表现的。
《茨冈人》描写了贵族青年阿乐哥无法真正融入茨冈文化的悲哀。托尔斯泰继承普希金的这一主题,在《哥萨克》中描写了自愿融入哥萨克人中却无法理解哥萨克文化的军官奥列宁。需要指出,托尔斯泰在继承上有所发展:不同于阿乐哥,奥列宁融入哥萨克人的愿望不仅出于他对上流社会的厌倦,还由于他热爱高加索的大自然,对哥萨克生活之热爱是从对大自然之热爱发展来的——他认为哥萨克代表着自然、自由与力量。然而,作为文明人他无法接受人的“自然”式死亡,最终只能离开。文化习俗的矛盾又体现为文明与自然的矛盾。
“相遇”必然涉及双方。然而,早期作品中或多或少地体现着对原住民文化的忽视或贬低。普希金在《茨冈人》篇末写道:
但你们也没有什么幸福,
天地间的可怜的子孙们!
……
而在破破烂烂的帐篷下,
定居的也只是痛苦的梦。
你们的漂泊无定的屋宇,
荒野里也不能避开穷困,
到处是无可逃躲的苦难,
没有什么屏障摆脱命运。[4]
而莱蒙托夫在《童僧》中叙述,格鲁吉亚王把土地交给俄罗斯人后,格鲁吉亚就迎来了春天。这些描写首先是从俄罗斯人的角度出发的。在这些作品中,“相遇”还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相遇”,而是一方从自己的角度对另一方进行评价。山民文化仍然被看作异己的、需要消灭的。
部分作品是从原住民角度创作的。莱蒙托夫的《伊斯梅尔—贝》从契尔克斯人的角度揭露“淫乱”的欧洲文明给契尔克斯人带来的灾难,批评被欧洲文明熏染的人“不会在递手时心灵也奉献”。托尔斯泰在《哈吉穆拉特》里塑造了山民领袖哈吉穆拉特的形象。他野蛮好勇,杀人如麻,但具有许多优秀品质。在他的映衬下,俄罗斯人——从军官直到沙皇——都显得猥琐软弱,虚伪自私。这些形象的确出于俄罗斯作家对山民文化的理解,体现了俄罗斯文学的人道主义立场。这些人身上的民族特点并不显著,作品中加以描绘的是他们作为“人”的优秀品质,如守信、坚强、责任心强等。也就是说,已经抛开身份上的相异,从普世人性角度审视他们,但这个时候俄罗斯人还没有意识到山民文化的价值。然而,这毕竟为后来黑海形象内涵的转变奠定了基础。黑海形象中蕴含的观念由“道路”转向“家园”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4)诗人的朝圣之途
纵观文学史,黑海沿岸是许多著名诗人和作家的诞生地或灵感来源地。普希金在克里米亚流放期间获得灵感;莱蒙托夫幼年曾在高加索居住,深爱这块土地;果戈理生于乌克兰波尔塔瓦省,极为关注乌克兰民间文化;托尔斯泰在高加索服役期间开始创作,且一生没有离开高加索主题;契诃夫生于马尔马拉海岸的塔甘罗格;阿赫玛托娃生于敖德萨,并选择具有鞑靼血统的曾祖母的姓氏作为笔名;巴别尔生于敖德萨;帕乌斯托夫斯基在乌克兰乡下长大;索尔仁尼琴生于北高加索的基斯洛沃茨克……因此,黑海地区尤其是高加索成了俄罗斯诗人的“第二摇篮”。
叶赛宁写道:
自古我们俄罗斯的诗坛
一直向往那陌生的地方,
高加索,唯有你比谁都
更能拨响那神秘的雾障。[5]
在这首诗中,叶赛宁把高加索作为创作灵感的圣地,向其祈求诗句,而他也正是从创作高加索题材的诗歌开始扬名的。
同样,叶夫图申科也写道:
哦,格鲁吉亚,
我们的眼泪已经擦干,
你是俄罗斯诗歌的
第二摇篮。
一旦忘记
格鲁吉亚,
在俄罗斯要成为诗人
便是空话。[6]
在《十二把椅子》里,大家批评里亚皮斯专写无聊的打油诗,他反驳道:“我写了高加索!”这里显然是用高加索来指代优美、崇高的诗歌。
黑海被呈现为一个文化符号,象征着俄罗斯缪斯的居所。它是通向诗人的途径,是被向往的陌生的地方,是诗人朝圣的道路。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黑海形象内涵在俄罗斯文学的一再诠释中得到的发展。然而,无论是把这个地区作为诗歌灵感的源头,还是讲述这一地区的历史传说,其中都表现了作为强势一方的俄罗斯文化和俄罗斯民族对弱小的当地原住民的忽视。在俄罗斯传统文学创作中,黑海地区的原住民某种程度上是“他者”和“失声者”。黑海地区对于俄罗斯作家是需要克服以便通向实现自我的“道路”空间。
对黑海地区本来面貌的忽视是俄罗斯作家中常见的倾向。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俄罗斯作家和诗人把黑海地区作为一个“理想化”空间来对待。对黑海的描述中无一不渗透着他们自己的理想和追求。这在增强艺术性的同时不可避免地“遮蔽”了黑海地区的本来面貌。俄罗斯作家对素材、人物形象、情节等的选择和塑造都遵从俄罗斯的审美法则,使当地居民的真正形象隐蔽在俄式审美观之后。对地区的“理想化”与对原住民的忽视是一体两面,互不可分的。
二、苏联解体后文学中“黑海形象”的观念特征在苏联解体后的文学作品中,黑海形象有渐渐淡出的趋势。这一是由于苏联解体后,黑海沿岸很多地区转而属于周边共和国,与俄罗斯本土关系削弱;二是由于俄罗斯把目光转向东方,文学描述的重心渐渐转到俄罗斯的亚洲地区;三是由于黑海地区少数民族向俄罗斯腹地迁徙,使得作家开始关注少数民族在俄罗斯文化环境中的问题而较少考虑黑海地区原住民的文化问题;四是对原住民社会文化研究的发展使黑海地区渐渐呈现本来面貌而失去了原来的“理想化”形象。
其中第一个原因最明显,但并不是决定性原因:这些地区多数还处于俄罗斯势力范围中,且政治国境线无法真正斩断文学艺术的纽带。第二和第三个原因是外部原因。而第四个原因是根本性原因,是由于黑海失去了其象征地位而导致的。
虽然描写黑海的文学作品数量变少,但仍有部分作品反映了黑海形象,且其中蕴含的观念不仅对传统有所继承,也有所发展。在此我们通过对照,来审视黑海形象中的观念内涵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些变化又意味着什么。
(一)“道路”观念
“道路”观念仍然是黑海形象中很典型的观念。我们通过分析相同特征,来作一对比。在上文提到的四个特征里,仍然比较突出的是“相遇”和“自由”两个特征,而其他两个特征已经消失了。
1.相遇
解体后的作品中延续了传统问题:当俄罗斯文化与原住民文化相遇时,会发生什么。但问题有所发展:首先,“相遇”涉及的不仅是双方相遇,还加入了西方文化;其次,相遇双方的态度和地位有所变化。
这些问题在古拉·希拉切夫的《你好,达尔加特!》这篇小说中得到了展现。西方文化入侵俄罗斯,又进入高加索地区,对原住民的伊斯兰文化造成了很大冲击。许多年轻人腐化堕落,加入性解放运动,把宗教当成掩饰的工具。针对道德堕落,虔诚的穆斯林中出现了原教旨主义者。虽然俄罗斯也是西方文化渣滓入侵的受害者,但由于历史积怨,伊斯兰教徒认定这些渣滓是从俄罗斯来的,结果双方矛盾与日俱增。
这篇小说改变角度,用穆斯林的眼光看待文化入侵问题,不再单纯从俄罗斯人角度作评判,也没有把穆斯林塑造成嗜杀好勇的野蛮人,而是考虑到了他们的处境,宽容地看待他们。
小说反映了俄罗斯与伊斯兰民族矛盾的荒谬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