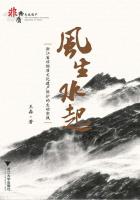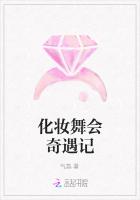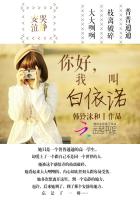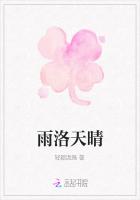至30年代,钱玄同的疑古态度愈发坚定,他重申:“凡治历史科学,第一步必要的工作是‘审查史料的真伪’”,钱玄同:《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钱玄同文集》第4卷,第135页。“总而言之,咱们现在对于古书,应该多用怀疑的态度去研究它们,断不可无条件地信任它们,认它们为真古书、真事实、真典礼、真制度。与其过而信之也,宁过而疑之,这才是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钱玄同:《〈左氏春秋考证〉书后》,《钱玄同文集》第4卷,第304页。他甚至为此不惜与同门吴承仕分裂,黎锦熙曾回顾说:“他的同门学友吴承仕先生,向来教的一门‘三礼名物’,民廿二,他一定要废除,大家以为是因为两人当时宗旨不合,但钱先生实在是不慊于吴先生之专据《三礼注疏》,不辨‘古文家’说之疑伪而一律认为真实”。见《钱玄同先生传》,《钱玄同印象》,第77页。与此相较,胡适虽在20年代初屡屡鼓励顾颉刚“宁可疑而过,不可信而过”,胡适:《适之先生评》、《告拟作〈伪书考〉长序书》、《自述古史观书》,《古史辨》第1册,第12、15、23页。但到了1929年却向顾颉刚宣称:“我不疑古了,要信古了!”顾颉刚:《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我与古史辨》,第198页。由此看来,钱玄同在30年代仍提倡“与其过而信之也,宁过而疑之”,显然更具有“疑古”的彻底性。
而作为“古史辨运动”的领袖,顾颉刚也一再提及钱玄同的鼓励。他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就说:“要是适之、玄同两先生不提起我的编集辨伪材料的兴趣,奖励我的大胆的假设,我对于研究古史的进行也不会这般地迅速。”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我与古史辨》,第89页。在晚年所撰《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一文中,他也写道:“我的《古史辨》的指导思想,……从近的来说则是受了胡适、钱玄钱玄同为顾颉刚编《古史辨》第二册题签同二人的启发和帮助。”顾颉刚:《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我与古史辨》,第197页。
第二,启发顾颉刚从“辨伪书”拓展到“辨伪事”。
如前所述,顾颉刚与钱玄同最初是通过编辑《辨伪丛刊》结识的,而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他曾经咨询钱氏:“我们的辨伪,还是专在‘伪书’上呢,还是并及于‘伪事’呢?……我们或者拿辨‘伪事’的算作《辨伪丛刊》的‘甲编’,辨‘伪书’的算作‘乙编’;……先生以为何如?”顾颉刚:《论〈辨伪丛刊〉分编分集书》,《古史辨》第1册,第23页。对此,钱玄同明确答复说:“我以为二者宜兼及之,而且辨‘伪事’比辨‘伪书’尤为重要。崔东壁、康长素、崔觯甫师诸人考订‘伪书’之识见不为不精,只因被‘伪事’所蔽,尽有他们据以驳‘伪书’之材料比‘伪书’还要荒唐难信的。……所以我认为辨‘伪事’比辨‘伪书’为尤重要。”钱玄同:《论近人辨伪见解书》,《钱玄同文集》第4卷,第221页。
今天看来,正是由于从“辨伪书”拓展到“辨伪事”,而且强调后者,才使“古史辨运动”超越了传统疑古辨伪的范围,上升为“疑古”史学。而在这一方面,钱玄同对顾颉刚的启发是极为关键的,台湾学者杜正胜便明确指出:“疑古之风演成一股潮流,虽数顾颉刚出力最多,但钱玄同才是灵魂人物,唯有他的辨‘伪事’更甚于‘伪书’的明确主张,疑古作风才进入史学的领域。”杜正胜:《从疑古到重建——傅斯年的史学革命及其与胡适、顾颉刚的关系》,《中国文化》第12期,1995年秋季号。
第三,鼓励顾颉刚从“辨伪子”、“辨伪史”发展到“辨伪经”。
钱玄同继承了历代疑古辨伪的成就,但他在此基础上又有所发展。他曾经向顾颉刚指出:“我觉得宋以来有四个大学者,本来都是可以有大成就的,因为被‘经’罩住了,以致大蒙其害。四人者,朱熹、颜元、章学诚、崔述是也”,钱玄同:《论〈诗〉说及群经辨伪书》,《钱玄同文集》第4卷,第234页。“‘六经’在古书中不过九牛之一毛,但它作怪了二千多年,受害的人真是不少了。它作怪时用的许多法宝之中,‘伪书’和‘伪解’就是很重要的两件,我们不可不使劲来推翻它”。钱玄同:《答顾颉刚先生书》,《钱玄同文集》第4卷,第250页。
鉴于此,钱玄同一再鼓励顾颉刚勇于“疑经”。他说:“我以为‘经’之辨伪与‘子’有同等之重要——或且过之。因为‘子’为前人所不看重,故治‘子’者尚多取怀疑之态度;而‘经’则自来为学者所尊崇,无论讲什么,总要征引它,信仰它,……故‘伪经辨证集说’之编纂尤不容缓也”,钱玄同:《论编纂经部辨伪文字书》,《钱玄同文集》第4卷,第228页。“过去的学术界,是被‘宗经’的思想支配的。……所以无论治文学的,治历史的,治政治的,乃至治其他种种国故的,无不宗经——宗《十三经》。他们尽管不信任‘史’和‘集’,甚至不信任‘子’,但一定信任‘经’。……所以我以为我们现在对于治国故的人们,应该供给他们许多辨伪的材料;而辨伪‘经’的材料,比辨伪‘史’、伪‘子’、伪‘集’的材料,尤其应该特别注重”。钱玄同:《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钱玄同文集》第4卷,第136—137页。
在具体实践中,钱玄同也身体力行地积极“辨伪经”。他在1922年12月24日的日记中即曾写道:“我极想采王充以来直到现代凡‘疑经’之论汇为一编,为推翻‘六经’之参考资料,……辨伪经实比辩伪子、伪史大,其重要因为子、史向不为人重视,打倒几部伪的,大家并不觉得什么,打倒伪经,实为推倒偶像之生力军,所关极大也,且此物不推翻,则非信为真正古史,即尊为‘微言大义’,于历史上、于学说上皆有损害也”。《钱玄同日记》第5册,1922年12月24日条,第2453—2454页。在1923年2月9日致顾颉刚信中他再次表示:“一年以来,我蓄志要搜集关于‘群经’之辨伪文字。我以为推倒‘群经’比疑辨‘诸子’尤为重要。因‘诸子’是向来被人目为‘异端’的,……若‘群经’则不然。……然正惟其如此,咱们所肩‘离经叛道’之责任乃愈重。”钱玄同:《论〈诗〉说及群经辨伪书》,《钱玄同文集》第4卷,第233页。
从后来“古史辨运动”的发展方向来看,钱玄同这种观点显然具有转折性意义。顾颉刚即曾回顾说:“在九年冬间,我初做辨伪工作的时候,原是专注目于伪史和伪书上;玄同先生却屡屡说起经书的本身和注解中有许多应辨的地方,使我感到经部方面也有可以扩充的境界”。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我与古史辨》,第55页。胡适也评价说:“崔述推翻了‘传记’回到了他认为可靠的‘经’,我们决定连‘经’都应考而后信,在这一方面,我们得着钱玄同先生的助力最大。”胡适:《介绍几部新出的史学书》,《古史辨》第2册,第336页。
第四,在许多方面启发丰富了顾颉刚的“古史辨”学说。
众所周知,顾颉刚“古史辨”学说的基础是“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亦即“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我与古史辨》,第58页。也正所谓:“时代越后,知道的古史越前;文籍越无征,知道的古史越多”。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古史辨》第1册,第65页。而客观来看,这种观点源自于崔述,钱穆就指出“颉刚史学渊源于崔东壁之《考信录》,变而过激,乃有《古史辨》之跃起”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67页。,胡适也说:“这个见解起于崔述。崔述曾说:世益晚则其取舍益慎,世益晚则其采择益杂。”胡适:《古史讨论的读后感》,《古史辨》第1册,第192页。但值得一提的是,在“古史辨派”中最早注意崔述这一观点的是钱玄同。早在1912年1月26日的日记中,他便写道:“崔先生谓凡秦汉经师传授,不可信者甚多,盖愈远而人愈详,如《七略》详于《史记》,东汉人说详于《七略》,逮三朝六朝,以至唐世之《经典释文》则传述人最为详备,岂有愈远愈详之理?则必不可信。……此说最为坚确。”《钱玄同日记》第3册,1912年1月26日条,第1043页。而从顾颉刚萌发“层累说”的经过来看,他与钱玄同曾有过密切交流,其首次揭橥“层累说”的文章即是《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由此来看,他对于崔述这一观点的关注,或许与钱玄同的启发不无相关。
此外,顾颉刚关于伪史料的“移置”主张或许也是受到钱玄同启发。这里首先必须澄清的是,“古史辨派”虽然力辨诸书,但也并未完全抹杀伪书的价值,而是主张将其“移置”至适当的时代。关于“移置”,时下学界多引陈寅恪1930年6月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的阐述:“以中国今日之考据学,已足辨别古书之真伪。然真伪者,不过相对问题,而最要在能审定伪材料之时代及作者,而利用之。盖伪材料亦有时与真材料同一可贵。如某种伪材料,若迳认为其所依托之时代及作者之真产物,固不可也。但能考出其作伪时代及作者,即据以说明此时代及作者之思想,则变为一真材料矣”。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80页。这固然不错,但是却忽略了“古史辨派”在这一问题上的贡献。实际上,较早提出这一主张的正是“古史辨派”。朱希祖早在1919年便提出:“证明是伪,即考明此书出于何时,即定为何时的政论或政策;其他一切伪书,皆须考明出于何时。关于文学的,即定为那时的文学;关于哲学的,即定为那时的哲学。盖伪造亦有伪造的学说,亦不可一概抹杀”(《整理中国最古书籍的方法论》,《北京大学月刊》第1卷第3号,1919年3月)。梁启超1922年也说:“辨别伪书,凡以求时代之正确而已,不能因其伪而径行抛弃。例如谓《管子》为管仲作,《商君书》为商鞅作,则诚伪也,然当作战国末法家言读之,则为绝好资料。谓《周礼》为周公致太平之书,则诚伪也,然其中或有一小部分为西周遗制,其大部分亦足表现春秋战国乃至秦汉之交之时代背景,则固可宝也”(《先秦政治思想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2页)。不过他们二人均未对此做更进一步的系统阐述。
在1923年发表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顾颉刚就曾阐发说,“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我们即不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即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古史辨》第1册,第60页。这无疑说明他此时已萌发了“移置”伪史料的主张。时至30年代初期,顾颉刚又一再表示:“倘使不用了信仰的态度去看而用了研究的态度去看,则这种迂谬的和伪造的东西,我们正可以利用了它们而认识它们的时代背景”,顾颉刚:《中国上古史研究课第二学期讲义序目》,顾颉刚编:《古史辨》第5册,第259页。“许多伪史料,置之于所伪的时代固不合,但置之于伪作的时代则仍是绝好的史料:我们得了这些史料,便可了解那个时代的思想和学术。……所以伪史的出现,即是真史的反映。我们破坏它,并不是要把它销毁,只是把它的时代移后,使它脱离了所托的时代而与出现的时代相应而已。实在,这与其说是破坏,不如称为‘移置’的适宜。一般人以为伪的材料便可不要,这未免缺乏了历史的观念”。顾颉刚:《古史辨第三册自序》,《我与古史辨》,第131—132页。至此,“移置”说显然已正式形成。
此后,顾颉刚还屡屡澄清说,“我们的辨伪,绝不是秦始皇的焚书。不过一般人确实常有焚书的误认,所以常听得人说:‘顾颉刚们说这部书伪,那部书伪。照这说法,不知再有什么书可读!’这真是太不了解我们的旨趣,不得不辨一下。我们辟《周官》伪,只是辟去《周官》与周公的关系,要使后人不再沿传统之说而云周公作《周官》。至于这部书的价值,我们终究承认的。要是战国时人作的,它是战国政治思想史的材料。若是西汉时人作的,它便是西汉政治思想史的材料。……这原是以汉还汉,以周还周的办法,有何不可”顾颉刚:《古史辨第四册序》,《我与古史辨》,第154—155页。,并明确提出:“我们只要把战国的伪古史不放在上古史里而放在战国史里,把汉代的伪古史也不放在上古史里而放在汉代史里。这样的结果,便可使这些材料达到不僭冒和不冤枉的地步而得着适如其分的安插。这便是我们今日所应负的责任。”顾颉刚:《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古史辨》第7册上编,第62—63页。
由此可见,“古史辨派”并非如有些人认为的那样,完全抹杀伪书的价值,而是主张将之“移置”至适当的时代,以作那一时代的研究材料。而且从提出的时间来看,“古史辨派”比陈寅恪要早得多。
值得一提的是,“古史辨派”中最早提出这一见解的是钱玄同。早在1922年9月1日,钱玄同在致胡适信中便指出:“自来造假书最有名的人是刘歆和王肃,但此二人所造的伪书,尽有他的价值,未可轻于抹杀。”钱玄同:《致胡适》,《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109页。1923年4月4日,他又在日记中说:“辨伪诚是整理国故中第一件大事,但辨伪的意思完全为求真相,就是对于大家都说是张三做的文章,我们觉得有些可能,于是考证,考证的结果断定这是李四做的,不是张三做的,如此而已,至于张三李四的好坏优劣这是另一问题。李四的话也许简直是胡说,也许略有道理,也许和张三有同等的价值,也许过于张三远甚,绝不可一概抹杀。比如《礼运》和《周礼》,说它不是孔丘和姬旦作的,这是不错的,至于它的价值,不但《周礼》的组织远非姬旦所能梦见,即《礼运》的思想恐怕也比孔丘要进步了。”《钱玄同日记》第5册,1923年4月4日条,第2622页。而在1923年5月25日致顾颉刚信中,他也写道:“若讲伪书的价值,正未可一概而论。乱抄乱说的固然不少,至于《易》之《彖》、《象》、《系辞传》,如《小戴礼记》中之《礼运》、《中庸》、《大学》诸篇,如《春秋》之《公羊传》与《繁露》,如《周礼》,这都是极有价值的‘托古’著作。……不能因其非姬旦、孔丘所作便说是无价值。我很佩服姚际恒、崔述、康有为那样‘疑古’的求真态度,很不佩服他们那样一味痛骂伪书的卫道态度。”钱玄同:《答顾颉刚先生书》,《钱玄同文集》第4卷,第249页。1925年12月13日,他又再次致信顾颉刚说:“辨古书的真伪是一件事,审史料的虚实又是一件事。譬如《周礼》、《列子》,虽然都是假书,但是《周礼》中也许埋藏着一部分周代的真制度,《列子》中也许埋藏着一部分周汉间道家的思想。……就是假书也是一种史料哇。《周官》如其是刘歆他们造的,便是关于他们的政治思想的史料;《公羊》便是周汉间一部分儒者的思想史料,或者就是董道士的思想的史料。”钱玄同:《论〈说文〉及壁中古文经书》,《钱玄同文集》第4卷,第265、2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