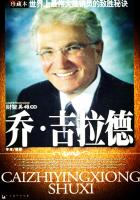占星术也就是星相学,中外都有,它是星相学家通过观测天象变化来占卜人世吉凶祸福的一种术数。古人为了认识星星、研究天体,便人为地把星空分成若干区域,中国称之为星宿(xiǜ),西方唤之为星座。星相学认为,天体,尤其是行星和星座,都以某种因果性或非偶然性的方式预示着人间万物的变化。德国哲学家卡西尔在其《人论》中就曾说:“人在天上所真正寻找到的乃是他自己的倒影和他那人的世界的秩序。”
占星术的最初目的是预卜某人一生的命运。后来发展为几个分支,一种是专门研究重大的天象和人类的关系,叫做总体占星术;一种是选择行动的吉祥时刻,叫做择时占星术;还有一种是决疑占星术,根据求卜者提问时的天象来回答他的问题。
占星术的出现可以追溯到很早以前。
国外的占星术起源于古美索不达米亚人的天体预兆。公元前18世纪到前16世纪的古巴比伦王朝,出现了第一本分门别类论述天体预兆的楔形文字的书。公元前6~4世纪,天体预兆学说传入埃及、希腊、近东地区和印度。后来经由印度僧人传到中亚。到了公元前3世纪,古希腊哲学家开始将星相学和古美索不达米亚人的天体“预兆”结合起来,星相学家相信,某些天体的运动变化及其组合与地上的火、气、水、土四种元素的发生和消亡过程有特定的联系。这种联系的复杂性,正反映了变化多端的人类世界的复杂性。有人把大小宇宙相对应的概念数学化。所谓“大宇宙”就是自然界的宇宙,“小宇宙”指人体。他们还把黄道十二宫进一步细分,认为五大行星在黄道不同的弧段上的作用不同,各有主次。星相学家们还发明了复杂的占星算术。公元2世纪时,古希腊的天文学家们大体上已把北天区域的星座确定了下来,而南天区域的星座的确定则是在环球航行成功之后、17世纪的事了。
希腊占星术也曾传入印度、伊朗,进入伊斯兰文化。17世纪后随着日心说的确立和近代科学的兴起,星相学失去了科学上的支持。但近年来星相学又在西方开始抬头,有人还试图将近代发现的外行星引入占星术中,并试图找出行星位置和人类生活的统计关系。
中国的占星活动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原始宗教崇拜。随着原始部落的统一以及阶级的出现,原始宗教对自然神的崇拜逐渐由崇拜天地众神变为崇拜单一的“至高无上”的神,殷商时代叫“帝”,周朝称为“天”。它被赋予社会属性和人格化,成为宇宙万物的主宰。天文与人文相联系,从而产生了原始的天命观。天命观认为,天象是天帝对人世态度的表征,日月经天,星辰出没,是天所安排的秩序;而一些罕见的天象如日月食、彗星、变星的出现,表明天的怨怒;五大行星的复杂运动则被认为是天含有深意的暗示或谴告。为了猜测天的意志,以规范人们的思想行动,于是便出现了占星术。
中国的占星纪事最早见于商代的甲骨文卜辞。当出现异常天象时,由专职的卜史根据观测到的星象变化提出卜问的问题,称“述命”,然后用火灼烤龟甲或牛的肩胛骨使其爆裂,裂纹就是兆象,成为判断吉凶的依据。最后卜史把验证情况刻在甲骨上,命辞和验辞便是卜辞。随着观测的天象资料积累越来越多,占星家可直接依据天象变化来预测人事吉凶,并将大量的占验情况记录汇集成书,这就是《占经》。《占经》是最早的天文著作,也是占星活动的经典或占验依据。早在商朝时期,古人对天象的观测已十分精细,并且逐步摸清并掌握了天体运行的一些重要规律。著名的二十八宿体系,可能就是在周朝初期确立下来的。在对天象观测实践中,古人将在天空中位置相对不变的星体称为恒星,以恒星为背景或坐标,据以观测日月和五大行星的运行规律。早在战国时期,古人已观测记述了120颗恒星的位置,而到了东汉,张衡作《灵宪》称:在中原地区能测得者,“为星二千五百”。
相比较而言,中国的天界比西方天界更系统、有序。例如,古希腊星座虽也有类似中国天帝的主神宙斯,但是,希腊星座的神话各自有其传说体系和渊源,众星座间的关系极其松散,因此星象体现出一种驳杂无序未经组织的自然状态。中国的天界则突出以北极帝星为中心,以三垣二十八宿为主干,构建了一个组织严密、体系完整、等级森严、居高临下、呼应四方的空中人伦社会,并成为星象占验的蓝本或主要依据。在古人看来,满天星辰都排列有序地自东向西运行,只有北极星不动,其他星辰都在围绕着它旋转。
此外,中国的星相学所比附和解释的天人关系更加玄妙和复杂。《史记·天官书》中记载了以五大行星占验的事件。五大行星原名岁星、荧惑、镇(填)星、太白、辰星,当其与五行相配,不但与方位、四时、礼义道德等挂钩,而且具有了木、火、土、金、水五种属性。占星家根据五星的属性,进一步引申出各星所司之事物:木星主年岁;火星司火旱;土星司五谷;金星司甲兵死丧;水星司大水。如果水星运行正常,说明阴阳调和,风调雨顺,否则就要“邦当大饥”。
五星的颜色也预示着吉凶,假如五星颜色随四季相应变化,就是吉,否则就是凶。五星的相互位置,三星、四星和五星的交会,都征兆着胜负、吉凶、祸福,如出现“五星连珠”天象被附会为“祥瑞吉兆”,而“荧惑守心”则被认为是凶兆。
此外,对某些尚未认识其运行规律的异常天象,古人大多视为凶兆。其中,日月的变异,被统治者视为最重要的征兆。日食被认为是大凶之兆,其次是彗星,彗星也不是经常出现的天象,当其出现,拖有长长的尾巴,以其形状如扫帚,《开元占经》称“彗星主扫帚”,附会为“除旧布新,改易君上”。这些附会常被一些野心家利用来发动政变。
前面提到二十八宿恒星分区体系,这种体系早在商末周初就已经出现了。二十八宿体系就是将天球黄道和赤道附近一周天的恒星自西向东分为二十八个不等分的星组,每组称为一个星宿,共计二十八宿。二十八宿与四陆(四维)之分相结合,演变为四象,表示天空东西南北四方区域的星象,每一区域分别以一种象形动物命名,即东宫苍龙之象、南宫朱雀之象、西宫白虎之象、北宫玄武(乌龟)之象,每象各含七宿。
二十八宿在我国民间流传甚广,汉代天文学家曾形容它为“苍龙连蜷于左,白虎猛踞于右,朱雀奋飞于前,灵龟圈首于后”。这实际上描述了我国中原地区初春季节黄昏后的天象。
中国占星术的论命与推运皆以二十八宿为准。
具体说来,三垣是指北天极周围的三个区域,即紫微垣、太微垣、天市垣。四象是指分布在黄道附近,环天一周的四个区域,即东方苍龙之相,西方白虎之相,南方朱雀之相,北方玄武之相。每象各分为七段,共计二十八宿。所谓黄道,是一个假想的带状区域,是一年当中太阳在天球上的视觉路径。具体说来,二十八宿包括下面这些星宿:
东方七宿:角木蛟,亢金龙,氐土貉,箕水豹,尾火虎,房日兔,心月狐;
南方七宿:井木犴,鬼金羊,柳土獐,轸水蚓,翼火蛇,星日马,张月鹿;
西方七宿:奎木狼、娄金狗、胃土雉、壁水蝓、觜火猴、昂日鸡、危月燕;
北方七宿:斗木豸、牛金牛、女土蝠、参水猿、室火猪、虚日鼠、毕月乌。
从上面的星宿名称可以看出,星体的命名有着明显的时代烙印。中国星体的命名和星区体系的划分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早期星体的命名直接反映了农牧社会的特点,并与古文字的象形有关。如牛郎、织女、箕(簸箕)、斗(盛酒器具)、奎(大猪)、娄(牧养牛马之苑)、毕(猎具,带网的叉子)、张(逮鸟之网)等;有的命名则出于古人的想象和传说,如东方苍龙的角(龙角)、亢(龙颈)、氐(龙足)、房(龙腹)、心(龙心)、尾(龙尾)等星宿,各以龙之一体命名,组合起来,东首西尾,如龙之腾跃于空。到了春秋以后,星名中逐渐采用帝、太子、后妃(勾陈)、上将、次相等帝王将相名称,并出现了离宫、大理、天牢、天廪、华盖等国家机构、建筑、庄园、器用等星名。星座也开始有尊卑,星体命名被打上了阶级烙印。
中国古代对天区的划分,除上述三垣二十八宿外,还有周天十二次的划分法。即根据岁星(木星)十二年运行一周天,自西向东地将周天分为十二等分,每等分代表一个星区,用以表示岁星每年所在位置。星象家将十二星区分别与人间的十二区域相配对,称为“分野”。人间的十二区域也叫十二辰,就是古代十二个诸侯的封地,以封国表示就是吴(越)、齐、卫、鲁、赵、晋、秦、周、楚、郑、宋、燕;以封地所辖之州郡表示就是扬州、青州、并州、徐州、冀州、益州、雍州、三河、荆州、兖州、豫州、幽州。十二辰所配对的星宿是以诸侯受封日岁星所处的星宿来定的。具体名称在此不再赘述。
分野之说提出的意义在于,根据天上某一星象的变异,即可以预测其相应州国的吉凶,又可以根据地上某一州国发生的灾祸,到相应天次的星象(分星)上去找到解释。
占星术除了用于占卜国运,还被用于占卜人事。例如《礼记·月令》郑玄对“季春之月命国傩(nuó)”注称:“此傩,傩阴气也。阴气至此不止,害将及人。所以及人者,阴气右行此月之中,日行历昴,昴有大陵、积尸之气,气佚(逸)则厉鬼随而出行。”傩,义为逐除,指古人击鼓驱除疫鬼的仪式。大陵、积尸都是星座名。再如,《尔雅·释天》中称:阴历“三月为病”。《说文》释:“病,卧惊病也。”所以这个月是灾疫流行之月。
为了使占兆比附对人事预测有较灵活的回旋余地,占星家们发展出一套幻化吉凶的术数,从而使占星活动更富玄虚而具迷惑性。
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占星学的神学思想与天文科学属于两种完全不同的思想体系。在历史上占星学曾经阻碍和束缚了天文科学的进步与发展,成为古天文学研究上的一个误区,并因此浪费了大量的精力。
即使在占星活动较为盛行的时候,还是有人根据自己的实际生活经历和社会现象,对天命的信念提出了怀疑。例如,《国语·越语下》中说有“天道皇皇,日月以为常”的句子。历代一些进步思想家如荀况、王充、柳宗元、王安石等相继发起了对神学天命观的批判。批判占星术及其哲学思想基础天命观的论争几乎贯串了整个历史时代,论争使得人们逐步扩大和加深了对宇宙天体的科学认识。
然而,我们并不能完全否定占星术的作用。
首先,占星术对天文学有着推动作用。古人对日月星辰崇拜并据以进行占卜,表明人类探索自然和认识能动性的开始,但限于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相应的认识能力,只能借助于幻想和神秘的猜测对天体进行解释,从而产生了原始神话传说和各种神灵观念,而原始天文科学却从中开始萌芽。
从实践的角度考察,由于天象观测长期处于宗教神学思想的支配下,历史上占星学与天文科学往往是融为一体,很难作出明确的划分。最早的天文官员都是由巫、祝、星、卜之类的宗教职业者担任,有的本身就是大巫。古人出于人事占验而对天象作了十分细致的观测记录,对天文科学研究和历法制定积累了大量宝贵的科学资料,客观上对天文科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单以我国来说,古天文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具有社会天文学的显著特征,其所体现出来的宗教人文内容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其中糟粕多于精华,但我们应以批判的态度来整理探索这份历史文化遗产,而不能一概加以否定排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