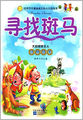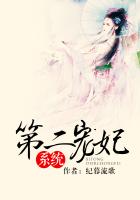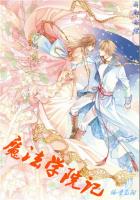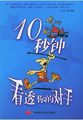在观影的时候,观者与创作者的位置则替换了过来。经过对镜头的剪切与衔接,一部影片表现出来的结构方式就是一种意识构成的方式,因此在观影时,观者所面对的是创作者的意识构成而非简单的生活事像。而为了理解这一意识构成——理解电影——观者则必须在其意识内把自己暗中替换为创作者,或者说,必须将另一个意识纳入自身的意识结构之内。对于这一点,现在的观者由于熟视无睹而已仿佛难于理解了:发展了上百年之后,电影(尤其是各种类型片)的各种结构套路早已成为陈词滥调,观者对之熟稔得看了上一个镜头即能猜出下一个镜头,看了开场十分钟即能大体猜测到结局。但是,这种“熟稔”却同时意味着观者与创作者之间替换与重合的“惯性”,而为了根除这种惯性,一些具有强烈自我意识的电影导演(尤其是先锋电影)则绞尽脑汁地突破旧套以创造新套,或者反其道而行之,从暴露与引入叙述痕迹方面来避免这种替换与重合的观影惯性——这成为了法国导演戈达尔的著名风格。但是,即便面对的是戈达尔的具有特殊叙述风格的电影,观众也必须首先把自己置换为电影的导演“戈达尔”,才能理解戈达尔创作“这一部”电影的表述方式和表述目的。戈达尔毕竟还是在构造电影,不管他以怎样新颖的方式。
因此,观影场景与对文字文本进行阅读不同。观影场景本身即模拟出了意识地形的结构,并就此模拟出了一个略微简单、但却充足的意识大脑。这立体地构成了一个虚拟的意识空间。文字阅读则一直处于读者的阅读联想和阅读幻想中,这是一个平面的而非立体的意识空间。
在电影的传统放映方式中,在黑暗的放映大厅里,放映机、观者、银幕(包括音箱)三者构成了一个封闭的、空间化的意识大脑。在这个技术化与空间化的意识大脑中,则同时包括了电影创作者和观者的双重的意识构成:在场的放映机正类似创作者那发送信息的大脑,银幕是眼睛,音箱是嘴,创作者的意识通过放映机、银幕和音箱而完整地、空间化地映现在银幕上;观者自身的大脑、眼睛与耳朵——另一个完整的意识——则与之发生重合和意识的替换。因此,观影场景的双重性同时包括着内部与外部、平面和立体的两种双重性:在创作者和观者意识内部发生的重合与交换的双重性,观影场景的“地形”所构成的外部意识重合与交换的双重性。观影地形的外部空间保障着内部意识的重合与交换,这多重的双重性则统一于观影场景的空间中;这空间是实际的,然而其本质则构成了对意识结构的虚拟。
在这既平面又立体的双重性之下,则是自我意识的多种构成和组合。意识交替的可能性不尽相同,每一个观者对电影的理解也都不尽相同,这构成了影片与观者之间意识关联的多重处所与多种结构,而所有这些交替复杂的处所与结构都同样被囊括于同一个虚拟的观影空间之内。因而,观影场景在实际上成为了自我意识的分裂与结构的空间摹本,它在一个实际性的空间中将之映现了出来。
观影场景正是将人的时间经验、空间经验与意识经验综合起来的一个特殊场景。在这一特殊的观影场景中,在对作为技术和艺术的双重形式的电影的观看中,人的自我间性也由此得到了最立体、最充分的表达。
由于多重的意识构成,观影场景成为自我认知和自我与他者关系认知的多重投射。与观影场景所囊括的双重性相应,自我认知和对自我与他者关系的认知既是创作者的,也是观者的。伯格曼的电影是他的生活世界和意识世界的分化性呈现,电影人物承担了伯格曼那分裂的、争斗的、片断性的自我意识。通过电影,通过人物的成型的命运表述,伯格曼将分裂的自我意识的诸种可能性与不可能性分化于其中,因而他的电影就是他的部分的意识世界,也是他对自我的认知、对自我意识的诸差别性的认知、对他者与自我关系的认知的视像性呈现。也就是说,在电影的艺术和技术的基础上,伯格曼的世界被结构化进而内化为他的自我并进一步内化于他的电影之中。电影成为他的自我的一种共相,成为他的自我间性的一种共相式表达(在这一点上,特吕弗所言的“作者电影”的类型,也就是那些自传性与自我性极强的导演——如费里尼、塔科夫斯基、安东尼奥尼等人——及其作品则为此提供了充足的范例)。
而其他的观者,在对伯格曼电影进行解读时,他将在伯格曼的电影中同样看到自身的自我,看到这个自我与他者和世界的关系,看到自己那分裂为多处的意识世界。在观影场景所提供的内部与外部、平面与立体的意识双重性之中,在自我间性的关系之网中,在自我与他者的意识性关联中,不仅银幕上的他者而且创作者的意识都足以成为观者自我的表征。在这当中,则潜藏着自我间性的那种否定性关系:为了获得对自我的确认,在这个虚拟空间的意识之网中,在观者的自我与他者之间将同样是那否定、扬弃与返回的意识运动。(在观影中,电影正是那言语与独白的主体而观众则是那黑暗的沉默主体,电影也同样具有极容易被污染的言语性而观众的沉默也同样容易被言语所揭露——在电影的言语与观众的沉默之间不是将同样发生言语与沉默的冲突与交换?正如同言语与沉默,电影与观众不也正构成了一种隐秘的但是脆弱的同盟?)
观影场景为自我间性的张力提供了最隐秘的空间和最大、最开放的可能。在观影时,观者的自我不断地外在化、对象化,同时也不断地内在化、结构化,在这一双向的持续的运动过程中,观者的自我确认着自身的无限性并最终加深了自身的分裂与矛盾。电影能够以一种空间化的形式——而非仅仅视觉的形式——激发观者自我的存在实感和世界实感,但是另一方面,当自我的存在和世界的存在被全面地内在化与结构化时,对意义的探询则终将被繁复的结构所覆盖。
自我的存在实感和世界实感本是那样的单薄、颤抖、纯真而透明,现在,它们却逐步地获得了虚拟的强大、坚实、浑浊和广阔。由于意义的被覆盖与被驱逐,在仿佛无所不能的结构性意志面前,自我的存在实感和世界实感的单薄则以另一种方式——另一种我们必须以反面读取的方式——而变得更加透明,透明得倘若我们不具备必要的目力,我们就看不见它。(在《假面》中,艾尔玛的言语不正是带着一种将存在编织进言语里的威胁步步进逼?佛格勒太太的沉默不正是被迫变得那样脆弱与透明以至于连她自己也可能看不见它?)
世界被拍了下来,凝聚在底片上,这当中包含着人类一种最巨大的精神野心:这野心试图将世界完全地可视化,在人的眼睛面前,世界被迫裸露成了一具横陈的肉体。然而,最可悲的,这肉体的灵魂却在别处,在我们所无法看见的地方。现在,因为我们没有看见,我们就会将它忘却。
在类型片中,观者的自我间性及其构成得到了突出的显示。根据风格、题材或形式构成的不同,叙述电影可以分成诸如西部片、青春片、战争片、恐怖片或科幻片的不同类型。与此同时,类型片的概念也是对自我与世界的一种想象性关系的规范与定型:类型片提供了一种规范的、相对稳定的意识结构与意识关联,通过对片型的选择性观看,观者可以轻易地把自我放置到某种结构关系中以及这一结构的任一位置上,例如,放置于战争片的暴力或科幻片的幻想当中,放置于英雄、美人甚或外星人的位置上。在意识的替换与认同中,观者的间性自我在与世界的某种关联里得到了想象性的实现,继而以结构的方式返回矛盾的自身。反过来,这种通过观影就能轻易实现的想象性关系也会形成一种意识惯性,影响观者对世界、对自我与他者关系的理解。类型片成为观者的自我与他者和世界的一种想象性的实现方式,同时也是对观者的心理需求、欲望和自我间性关系的映现。
作为一种想象性的实现方式,观者对电影(指叙述电影)的迷恋是对自我实现的可能性的迷恋。一些观者宁愿生活在电影生活和电影世界所提供的可能性中,却会放弃现实生活中的可能。这个“观者”既可用以指称创作者,也可用以指称通常的观众。创作者通过电影艺术寄托了自己的生活和自我意识,艺术成为一件私人、私己、私密的事;观者则通过观看,在意识上重新结构并分享和参与了这件私人事务(一直到欧洲的中世纪时,艺术的概念还未包括这种纯粹的私己性自我,那时的“艺术”还是一种跟上帝有关的公共事务)。
在电影的经济机制上,这种自我实现的“可能性”则集中体现为好莱坞式的明星制。“明星”—“追星”无不带有自恋的、替代性的自我意识的影子,这“影子”既包括电影明星对自我意识与角色意识的可能性混同,也包括影星的迷恋者对自己与明星或角色的可能性混同。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则令电影商业通过各种方式持续地制造、鼓励并保障着这些混同。观众对明星的迷恋映射了自我的假想——“我”注视着“我”的可能的生活,这种假想的“注视”是自我的、安全的、隐秘的,但是,这假想的、替代性的自我实现方式也可以是极端的、否定性的。拉康在他的博士论文《论妄想型变态心理及其与人格的关系》中对精神病患者艾梅的研究就是这样的一个个案。艾梅在巴黎一家剧院持刀攻击一个著名的女演员,实际上,艾梅的攻击正是其分裂自我的一种内部否定,她所攻击并否定的并不是“那个”女演员,而是一个想象中的(“误识的”)自我的他者——另一个“我”。
电影成为了观者的自我的洞穴,他在其中得以分藏了间性自我。在观影过程中,分裂的自我既得以映射,也得到想象性的实现。观影过程是观者在一种既现实又幻觉的方式中将分裂性自我进行重新组合与重新构成的过程。这一过程,在其极端的方面,则激发并构成了观者在虚拟的意识空间中的“现实生活”。
若是传统电影放映方式中的放映机退出,并不会影响这个虚拟的意识地形的完整性。一个当代观者,只要面对一个包括了声音和画面的屏幕,就足以构成一个虚拟的意识空间。在早期的电影放映机制里,电影院曾经作为实现电影“意识地形”的一个重要保障,但是经过了几十年上百年之后,人们已经完全熟悉了电影的结构方式和放映方式,电影院的“意识地形”已经深入观者的潜意识当中——即便手头正在忙碌于其他事情,只要瞥一眼电视屏幕,一个最普通的观众也能马上明白屏幕上“正在干什么”。然而,这种观影情形绝对不是天生的或自然而然的。在电影发展的初期,卢米埃尔的《火车进站》(1895)仅仅表现了火车进站的单一场面,就足以令电影院里的观众产生火车即将碾压过来的错觉而惊叫着逃离座位。今天的情形则是,一个在电视机和电脑的环绕下长大的普通观众对屏幕上的暴力、恐怖和色情早已司空见惯而显得几乎麻木不仁,而这暴力、恐怖与色情的程度都是早期的电影观众——或者非洲遥远部落里的原始居民,虽然这类没接触过任何电影或电视画面的居民在数字化的地球上几乎已经不存在了——所完全不能想象的。
立体的虚拟空间为自我意识提供了一个巨大的结构之网,它将世界、他人、他人的自我都内化为观者的自我的结构,观者的意识自我在这结构性关系中则获得了丰富的选择余地和巨大的实现可能。对此令人深思的则是:这本是一种虚拟的选择与可能,它为何也同时成为了一种“现实的”可能?——这可能比真正的外部现实生活所提供的可能都更为庞杂和具有吸引力,足以令人暂时忘却或取代现实生活的单薄可能。
这虚拟的同时也无比现实的可能性,在现今的网络和电脑游戏中则以另一种方式、另一种趋势而迅速得以扩展。网络与电脑游戏提供了另一虚拟的意识空间,这空间同样存在一面屏幕和一个坐在屏幕前的观者。与电影的观看场景稍有不同的是,网络和电脑游戏(包括网络游戏)提供的是一个动态化的、可参与的自我意识的虚拟空间,它能充分满足观者对自我表达、自我的创造力或超人般的特殊能力的心理需求。对于现代社会而言,电脑游戏可说是一出悲喜剧:它将现实生活的无意义与令人厌倦从年轻的观者的现实存在中剥离了出来(这时常会造成游戏玩家在精神上的自闭倾向、与社会关系的隔绝或反社会的心理倾向),在观者对怪物、魔鬼、敌人的砍杀和征服中,在对友谊、爱情、超人能力甚或财富的追求与获得中,构造了一出在虚无主义时代寻求传统价值、绝对意义和完满空间的悲喜剧。
因此,仅就虚拟空间的完整性而言,网络以及游戏因其充分的参与感和动态性而比观影空间更完整,但是另一方面,电影却(不甘落后地)具有比网络和游戏空间的随机与动态更丰富的结构和更完整的表达。1999年上映的《黑客帝国》(Matrix,沃卓斯基兄弟编导,共三集)就是结合了网络、游戏和电影故事的一次纯粹后现代式的完整的幻觉表达。
男主人公尼欧所面对的一个难题是:“你怎么知道梦和现实的区别?”《黑客帝国》一片呈现出梦与现实、真实空间与幻觉空间的重合,是在空间交叠与重合的基础上,它们才得以被区分为由电脑程序所控制的虚拟的现实母体、世界末日般的悲惨现实的虚拟母体以及电脑自身的母体。而人在其中,不管是“救世主”尼欧还是电脑人,都是被母体空间——Matrix-—所控制的代码。这套影片结合了在虚拟时空和真实时空的交叠中所包含着的几乎所有的真实与幻觉的因素,这些本应令观者对真实与幻觉的现实性交叠形成足够的警惕。然而与此恰恰相反,这套影片引领出一大批年轻的追随者。对这套影片的迷恋与讨论不仅加深了观者对电影作为虚拟空间的涉足,也在实际上进一步加深了——这“加深”则与影片的故事内容具有某种令人吃惊的同步性——现实空间与幻觉空间之间的真伪莫辨。
从电影的观影场景到网络游戏,自我的悖论必然持续存在。自我意识的分裂及其结构关系构成了多种可能,当代视听技术的发展则为这些可能一一提供了充足的想象性实现的方式。由此,我们却可以回想到,欧洲在其现代性进程中也同时酝酿了它的分裂及其悖论。一个多世纪前,这分裂导致了对民族作为政治共同体——在现代性的论述中,民族同样成为了既虚拟又真实、既多重又立体的意识空间——的普泛性建构并延续着其悖论和冲突,而这一建构在如今则无法逆转地发展成为了对作为意识与地域空间的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意识偏执。
然而,21世纪的观者所处的这一自我意识的结构性网络,却并未脱离16世纪的德国人荷尔拜因曾经对此的结构性描绘。21世纪观者的意识,仍旧作为“中项”处于生存与死亡、信仰与虚无、理性与非理性之间,只不过,所有这些在16世纪时虽然对立却尚还坚实的意义在如今则已带上了过于明确的虚无与幻觉的内涵。我们已经学会平静地将虚无当作了自己的一种存在,将分裂的自我、间性的自我当作了自身意识的存在。而观影场景,正是将我们自身这一结构性的“存在”、将我们在理性的岔路上就自身所取得的这一特殊形式明明白白地映现在了我们自己的眼睛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