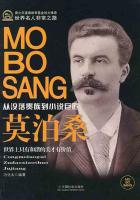柳宗元(773—819),字子厚,原籍山西河东(今山西永济),出身官宦之家。贞元九年(793),他考中进士,官秘书省校书郎。后考中博学鸿词科,历任集贤殿正字、蓝田尉、监察御史里行、礼部员外郎。后贬官为永州司马、柳州刺史。
柳宗元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在文学上有极高的造诣,他是唐代和中国历史上那些为数不多的具有鲜明个性的著名作家之一。他积极投身于当时文坛兴起的以反对骈文、提倡散文为标识的文学革新运动,强调“文者以明道”,柳宗元的文学创作成就是多方面的,包括政论、诗歌、散文、寓言、游记、辞赋,但最突出的是散文,无论思想水平,还是艺术水平,都可谓达到空前程度。
非国语上选
灭密
恭王游于泾上,密康公从,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王。众以美物归汝,何德以堪之?小丑备物,终必亡。”康公不献。一年,王灭密。
非曰:康公之母诚贤耶,则宜以淫荒失度命其子,焉用惧之以数?且以德大而后堪,则纳三女之奔者,德果何如?若曰“勿受之”,则可矣。教子而媚王以女,非正也。左氏以灭密征之,无足取者。
不藉
宣王不藉千亩。虢文公谏曰:“云云。将何以求福用人?”王不听。三十九年,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
非曰:古之必藉千亩者,礼之饰也。其道若曰“吾犹耕云尔”,又曰:“吾以奉天地宗庙,则存其礼诚善矣。然而存其礼之为劝乎农也,则未若时使而不夺其力,节用而不殚其财,通其有无,和其乡闾,则食固人之大急,不劝而劝矣。启蛰也得其耕,时雨也得其种,苗之猥大也得其耘,实之坚好也得其获,京庾得其贮,老幼得其养,取之也均以薄,藏之也优以固,则三推之道,存乎亡乎,皆可以为国矣。彼之不图,而曰我特以是劝,则固不可。”今为书者曰“将何以求福用人”,夫福之求,不若行吾言之大德也;人之用,不若行吾言之和乐以死也。败于戎,而引是以合焉,夫何怪而不属也?又曰“战于千亩”者,吾益羞之。
料民
宣王料民于太原,仲山父谏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王治戎于藉,蒐于农隙,耨获亦于藉,狝于既蒸,狩于毕时,是皆习民数也,又何料焉!不谓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恶事也。临政示少,诸侯避之。治民恶事,无以赋令。且无故而料民,天之所恶也,害于政而妨于嗣。”王卒料之。及幽王,乃废灭。
非曰:吾尝言,圣人之道,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故孔子不语怪与神。君子之谏其君也,以道不以诬,务明其君,非务愚其君也。诬以愚其君,则不臣。仲山氏果以职有所协,不待料而具,而料之者政之尨也,姑云尔而已矣,又何以示少恶事为哉!况为大妄以诿乎后嗣?惑于神怪愚诬之说,而以是征幽之废灭,则是幽之悖乱不足以取灭,而料民者以祸之也。仲山氏其至于是乎?盖左氏之嗜诬斯人也已,何取乎尔也!
神降于莘
周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王问于内史过曰:“今是何神也?”对曰:“昔昭王娶于房,曰房后,实有爽德,协于丹朱。丹朱冯身以仪之,生穆王焉。实临周之子孙而祸福之。夫神壹,不远徙迁。若由是观之,其丹朱之神乎?”王曰:“其谁受之?”对曰:“在虢土。”王曰:“然则何为?”对曰:“臣闻之,道而得神,是谓逢福;淫而得神,是谓贪祸。今虢少荒,其亡乎!”王曰:“吾其若之何?”对曰:“使太宰以祝史帅狸姓,奉牺牲粢盛玉帛往献焉,无有祈也。”王曰:“虢其几何?”对曰:“昔尧临民以五,今其胄见,神之见也,不过其物。若由是观之,不过五年。”
非曰:力足者取乎人,力不足者取乎神。所谓足,足乎道之谓也,尧、舜是矣。周之始,固以神矣,况其征乎?彼鸣乎莘者,以焄蒿凄怆,妖之浅者也。天子以是问,卿以是言,则固已陋矣。而其甚者,乃妄取时日,莽浪无状,而寓之丹朱,则又以房后之恶德与丹朱协,而凭以生穆王,而降于虢,以临周之子孙,于是遂帅丹朱之裔以奉祠焉;又曰尧临人以五,今其胄见,虢之亡,不过五年。斯其为书也,不待片言而迂诞彰矣。
聘鲁
定王八年,使刘康公聘于鲁。发币于大夫,季文子、孟献子皆俭,叔孙宣子、东门子家皆侈。归,王问鲁大夫孰贤,对曰:“季、孟其长处鲁乎?叔孙、东门其亡乎?若家不亡,身必不免。”王曰:“几何?”对曰:“东门之位,不若叔孙,而泰侈焉,不可以事二君。叔孙之位,不若季孟,而亦泰侈焉,不可以事三君。若皆蚤世犹可,若登年以载其毒,必亡。”
非曰:泰侈之德恶矣,其死亡也有之矣,而孰能必其时之蚤暮耶?设令时之可必,又孰能必其君之寿夭耶?若二君而寿,三君而夭,则登年载毒之数,如之何而准?
叔孙侨如
简王八年,鲁成公来朝,使叔孙侨如先聘,且告。见王孙说,与之语。说言于王曰:“鲁叔孙之来也,必有异焉。其享觐之币薄而言谄,殆请之也。若请之,必欲赐也。鲁执政唯强,故不欢焉,而后遣之。且其状方上而锐下,宜触冒人,王其勿赐。若贪陵之人来,而盈其愿,是不赏善也。”
非曰:诸侯之来,王有赐予,非以货其人也,以礼其国也。苟叔孙之来,不度于礼,不仪于物,则罪也。王而刑之,谁曰不可?若力之不能而姑勿赐,未足以惩夫贪陵者也,不若与之。今使王逆诈诸侯而蔑其卿,苟兴怨于鲁,未必周之福也。且夫恶叔孙者,泰侈贪陵则可矣,方上而锐下,非所以得罪于天子。
郄至
晋既克楚于鄢,使郄至告庆于周。未将事,王叔简公饮之酒,相说也。明日,王叔子誉诸朝。郄至见邵桓公,与之语。邵公以告单襄公曰:王叔子誉温季,以为必相晋国,相晋国必大得诸侯,劝二三君子必先导焉,可以树。“襄公曰:人有言曰‘兵在其颈’,其郄至之谓乎!君子不自称也。云云。在《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王叔欲郄至,能勿从乎?”郄至归,明年死难。及伯舆之狱,王叔陈生出奔晋。
非曰:单子罪郄至之伐当矣。因以列数舍郑伯、下楚子、逐楚卒,咸以为奸,则是后之人乘其败追合之也。左氏在《晋语》言免胄之事,则曰“勇以知礼”,于此焉而异,吾何取乎?郄氏诚良大夫,不幸其宗侈而亢;兄弟之下令,而智不能周,强不能制,遭晋厉之淫暴,谗嬖窃构以利其室,卒及于祸。吾尝怜焉。今夫执笔者以其及也,而必求其恶以播于后世,然则有大恶幸而得终者,则固掩矣。世俗之情固然耶?其终曰“王叔欲郄至,能勿从乎”,斯固不足讥也已。
柯陵之会
柯陵之会,单襄公见晋厉公视远步高,晋郄锜见,其语犯:郄犫见,其语迂;郄至见,其语伐;齐国佐见,其语尽。鲁成公见,言及晋难及郄犫之谮。单子曰:“晋将有乱,其君与三郄其当之乎?”鲁侯曰:“敢问天道乎,抑人故也?”对曰:“夫合诸侯,民之大事也。其君在会,步言视听,必皆无谪,则可以知德矣。晋侯爽二,吾是以云。今郄伯之语犯,叔迂,季伐。犯则陵人,迂则诬人,伐则掩人,其谁能忍之?虽齐国子亦将与焉。立于淫乱之国,而好尽言以招人过,怨之本也。”简王十二年,晋杀三郄。十三年,晋侯弑。齐人杀国武子。
非曰:是五子者,虽皆见杀,非单子之所宜必也。而曰合诸侯,人之大事,于是乎观存亡。若是,则单子果巫史矣。视远步高、犯、迂、伐、尽者,皆必乎死也,则宜死者众矣!夫以语之迂而曰宜死,则单子之语,迂之大者,独无谪邪?
晋孙周
晋孙谈之子周适周。单襄公以告顷公曰:“必善晋周,将得晋国。其行也文,能文则得天地。天地所祚,小而后国。夫敬,文之恭也;忠,文之实也;信,文之孚也;仁,文之爱也;义,文之制也;智,文之舆也;勇,文之师也;教,文之施也;孝,文之本也;惠,文之慈也;让,文之材也。此十一者,夫子皆有焉。天六地五,数之常也。”云云。“成公之归也,吾闻晋之筮之也,遇《乾》之《否》,曰‘配而不终’。君三出焉。一即往矣,后之不知,其次必此。且成公之生也,其母梦神规其臀以黑,曰:‘使有晋国,三而畀之孙。’故名之曰黑臀。于今再矣。晋襄公曰,此其孙也,而令德孝恭,非此而谁?必早善晋子,其当之也。”顷公许诺。
非曰:单子数晋周之德十一,而曰合天地之数,岂德义之言耶?又征卦、梦以附合之,皆不足取也。
谷洛斗
灵王二十二年,谷、洛斗,将毁王宫。王欲壅之,太子晋谏。云云。王卒壅之。及景王,多宠人,乱于是乎始生。景王崩,王室大乱。及定王,王室遂卑。
非曰:谷、洛之说,与三川震同。天将毁王宫而勿壅,则王罪大矣,奚以守先王之国?壅之诚是也。彼小子之者,又足记耶?王室之乱且卑,在德,而又奚谷、洛之斗而征之也?
大钱
景王将铸大钱。单穆公曰:“不可。云云。可先而不备,谓之怠;可后而先之,谓之召灾。”
非曰:古今之言泉币者多矣。是不可一贯,以其时之升降轻重也。币轻则物价腾踊,物价腾踊则农无所售,皆害也。就而言之,孰为利?曰“币重则利”,曰“奈害农何”,曰“赋不以钱”。而制其布帛之数,则农不害;以钱则多出布帛而贾,则害矣。今夫病大钱者,吾不知周之明何如哉?其曰“召灾”,则未之闻也。左氏又于《内传》曰:“王其心疾死乎”,其为书皆类此矣。
无射
王将铸无射,单襄公曰:“不可。”
非曰:钟之大不和于律,乐之所无用,则王妄作矣。单子词曰:口内味,耳内声,声味生气。气在口为言,在目为明。言以信名,明以时动,名以成政,动以殖生。政成生殖,乐之至也。若视听不和,而有震眩,则味入不精。不精则气佚,气佚则不和。于是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转易之名,有过慝之度。出令不信,刑政放纷。’而伶州鸠又曰:“乐以殖财。”又曰:“离人怒神。”呜呼,是何取于钟之备也!吾以是怪而不信。或曰:“移风易俗则何如?”曰:圣人既理,定知风俗和恒,而由吾教,于是乎作乐以象之。后之学者述焉,则移风易俗之象可见,非乐能移风易俗也。曰乐之不能化人也,则圣人何作焉?曰乐之来,由人情出者也,其始非圣人作也。圣人以为人情之所不能免,因而象政令之美,使之存乎其中,是圣人饰乎乐也。所以明乎物无非道,而政之不可忘耳。孟子曰:“今之乐,犹古之乐也”、“与人同乐,则王矣”,吾独以孟子为知乐。
律
王问律于伶州鸠,对曰:云云。
非曰:律者,乐之本也,而气达乎物,凡音之起者本焉。而州鸠之辞曰:“律吕不易,无奸物也。和平则久,久固则纯,纯明则终,终复则乐,所以成政。”吾无取乎尔。又曰:“姬氏出自天鼋,大姜之侄所凭神也。岁在周之分野。月在农祥,后稷之所经纬也。武王欲合是而用之。”斯为诬圣人亦大矣。又曰:“王以夷则毕陈,黄钟布戎,太蔟布令,无射布宪,施舍于百姓。”吾知其来之自矣,是《大武》之声也。州鸠之愚,信其传,而以为武用律也。孔子语宾牟贾之言《大武》也,曰:“《武》始自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天子,夹振之而四伐,盛威于中国。”则是《大武》之象也。“致右宪左”、“久立于缀”,皆《大武》之形也。夷则、黄钟、太蔟、无射,《大武》之律变也。
城成周
刘文公与苌弘欲城成周,告晋。魏献子为政,将合诸侯。卫彪傒见单穆公曰:“苌弘其不没乎?苌叔必速及,魏子亦将及焉。若得天福,其当身乎?若刘氏,则子孙实有祸。”是岁,魏献子焚死。二十八年,杀苌弘。及定王,刘氏亡。
非曰:彪傒天所坏之说,吾友化光铭城周,其后牛思黯作《颂忠》,苌弘之忠悉矣,学者求焉。若夫“当身”“速及”之说,巫之无恒者之言也,追为之耳。
问战
长勺之役,曹刿问所以战于严公。公曰:“小大之狱,必以情断之。”刿曰:可以一战。
非曰:刿之问洎严公之对,皆庶乎知战之本矣。而曰夫“神求优裕于飨”,“不优,神不福也”,是大不可。方斗二国之存亡,以决民命,不务乎实,而神道焉是问,则事几殆矣。既问公之言狱也,则率然曰“可以一战”,亦问略之尤也。苟公之德可怀诸侯,而不事乎战则已耳;既至于战矣,徒以断狱为战之具,则吾未之信也。刿之辞宜曰:君之臣谋而可制敌者谁也?将而死国难者几何人?士卒之熟练者众寡?器械之坚利者何若?趋地形得上游以延敌者何所?然后可以言战。若独用公之言而恃以战,则其不误国之社稷无几矣。申包胥之言战得之,语在《吴》篇中。
跻僖公
夏父弗忌为宗,烝,将跻僖公。云云。展禽曰:“夏父弗忌必有殃”,“若血气强固,将寿宠得没,虽寿而没,不为无殃。”其葬也,焚,烟彻其上。
非曰:由“有殃”以下,非士师所宜云者,诬吾祖矣。
莒仆
莒太子仆杀纪公,以其宝来奔。宣公使仆人以书命季文子,里革遇之而更其书。明日,有司复命,公诘之,仆人以里革对。公执之,里革对曰:“毁则者为贼,掩贼者为藏,窃宝者为宄,用宄之财者为奸。使君为藏、奸者,不可不去也;臣违君命者,不可不杀也。”公曰:“寡人实贪,非子之罪也。”乃舍之。
非曰:里革其直矣。曷若授仆人以入谏之为善?公之舍革也美矣!而仆人将君命以行,遇一夫而受其更,释是而勿诛,则无以行令矣。若君命以道而遇奸臣更之,则何如?
仲孙它
季文子无衣帛之妾,无食粟之马,仲孙它谏。云云。文子以告孟献子,孟献子囚之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过七升之布,马饩不过稂莠。
非曰:它可谓能改过矣。然而父在焉,而俭侈专乎己,何也?七升之布,大功之缞也,居然而用之,未适乎中庸也已。
羊
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有羊焉。使人问仲尼曰:“吾穿井获狗,何也?”仲尼曰:“以丘所闻者,羊也。”
非曰:“君子于所不知,盖阙如也”,孔氏恶能穷物怪之形也,是必诬圣人矣。史之记地坼犬出者,有之矣。近世京兆杜济穿井获土缶,中有狗焉。投之于河,化为龙。
骨节专车楛矢
吴伐越,隳会稽,获骨节专车。吴子使好来聘,且问之仲尼。仲尼曰:“丘闻之,昔禹致群臣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其骨节专车,此为大矣。”仲尼在陈,有隼集于陈侯之庭而死。楛矢贯之,石砮,其长尺有咫。陈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馆问之。仲尼曰:“隼之来也远矣,此肃慎氏之矢也。”
非曰:左氏,鲁人也。或言事孔子,宜乎闻圣人之嘉言,为《鲁语》也,盍亦征其大者,书以为世法?今乃取辨大骨、石砮以为异,其知圣人也亦外矣。言固圣人之耻也。孔子曰:“丘少也贱,故多能鄙事。”
轻币
天下诸侯知桓公之非为己动也,是故诸侯归之。桓公知诸侯之归己也,故使轻其币而重其礼。故天下诸侯罢马以为币,缕綦以为奉,鹿皮四箇。诸侯之使垂橐而入,稛载而归。
非曰:桓公之苟能吊天下之败,卫诸侯之地,贪强忌服,戎狄缩匿;君得以有其国,人得以安其堵,虽受赋于诸侯,乐而归之矣,又奚控焉?悉国之货以利交天下,若是耶,则区区齐人,恶足以奉天下?己之人且不堪矣,又奚利天下之能得?若竭其国,劳其人,抗其兵,以市伯名于天下,又奚仁义之有?予以谓桓公之伯,不如是之弊也。
卜
献公卜伐骊戎,史苏占之曰:“胜而不吉。”
非曰:卜者,世之余伎也,道之所无用也。圣人用之,吾未之敢非。然而圣人之用也,盖以驱陋民也,非恒用而征信矣。尔后之昏邪者神之,恒用而征信焉,反以阻大事。要之卜史之害于道也多,而益于道也少,虽勿用之,可也。左氏惑于巫而尤神怪之,乃始迁就附益以成其说,虽勿信之,可也。
郭偃
郭偃曰:“夫口,三五之门也。是以谗口之乱,不过三五。”
非曰:举斯言而观之,则愚诬可见矣。
公予申生
申生曰:“弃命不敬,作令不孝,间父之爱而嘉其贶,有不忠焉。废人以自成,有不贞焉。”
非曰:申生于是四者咸得焉。昔之儒者有能明之矣,故予之辞也略。
狐突
公使太子伐东山,狐突御戎。至于稷桑,翟人出逆。申生欲战,孤突谏曰:“不可。”申生曰:“君之使我非欢也,抑欲测吾心也。不战而反,我罪滋厚;我战虽死,犹有名焉。”果战,败翟于稷桑而反,谗言益起。狐突杜门不出。君子曰:“善深谋。”
非曰:古之所谓善深谋,居乎亲戚辅佐之位,则纳君子道;否则继之以死,唯己之义所在,莫之失之谓也。今孤突,以位,则戎御也;以亲,则外王父也。申生之出,未尝不从,睹其将败而杜其门,则奸矣。而曰“善深谋”,则无以劝乎事君也已。丕郑曰“君为我心”,里克曰“中立”,晋无良臣,故申生终以不免。
虢梦
虢公梦在庙,有神面白毛虎爪,执钺立于西阿之下。云云。公觉,且使国人贺梦。舟之侨告诸其族曰:“众谓虢不久,吾今知之。”以其族行,适晋。
非曰:虢,小国也而泰,以招大国之怒,政荒人乱,亡夏阳而不惧,而犹用兵穷武以增其雠怨,所谓自拔其本者。亡,孰曰不宜?又恶在乎梦也?舟之侨诚贤者欤?则观其政可以去焉。由梦而去,则吾笑之矣。
童谣
献公问于卜偃曰:“攻虢何月也?”对曰:“童谣有之,曰丙之辰,云云。”
非曰:童谣无足取者。君子不道也。
宰周公
葵丘之会,献公将如会,遇宰周公,曰:“君可无会也。夫齐侯将施惠出责,是之不果,而暇晋是皇。”公乃还。宰孔曰:“晋侯将死矣。景霍以为城,而汾、河、涑、浍以为渊,戎狄之民实环之,汪是土也,苟违其违,谁能惧之?”是岁,献公卒。
非曰:凡诸侯之会霸主,小国,则固畏其力而望其庥焉者也;大国,则宜观乎义,义在焉则往,以尊天子,以和百姓。今孔之还晋侯也,曰“而暇晋是皇”,则非吾所陈者矣。又曰“汪是土也,苟违其违,谁能惧之”,则是恃乎力而不务乎义,非中国之道也。假令一失其道以出,而以必其死,为书者又从而征之,其可取乎?
荀息
里克欲杀奚齐,荀息曰:“吾有死而已。先君问臣于我,我对以忠贞。”既杀奚齐,荀息将死之,人曰:“不如立其弟而辅之。”荀息立卓子。里克又杀卓子,荀息死之。君子曰:“不食其言矣。”
非曰:夫忠之为言中也,贞之为言正也。息之所以为者有是夫?间君之惑,排长嗣而拥非正,其于中正也远矣。或曰:“夫己死之不爱,死君之不欺也。抑其有是,而子非之耶?”曰:“子以自经于沟渎者举为忠贞也欤?”或者:“左氏、谷梁子皆以不食其言,然则为信可乎?”曰:“又不可。不得中正而复其言,乱也,恶得为信?”曰:“孔父、仇牧,是二子类耶?”曰:不类,则如《春秋》何?曰:“《春秋》之类也,以激不能死者耳。孔子曰:‘与其进,不保其往也。’《春秋》之罪许止也,隐忍焉耳。其类荀息也亦然,皆非圣人之情也。枉许止以惩不子之祸,进荀息以甚苟免之恶,忍之也。吾言《春秋》之情,而子征其文,不亦外乎?故凡得《春秋》者,宜是乎我也。此之谓信道哉!”
非国语下选
狐偃
里克既杀卓子,使屠岸夷告重耳曰:“子盍入乎?”舅犯曰:“不可。云云。”秦穆公使公子絷吊重耳曰:“时不可失。”舅犯曰:“不可。云云。”
非曰:狐偃之为重耳谋者,亦迂矣。国虚而不知入,以纵夷吾之昏殆,而社稷几丧。徒为多言,无足采者。且重耳,兄也;夷吾,弟也。重耳,贤也;夷吾,昧也。弟而昧,入犹可终也;兄而贤者,又何慄焉?使晋国不顺而多败,百姓之不蒙福,兄弟为豺狼以相避于天下,由偃之策失也。而重耳乃始伥伥焉游诸侯,阴蓄重利,以幸其弟死,独何心欤?仅能入,而国以霸,斯福偶然耳,非计之得也。若重耳早从里克、秦伯之言而入,则国可以无向者之祸,而兄弟之爱可全,而有分定焉故也。夫如是,以为诸侯之孝,又何戮笑于天下哉!
舆人诵
惠公入而背内外之赂。舆人诵之曰:“云云。得之而狃,终逢其咎;丧田不惩,祸乱其兴。”既,里、死,公陨于韩。郭偃曰:“善哉,夫众口,祸福之门也!”
非曰:惠公、里、之为也,则宜咎,祸及之矣,又何以神众口哉!其曰“祸福之门”,则愈陋矣。
葬恭世子
惠公出恭世子而改葬之,臭达于外。国人颂之曰:“云云。岁之二七,其靡有征兮。若翟公子,吾是之依兮。安抚国家,为王妃兮。”郭偃曰:“十四年,君之冢嗣其替乎?其数告于人矣。公子重耳其入乎?其魄兆于人矣。若入,必霸于诸侯,其光耿于民矣。”
非曰:众人者言政之善恶,则有可采者,以其利害也,又何以知君嗣二七之数与重耳之伯?是好事者追而为之,未必偃能征之也,况以是故发耶!
杀里克
惠公既杀里克而悔之,曰:“芮也使寡人过杀社稷之镇。”郭偃闻之曰:“不谋而谏者,冀芮也,不图而杀者,君也。不谋而谏不忠,不图而杀不详。不忠受君之罚,不祥罹天之祸。受君之罚死戮,罹天之祸无后。”
非曰:芮之陷杀克也,其不祥宜大于惠公。而异其辞,以配君罚天祸,皆所谓迁就而附益之者也。
获晋侯
秦穆公归,至于王城,合大夫而谋曰:杀晋君与逐出之,与以归与复之,孰利?公子絷曰:“杀之利。”公孙枝曰:“不可。”公子絷曰:“吾将以重耳代之。晋之君无道,莫不闻;重耳之仁,莫不知。杀无道立有道,仁也。”公孙枝曰:“耻一国之士,又曰‘余纳有道以临汝’,无乃不可乎?不若以归,要晋国之成,复其君而质其适子,使父子代处秦,国可以无害。”
非曰:秦伯之不霸天下也,以枝之言也。且曰“纳有道以临汝”,何故不可?絷之言杀之也,则果而不仁;其言立重耳,则义而顺。当是时,天下之人君莫能宗周,而能宗周者则大国之霸基也。向使穆公既执晋侯,以告于王曰:“晋夷吾之无道莫不闻,重耳之仁莫不知,且又不顺,既讨而执之矣。”于是以王命黜夷吾而立重耳,咸告于诸侯曰:“吾讨恶而进仁,既得命于天子矣,吾将达公道于天下。”则天下诸侯无道者畏,有德者莫不皆知严恭欣戴而霸秦矣。周室虽卑,犹是王命,命穆公以为侯伯,则谁敢不服?夫如是,秦之所耻者亦大矣。弃至公之道,而不知求,姑欲离人父子,而要河东之赂,其舍大务小、违义从利也基矣,霸之不能也以是夫!
庆郑
丁丑,斩庆郑,乃入绛。
非曰:庆郑误止公,罪死可也,而其志有可用者。坐以待刑,而能舍之,则获其用亦大矣。晋君不能由是道也,悲夫,若夷吾者,又何诛焉?
乞食于野人
文公在狄十二年,将适齐,行过五鹿,野人举块以与之。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赐也。人以土服,又何求焉?十有二年,必获此土。有此其以戊申云乎?”
非曰:是非子犯之言也,后之好事者为之。若五鹿之人献块,十二年以有卫土,则涓人畴枕楚子以块,后十二年其复得楚乎?何没而不云也,而独载乎是?戊申之云,尤足怪乎。
怀嬴
秦伯归女五人,怀嬴与焉。
非曰:重耳之受怀嬴,不得已也。其志将以守宗庙社稷,阻焉,则惧其不克也。其取者大,故容为权可也。秦伯以大国行仁义交诸侯,而乃行非礼以强乎人,岂习西戎之遗风欤?
筮
公子亲筮之,曰:“尚有晋国。”得贞《屯》、悔《豫》皆八筮。史占之曰“不吉”,司空季子曰“吉”。云云。
非曰:重耳虽在外,晋国固戴而君焉;又况夷吾死,圉也童昏以守内,秦楚之大以翼之,大夫之强族皆启之,而又筮焉是问,则末矣。季子博而多言,皆不及道者也,又何载焉!
董因
董因迎公于河,公问焉,曰“吾其济乎?”对曰:“岁在大梁,云云。”
非曰:晋侯之入,取于人事备矣,因之云可略也。大火、实沈之说赘矣。
命官
胥、籍、狐、箕、栾、郄、桓、先、羊舌、董、韩,实掌近官。诸姬之良,掌其中官。异姓之能,掌其远官。
非曰:官之命,宜以材耶?抑以姓乎?文公将行霸,而不知变是弊俗,以登天下之士,而举族以命乎远近,则陋矣。若将军大夫必出旧族,或无可焉,犹用之耶?必不出乎异族,或有可焉,犹弃之耶?则晋国之政可见矣。
仓葛
周襄王避贻叔之难,居于郑地汜。晋文公迎王入于成周,遂定之于郏。王赐公南阳阳樊、温、原、州、陉、纟希、钅且、攒茅之田。阳人不服,公围之。将残其民,仓葛呼曰:“君补王阙,以顺礼也。阳人未狎君德而未敢承命,君将残之,无乃非礼乎?”公曰:“是君子之言也。”乃出阳人。
非曰:于《周语》既言之矣,又辱再告而异其文,抑有异旨耶?其无乎,则耄者乎?
观状
文公诛观状以伐郑。郑人以名宝行成,公弗许。郑人以瞻与晋,晋人将烹之,瞻曰:“天降祸郑,使淫观状,弃礼遗亲。云云。”
非曰:观晋侯之状者,曹也。今于郑胡言之,则是多为诬者且耄,故以至乎是。其说者云“郑效曹也”,是乃私为之辞,不足以盖其误。
救饥
晋饥,公问于箕郑曰:“救饥何以?”对曰:“信”。公曰:“安信?”对曰:“信于君心,信于名,信于令,信于事。”
非曰:信,政之常,不可须臾去之也。奚独救饥耶?其言则远矣。夫人之困在朝夕之内,而信之行在岁月之外。是道之常,非知变之权也。其曰“藏出如入”则可矣,而致之言若是远焉,何哉?或曰:“时之信未洽,故云以激之也。信之速于置邮,子何远之耶?”曰:“夫大信去令,故曰信如四时恒也,恒固在久。若为一切之信,则所谓未孚者也。彼有激乎则可也,而以为救饥之道,则未尽乎术。”
赵宣子
赵宣子言韩献子于灵公,以为司马。河曲之役,赵孟使人以其乘车干行,献子执而戮之。
非曰:赵宣子不怒韩献子而又褒其能也,诚当。然而使人以其乘车干行,陷而至乎戮,是轻人之死甚矣。彼何罪而获是讨也?孟子曰:“杀一不辜而得天下,君子不为。”是所谓无辜也欤?或曰:“戮,辱也,非必为死。”曰:“虽就为辱,犹不可以为君子之道。舍是其无以观乎?吾惧司马之以死讨也。”
伐宋
宋人杀昭公,赵宣子请师以伐宋。云云。曰:“是反天地而逆民则也,天必诛焉。晋为盟主而不修天罚,将惧及焉。”
非曰:盟主之讨杀君也,宜矣。若乃天者,则吾焉知其好恶而暇征之耶!古之杀夺有大于宋人者,而寿考佚乐不可胜道,天之诛何如也?宣子之事则是矣,而其言无可用者。
祈死
反自鄢,范文子请其宗祝曰:“君骄而有烈,吾恐及焉。凡吾宗祝为我祈死,先难为免。”七年夏,范文子卒。
非曰:死之长短而在宗祝,则谁不择良宗祝而祈寿焉?文子祈死而得,亦妄之大者。
长鱼矫
长鱼矫既杀三郤,乃胁栾、中行,云云。公曰:“一旦而尸三卿,不可益也。”对曰:“乱在内为宄,在外为奸。御宄以德,御奸以刑。今治政而内乱,不可谓德;除鲠而避强,不可谓刑。德刑不立,奸宄并至。臣脆弱,不能忍俟也。”乃奔狄。三月,厉公杀。
非曰:厉公,乱君也;矫,乱臣也。假如杀栾书、中行偃,则厉公之敌益众,其尤可尽乎?今左氏多为文辞,以著其言而征其效,若曰矫知几者然,则惑甚也。
戮仆
晋悼公四年,会诸侯于鸡丘。魏绛为中军司马。公子扬干乱行于曲梁,魏绛斩其仆。
非曰:仆,禀命者也。乱行之罪在公子。公子贵,不能讨,而禀命者死,非能刑也。使后世多为是以害无罪,问之,则曰魏绛故事,不亦甚乎!然则绛宜奈何?止公子以请君之命。
叔鱼生
叔鱼生,其母视之曰:“云云。必以贿死。”杨食我生,叔向之母闻其号也,曰:“终灭羊舌氏之宗。”
非曰:君子之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犹不足以言其祸福,以其有幸有不幸也。今取赤子之形声,以命其死亡,则何耶?或者以其鬼事知之乎?则知之未必贤也。是不足书以示后世。
逐栾盈
平公六年,箕遗及黄渊、嘉父作乱,不克而死,公遂逐群贼,云云。阳毕曰:“君抡贤人之后,有常位于国者而立之;亦抡逞志亏君以乱国者之后而去之。”云云。使祁午、阳毕适曲沃,逐栾盈。
非曰:当其时不能讨,后之人何罪?盈之始,良大夫也,有功焉,而无所获其罪。阳毕以其父杀君而罪其宗,一朝而逐之,激而使至乎乱也。且君将惧祸惩乱耶?则增其德而修其政,贼斯顺矣。反是,顺斯贼矣,况其胤之无罪乎!
新声
平公说新声,师旷曰:“公室其将卑乎?君之明兆于衰矣。”
非曰:耳之于声也,犹口之于味也。苟说新味,亦将卑乎?乐之说,吾于《无射》既言之矣。
射
平公射不死,使竖襄搏之,失。公怒,拘将杀之。叔向曰:“君必杀之。昔吾先君唐叔射兕于徒林,殪以为大甲。今君嗣吾先君,射不死,搏之不得,是扬吾君之耻者也。君其必速杀之,勿令远闻。”君忸怩于颜,乃趣舍之。
非曰:羊舌子以其君明暗何如哉?若果暗也,则从其言,斯杀人矣。明者固可以理谕,胡乃反征先君以耻之耶?是使平公滋不欲人谏己也。
赵文子
秦后子来奔,赵文子曰:“公子辱于敝邑,必避不道也?”对曰:“有焉。”文子曰:“犹可以久乎?”对曰:“国无道而年谷和熟,鲜不五稔。”文子视日,曰:“朝不及夕,谁能俟五?”后子曰:“赵孟将死矣。怠偷甚矣,非死逮之,必有大咎。”
非曰:死与大咎,非偷之能必乎尔也。偷者自偷,死者自死。若夫大咎者,非有罪恶,则不幸及之,偷不与也。左氏于《内传》曰“人主偷必死”,亦陋矣。
医和
平公有疾,秦景公使医和视之。赵文子曰:“医及国家乎?”对曰:“上医医国,其次疾人,固医官也。”文子曰:“君其几何?”对曰:“若诸侯服,不过三年;不服,不过十年。过是,晋之殃也。”
非曰:和,妄人也。非诊视攻熨之专,而苟及国家,去其守以施大言,诚不足闻也。其言晋君曰:“诸侯服,不过三年;不服,不过十年。”凡医之所取,在荣卫合脉理也,然则诸侯服,则荣卫离、脉理乱,以速其死;不服,则荣卫和、脉理平,以延其年耶?
黄熊
晋侯梦黄熊入于寝门,子产曰:“殛于羽山,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实为夏郊。云云。”
非曰:之为夏郊也,禹之父也,非为熊也。熊之说,好事者为之。凡人之疾,魄动而气荡,视听离散,于是寐而有怪梦,罔不为也,夫何神奇之有?
韩宣子忧贫
韩宣子忧贫,叔向贺之曰:“栾武子无一卒之田,云云。行刑不疚,以免于难。及桓子骄泰奢侈,云云。宜及于难,而赖武子之德,以没其身。及怀子改桓之行,修武子之德,而离桓子之罪,以亡于楚。云云。”
非曰:叔向言贫之可以安,则诚然;其言栾书之德,则悖而不信。以下逆上,亦可谓行刑耶?前之言曰:栾书“杀厉公以厚其家”,今而曰“无一卒之田”,前之言曰“栾氏之诬晋国久矣”,用书之罪以逐盈,今而曰“离桓之罪,以亡于楚”,则吾恶乎信?且人之善恶,咸系其先人,己无可力者,以是存乎简策,是替教也!
围鼓
中行穆子帅师伐翟,围鼓。鼓人或请以城畔,穆子不受,曰:“夫以城来者,必将求利于我。夫守而二心,奸之大者也。”
非曰:城之畔而归己者有三:有逃暴而附德者,有力屈而爱死者,有反常以求利者。逃暴而附德者庥之,曰德能致之也;力屈而爱死者,与之以不死,曰力能加之也。皆受之。反常以求利者,德力无及焉,君子不受也。穆子曰:“夫以城来者,必将求利于我。”是焉知非向之二者耶?
具敖
范献子聘于鲁,问具山、敖山,鲁人以其乡对。曰:“不为具、敖乎?”曰:“先君献、武之讳也。”献子归曰:“人不可以不学。吾适鲁而名其二讳,为笑矣,唯不学也。”
非曰:诸侯之讳,国有数十焉,尚不行于其国,他国之大夫名之,无惭焉可也。鲁有大夫公孙敖,鲁之君臣莫罪而更也,又何鄙野之不云具、敖?
董安于
下邑之役,董安于多。简子赏之,辞曰:“云云。今一旦为狂疾,而曰必赏汝,是以狂疾赏也,不如亡。”趣而出,乃释之。
非曰:功之受赏也,可传继之道也。君子虽不欲,亦必将受之。今乃遁逃以自洁也,则受赏者必耻。受赏者耻,则立功者怠,国斯弱矣。君子之为也,动以谋国。吾固不悦董子之洁也。其言若怼焉,则滋不可。
祝融
史伯曰:“夫黎,为高辛氏火正,以淳燿敦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彰,虞、夏、商、周是也。其后皆为王公侯伯。祝融亦能照显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其后八姓,于周未有侯伯。佐制物于前代者,昆吾为夏伯矣,大彭、豕韦为商伯矣。当周未有,融之兴者,其在芈姓乎?”
非曰:以虞、舜之至也,又重之以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而其后卒以殄灭。武王继之以陈,覆坠之不暇。尧之时,祝融无闻焉。祝融之后,昆吾、大彭、豕韦,世伯夏、商。今史伯又曰“于周未有侯伯”,必在楚也。则尧、舜反不足祐耶?故凡言盛之及后嗣者皆勿取。
褒神
桓公曰:“周其弊乎?”史伯对曰:“殆必于弊者也。今王弃高明昭显,而好谗慝暗昧,恶角犀丰盈,而近顽童穷固。云云。训语有之,曰:‘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为二龙,以伺于王庭。云云。’天之生此久矣,其为毒也大矣。申、缯、西戎方强,王欲杀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若伐申,而缯与西戎会以伐周,周不守矣。”
非曰:史伯以幽王弃高明显昭,而好谗慝暗昧,近顽嚚穷固,黜太子以怒西戎、申、缯,于彼,以取其必弊焉可也;而言褒神之流祸,是好怪者之为焉,非君子之所宜言也。
嗜芰
屈到嗜芰。将死,戒其宗老曰:“苟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将荐芰,屈建命去之,曰:“国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馈,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鱼炙之荐。笾豆脯醢,则上下共之。不羞珍异,不陈庶侈,夫子其以私欲干国之典?”遂不用。
非曰:门内之理恩掩义。父子,恩之至也,而芰之荐,不为愆义。屈子以礼之末,忍绝其父将死之言,吾未敢贤乎尔也。苟荐其羊馈,而进芰于笾,是固不为非。《礼》之言斋也,曰“思其所嗜”,屈建曾无思乎?且曰违而道,吾以为逆也。
祀
王曰:“祀不可已乎?”对曰:“祀所以昭孝、息民、抚国家、定百姓,不可以已。夫民气纵则底,底则滞,滞久不振,生乃不殖。”
非曰:夫祀,先王所以佐教也,未必神之。今其曰“昭孝”焉,则可也;自“息民”以下,咸无足取焉尔。
左史倚相
王孙圉聘于晋,定公飨之。赵简子鸣玉以相,问于王孙圉曰:“楚之白珩犹在乎?其为宝也几何矣?”对曰:“未尝为宝。楚之所宝者,曰观射父,又有左史倚相,能使上下说于鬼神,顺道其欲恶,使神无有怨痛于楚国。”
非曰:圉之言楚国之宝,使知君子之贵于白珩可矣,而其云倚相之德者则何如哉?诚倚相之道若此,则觋之妄者,又何以为宝?非可以夸于敌国。
伍员
伍员伏剑而死。
非曰:伍子胥者,非吴之昵亲也。其始交阖闾以道,故由其谋。今于嗣君已不合,言见进则谗者胜,国无可救者。于是焉,去之可也。出则以孥累于人,而又入以即死,是固非吾之所知也。然则员者果很人与欤?
柳先生曰:宋、卫、秦,皆诸侯之豪杰也。左氏忽弃不录其语,其谬耶?吴、越之事无他焉,举一国足以尽之,而反分为二篇,务以相乘,凡其繁芜曼衍者甚众,背理去道,以务富其语。凡读吾书者,可以类取之也。《越》之下篇尤奇峻,而其事多杂,盖非出于左氏。吾乃今知文之可以行于远也。以彼庸蔽奇怪之语,而黼黻之,金石之,用震曜后世之耳目,而读者莫之或非,反谓之近经,则知文者可不慎耶!呜呼!余黜其不臧,以救世之谬,凡六十七篇。
伊尹五就桀赞
伊尹五就桀。或疑曰:“汤之仁闻且见矣,桀之不仁闻且见矣,夫胡去就之亟也?”柳子曰:“恶,是吾所以见伊尹之大者也。彼伊尹,圣人也。圣人出于天下,不夏、商其心,心乎生民而已。曰:‘孰能由吾言?由吾言者为尧、舜,而吾生人尧、舜人矣。’退而思曰;‘汤诚仁,其功迟;桀诚不仁,朝吾从而暮及于天下可也。’于是就桀。桀果不可得,反而从汤。既而又思曰:‘尚可十一乎?使斯人蚤被其泽也。’又往就桀。桀不可,而又从汤。以至于百一、千一、万一,卒不可,乃相汤伐桀。俾汤为尧、舜,而人为尧、舜之人,是吾所以见伊尹之大者也。仁至于汤矣,四去之;不仁至于桀矣,五就之,大人之欲速其功如此。不然,汤、桀之辨,一恒人尽之矣,又奚以憧憧圣人之足观乎?吾观圣人之急生人,莫若伊尹;伊尹之大,莫若于五就桀。”作《伊尹五就桀赞》:
圣有伊尹,思德于民。往归汤之仁,曰仁则仁矣,非久不亲。退思其速之道,宜夏是因。就焉不可,复反亳殷。犹不忍其迟,亟往以观。庶狂作圣,一日胜残。至千万冀一,卒无其端。五往不疲,其心乃安。遂升自陑,黜桀尊汤,遗民以完。大人无形,与道为偶。道之为大,为人父母。大矣伊尹,惟圣之首。既得其仁,犹病其久。恒人所疑,我之所大。呜呼远哉,志以为诲。
梓人传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欵其门,愿佣隟宇而处焉。所职寻引、规矩、绳墨,家不居砻斫之器。问其能,曰:“吾善度材,视栋宇之制,高深、圆方、短长之宜,吾指使而群工役焉。舍我,众莫能就一宇。故食于官府,吾受禄三倍;作于私家,吾收其直太半焉。”他日,入其室,其床阙足而不能理,曰:“将求他工。”余甚笑之,谓其无能而贪禄嗜货者。
其后京兆尹将饰官署,余往过焉。委群材,会众工。或执斧斤,或执刀锯,皆环立向之。梓人左持引,右执仗而中处焉。量栋宇之任,视木之能,举挥其杖曰“斧!”彼执斧者奔而右;顾而指曰:“锯!”彼执锯者趋而左。俄而斤者斫、刀者削,皆视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断者。其不胜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画宫于堵,盈尺而曲尽其制,计其毫厘而构大厦,无进退焉。既成,书于上栋,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则其姓字也。凡执用之工不在列。余圜视大骇,然后知其术之工大矣。
继而叹曰:彼将舍其手艺,专其心智,而能知体要者欤?吾闻劳心者役人,劳力者役于人,彼其劳心者欤?能者用而智者谋,彼其智者欤?是足为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为天下者本于人。其执役者,为徒隶,为乡师、里胥;其上为下士;又其上为中士、为上士;又其上为大夫、为卿、为公。离而为六职,判而为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连率。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啬夫、版尹,以就役焉,犹众工之各有执伎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举而加焉,指而使焉,条其纲纪而盈缩焉,齐其法制而整顿焉,犹梓人之有规矩、绳墨以定制也。择天下之士,使称其职;居天下之人,使安其业。视都知野,视野知国,视国知天下,其远迩细大,可手据其图而究焉,犹梓人画宫于堵而绩于成也。能者进而由之,使无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愠。不炫能,不矜名,不亲小劳,不侵众官,日与天下之英材讨论其大经,犹梓人之善运众工而不伐艺也。夫然后相道得而万国理矣。相道既得,万国既理,天下举首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后之人循迹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谈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执事之勤劳而不得纪焉,犹梓人自名其功而执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谓相而已矣。其不知体要者反此:以恪勤为公,以簿书为尊,炫能矜名,亲小劳,侵众官,窃取六职百役之事,听听于府廷,而遗其大者远者焉,所谓不通是道者也。犹梓人而不知绳墨之曲直、规矩之方圆、寻引之短长,姑夺众工之斧斤刀锯以佐其艺,又不能备其工,以至败绩用而无所成也。不亦谬欤?
或曰:“彼主为室者,傥或发其私智,牵制梓人之虑,夺其世守而道谋是用,虽不能成功,岂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绳墨诚陈,规矩诚设,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狭者不可张而广也。由我则固,不由我则圮。彼将乐去固而就圮也,则卷其术,默其智,悠尔而去,不屈吾道,是诚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货利,忍而不能舍也,丧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栋挠屋坏,则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
余谓梓人之道类于相,故书而藏之。梓人,盖古之审曲面势者,今谓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杨氏,潜其名。
宋清传
宋清,长安西部药市人也。居善药。有自山泽来者,必归宋清氏,清优主之。长安医工得清药辅其方,辄易雠,咸誉清。疾病疕疡者,亦皆乐就清求药,冀速已。清皆乐然响应,虽不持钱者,皆与善药,积券如山,未尝诣取直。或不识遥与券,清不为辞。岁终,度不能报,辄焚券,终不复言。市人以其异,皆笑之,曰:“清,蚩妄人也。”或曰:“清其有道者欤?”清闻之曰:“清逐利以活妻子耳,非有道也,然谓我蚩妄者亦谬。”
清居药四十年,所焚券者百数十人,或至大官,或连数州,受俸博,其馈遗清者,相属于户。虽不能立报,而以赊死者千百,不害清之为富也。清之取利远,远故大,岂若小市人哉?一不得直,则怫然怒,再则骂而仇耳。彼之为利,不亦翦翦乎!吾见蚩之有在也。清诚以是得大利,又不为妄,执其道不废,卒以富。求者益众,其应益广。或斥弃沉废,亲与交;视之落然者,清不以怠,遇其人,必与善药如故。一旦复柄用,益厚报清,其远取利,皆类此。
吾观今之交乎人者,炎而附,寒而弃,鲜有能类清之为者。世之言,徒曰“市道交”。呜呼,清,市人也,今之交有能望报如清之远者乎!幸而庶几,则天下之穷困废辱得不死亡者众矣,市道交岂可少耶?或曰:“清,非市道人也。”柳先生曰:“清居市不为市之道,然而居朝廷、居官府、居庠塾乡党以士大夫自名者,反争为之不已,悲夫!然则清非独异于市人也。”
童区寄传
柳先生曰:越人少恩,生男女,必货视之。自毁齿已上,父兄鬻卖,以觊其利。不足,则取他室,束缚钳梏之。至有须鬣者,力不胜,皆屈为僮。当道相贼杀以为俗。幸得壮大,则缚取么弱者。汉官因以为己利,苟得僮,恣所为不问。以是越中户口滋耗。少得自脱,惟童区寄以十一岁胜,斯亦奇矣。桂部从事杜周士,为余言之。
童寄者,郴州荛牧儿也。行牧且荛,二豪贼劫持反接,布囊其口,去逾四十里之虚所卖之。寄伪儿啼,恐慄为儿恒状。贼易之,对饮,酒醉。一人去为市,一人卧,植刃道上。童微伺其睡,以缚背刃,力下上,得绝,因取刃杀之。逃未及远,市者还,得童大骇。将杀童,遽曰:“为两郎僮,孰若为一郎僮耶?彼不我恩也。郎诚见完与恩,无所不可。”市者良久计曰:“与其杀是僮,孰若卖之;与其卖而分,孰若吾得专焉。幸而杀彼,甚善。”即藏其尸,持童抵主人所,愈束缚牢甚。夜半,童自转,以缚即炉火烧绝之,虽疮手勿惮,复取刃杀市者。因大号,一墟皆惊。童曰:“我区氏儿也,不当为僮。贼二人得我,我幸皆杀之矣,愿以闻于官。”
墟吏白州,州白大府,大府召视,儿幼愿耳。刺史颜证奇之,留为小吏,不肯。与衣裳,吏护还之乡。乡之行劫缚者,侧目莫敢过其门,皆曰:“是儿少秦武阳二岁,而讨杀二豪,岂可近耶!”
河间传
河间,淫妇人也。不欲言其姓,故以邑称。始妇人居戚里,有贤操。自未嫁,固已恶群戚之乱尨,羞与为类,独深居为翦制缕结。既嫁,不及其舅,独养姑,谨甚,未尝言门外事。又礼敬夫宾友之相与为肺腑者。
其族类丑行者谋曰:“若河间何?”其甚者曰:“必坏之。”乃谋以车众造门,邀之遨嬉,且美其辞曰:“自吾里有河间,戚里之人日夜为饬厉,一有小不善,唯恐闻焉。今欲更其故,以相效为礼节,愿朝夕望若仪状以自惕也。”河间固谢不欲。姑怒曰:“今人好辞来,以一接新妇来为得师,何拒之坚也?”辞曰:“闻妇之道,以贞顺静专为礼。若夫矜车服、耀首饰,族出欢闹,以饮食观游,非妇人宜也。”姑强之,乃从之游。过市,或曰:市少南入浮图,有国工吴叟始图东南壁,甚怪,可使奚官先壁道乃入观。观已,延及客位,具食帷床之侧。闻男子咳者,河间惊,跣走出,召从者驰车归。泣数日,愈自闭,不与众戚通。戚里乃更来谢曰:“河间之遽也,犹以前故,得无罪吾属耶?向之咳者,为膳奴耳。”曰:“数人笑于门,如是何耶?”群戚闻且退。
期年,乃敢复召,邀于姑,必致之。与偕行,遂入阝豊阝岂州西浮图两间,叩槛出鱼鳖食之,河间为一笑,众乃欢。俄而又引至食所,空无帷幕,廊庑廓然,河间乃肯入。先壁群恶少于北牖下,降帘,使女子为秦声,倨坐观之。有顷,壁者出宿选貌美阴大者主河间,乃便抱持河间。河间号且泣,婢夹持之,或谕以利,或骂且笑之。河间窃顾视持己者甚美,左右为不善者已更得适意,鼻息咈然,意不能无动,力稍纵,主者幸一遂焉。因拥致之房,河间收泣甚适,自庆未始得也。至日仄,食具,类呼之食。曰:“吾不食矣。”旦暮,驾车相戒归,河间曰:“吾不归矣。必与是人俱死。”群戚反大闷,不得已,俱宿焉。夫骑来迎,莫得见。左右力制,明日乃肯归。持淫夫大泣,啮臂相与盟而后就车。
既归,不忍视其夫,闭目曰:“吾病。”与之百物,卒不食。饵以善药,挥去。心怦怦,恒若危柱之弦。夫来,辄大骂,终不一开目,愈益恶之,夫不胜其忧。数日,乃曰:“吾病且死,非药饵能已,为吾召鬼解除之,然必以夜。”其夫自河间病,言如狂人,思所以悦其心,度无不为。时上恶夜祠甚,夫无所避。既张具,河间命邑臣告其夫召鬼祝诅,上下吏讯验,笞杀之。将死,犹曰:“吾负夫人,吾负夫人!”河间大喜,不为服,辟门召所与淫者,倮逐为荒淫。
居一岁,所淫者衰,益厌,乃出之。召长安无赖男子,晨夜交于门,犹不慊。又为酒垆西南隅,己居楼上,微观之,凿小门,以女侍饵焉。凡来饮酒,大鼻者,少且壮者,美颜色者,善为酒戏者,皆上与合。且合且窥,恐失一男子也,犹日呻呼懵懵,以为不足。积十余年,病髓竭而死。自是虽戚里为邪行者,闻河间之名,则掩鼻蹙皆不欲道也。
柳先生曰:天下之士为修洁者,有如河间之始为妻妇者乎?天下之言朋友相慕望,有如河间与其夫之切密者乎?河间一自败于强暴,诚服其利,归敌其夫犹盗贼仇雠,不忍一视其面,卒计以杀之,无须臾之戚。则凡以情爱相恋结者,得不有邪利之猾其中耶?亦足知恩之难恃矣!朋友固如此,况君臣之际,尤可畏哉!余故私自列云。
刘叟传
鲁有刘叟者,尝以御龙术进于鲁公。云云。刘叟曰:“岁不雨,无以出终无以入。民枯然视天,卿士大夫绝智,谋山川祷神祇以祈,咸不应。臣投是龙于尺地之内,不逾晷,雷孚上下,雷孚东西,于是先之以风,腾之以去,从之以雨。如君之意,欲一邑足之,欲一国足之,欲天下足之。”鲁公曰:“斯龙也其神乎?是则寡人之国非敢用。”刘叟曰:“臣闻避风雨,御寒暑,当在未寒暑乎?是故事至而后求,曷若未至而先备。”于是鲁公止刘叟而内龙。明年,果大旱。命刘叟出龙,果大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