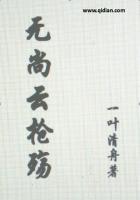凌云怕过多地谈论问题会伤害到周承恩,就直奔主题:“问题就不谈了。我想冲击一下现状,对企业内部采取一些措施。现在,搞经济建设,班子、路子和我们脑子都应该着眼于票子。”
周承恩首肯地点头。
“我想对企业内部作一次大手术。”凌云把话引入正题,“矿机关,矿区机关科室太多,地面后勤职工太多,因人设岗的问题太严重。干部和后勤人员必须坚决消肿,压减三、四百人充实井下生产一线……”
“嗯?”周承恩心里一震,压减三、四百干部和后勤服务人员?好大的口气!动三、四十人就要闹得你晕头转向。他心里这么想,但未动声色,仍笑着,似乎在鼓励凌云说下去。
凌云的情绪渐渐地激动起来:“现在,矿井里缺人干活,地面上缺活人干。去年招收的井下临时合同工人,就有几十人干起地面工作。一个矿山井下企业,井下一线的矿工只占职工总数一半多点,而地面单位只有机修分厂、汽车队、机电队、职工医院和子弟校,两、三千地面人员在干什么?矿机关将近三百人,这样大一幢办公大楼居然还不够用!我清理了一下,一个矿区,不包括脱产的采、掘队长、支部书记,仅矿区机关又是近百人,养的闲人太多了。”
周承恩说:“这是前年企业达标时搞出来的。”
“必须解决!”凌云斩钉截铁地说,“企业不是养老院!人浮于事,导致职责不分,责任不明。还有,企业管理体制极其不顺畅,必须坚决实行全企业全面计划管理。现在,生产科不管实际生产数据,供应科不管库房,销售科不管销售,成本科不知道矿区、分厂真实成本,财务科秋后算账,死后验尸,机电科不知道设备台件…… 表面上看,企业井然有序。实际上,根本不是在有效地控制下运转。矿长是傀儡!是给下面收拾残局的冤大头!企业除了职工人数和实际支出的资金是真实的,其他数据都是建立在矿区、分厂、院校和队所不真实的报表基础上的虚假东西。管理完全失控,矿长被下面牵着鼻子走,成天疲于奔命,最终劳而无功。”
凌云短短几句话,把周承恩听呆了,企业里如此深层次的问题,他一个多月时间就洞幽烛微透视了出来!
凌云一直在观察周承恩的脸色:“也许,我言过其实…… ”
周承恩沉思着,说:“你说,谈谈你的措施。”
凌云递了一支烟给周承恩,自己也点了一支,说:“重症就得下猛药!企业要在有效的控制下运转,必须多管齐下,综合治理。所有的问题都是人造成的,就得从人着手。第一,机关消肿,精简冗员。和尚多了没水吃,艄公多了打烂船,庙门多了难行礼。办公室与行政科、劳资科、总务科合并,生产科与技术科、质检科、基建科合并,安全科与通风科合并,供应科与销售科、物管科合并,机电科与设备科、机电队合并,财务科与统计科、成本科合并。建议党委只设办公室和政工科,其他科室一律撤销,矿机关只保留一百人左右。”
周承恩怔住了:“其余一、二百人怎么办?”他倒吸了一口凉气。
“精简到矿区、分厂去。”
“下面拿着怎么办?”
凌云决然地说:“从矿区、分厂压减三、四百人到井下采掘一线去!”
周承恩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无异于痴人说梦!触动企业复杂人际关系网,不仅仅企业寸步难行,自己和凌云也休想全身而退!他看了一眼凌云,故作轻松地笑道:“你的想法很好,但根本行不通…… ”
“为什么?”凌云急切地问。
周承恩沉思片刻,说:“科室设立是按地区相关部门的要求设立的,人员是人事局核定的,撤得了吗?”
凌云说:“我们是厂长负责制试点企业,机构设置和中层干部任免权已经放给企业。”
“一次撤这么多机构,免这么多干部,不谈管理权限问题,我问你:减谁?留谁?怎么精简?机关干部绝大多数是国家干部,这会引起多大的矛盾?年老的干部动得了吗?从地面压减几百人下矿井劳动,怎么压?压减谁?压减谁,谁找你扯皮。人际关系是一张盘根错节的网,牵一发动全身,你拿机关人员开刀,企业必然大乱!”周承恩急了。
凌云说:“人员问题是死结,不用铁手腕,一切问题都无法解决!改革,就是破掉企业干部的铁交椅、职工的铁饭碗和铁工资。要搞活企业,这道难关必须闯,这个死结必须解。”
“怎么闯?”周承恩反问:“砸了铁饭碗,给不给人家一个胶饭碗、泥饭碗?砸了铁交椅给不给一张木凳子,石墩子?人的问题,相当敏感复杂,那一个干部背后没有微妙的社会关系?几个人的事好办,几十个人的事难办,牵涉几百人的事怎么办?”
凌云说:“这就靠宣传教育和思想发动,要让大家明白:安于现状,企业活不起来,职工也富不起来,最终大家都吃不饱。”
周承恩为凌云的天真感到好笑,事情如此简单,还用得着你指点吗?他不想打击凌云的积极性,心里很不以为然地问:“除了人的问题,你还有什么打算?”
“下决心改革内部管理体制。”凌云说:“该放的权彻底放下去,责任也随之而放下去;该收的权坚决收上来,企业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全面计划管理。管理体制不顺,是导致企业管理混乱的根源。企业的现状是权利在基层,责任在矿上。我的意见:汽车队和汽修厂分离开,职工医院,机修分厂实行独立核算,放开经营。我算过一笔账,我们自己汽车队的运输费比专业运输公司高十一个百分点!仅此一项,企业每年要多支付几十万元运输成本。还有那近百人的汽修厂,不仅人浮于事,而且,很多配件根本没有用到矿里的汽车上,账却摆在自己的汽车上。机修分厂从来没有间断过给小煤窑修理和加工,却不见收到多少费用。他们给矿区生产的东西,比在市场上买的还贵。和尚挣了钱,木鱼糟了殃!职工医院的技术力量很强,骨科在全区都小有名气,要让他们扬其所长,八仙过海,挣钱回来。且不说,要这些单位为企业挣多少钱,至少,不能让矿工累死累活养他们;至少,不能让他们挖企业的生肉。这又涉及人员过多的问题。我查过,近三年,机修分厂从两个矿区调了上百人进去。放开经营,独立核算后,他们还会养闲人吗?当然不会。问题又集中在人的问题上。”
周承恩表情严峻了:“问题是,从井下调到井上工作的人,多数是老、弱、病、残,压减得了吗?”
“不尽然。真正的老、弱、病、残,企业应当照顾。但是,假伤、假病,通过关系调出来的人,必须坚决调回去,谁也没有权力要别人养着!不想下井的人多,特别是青年矿工。我听说放牛坪的熊忠,为了到井上来工作,把自己的两根手指伸进矿车轮子下轧断,如愿到了地面工作,一天却无所事事,四处惹是生非。还有,去年招收的井下合同工,几十个人是如何到的地面工作?自己的人都养不活,还招几十个人来白白养着,真是岂有此理!”凌云越说越激动。
周承恩说:“有几个人是地区几个部门和万山市、云山县的领导找的我们。企业很多事有求于他们…… ”
凌云打断周承恩的话:“又是所谓的关系!企业不是唐僧肉,不是养老院,更不是福利院!钱,天上不落,地下不生,要人干活去挣!矿长也不是哭脸抹泪,四处要钱的大乞丐!这问题,必须解决。管理体制要改,与矿区、分厂、车间的结算方式要改、职工工资分配也要改。要用合理的指标把矿区、分厂、车间控制住,要用实实在在的数据逼迫矿区、分厂抓管理,降成本。今后,矿区只负责生产、安全、质量、成本;矿上把销售供应、物资管理、产品管理、资金管理的权利、责任收上来,交职能科室负责履职。必须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形成全矿一盘棋,上下齐手抓效益的局面!”
周承恩缓缓地从椅子起身,表情很严肃地在办公室里来来回回地走动,心里已是翻江倒海。他承认凌云所指出的问题不仅客观存在,而且凾待解决,要解决这些问题,也只能按凌云所指的路子走。他惊叹凌云锐利的目光和严密的思维,感叹凌云敏捷的才智和过人的胆略。他无法想象,仅仅一个月时间,凌云竟能把企业的情况摸得如此透彻,想得如此透切!难怪他一天晓行夜不宿,日无暇晷;难怪他消瘦得如此厉害;难怪地委敢把这么大的企业交给他。周承恩感慨万千,思绪万千。他在努力平息心潮,清理思绪。
凌云见周承恩不语,继续说:“国营企业管理混乱,人员臃肿,权责不明,推过揽权是通病,我就此专门写了几篇文章发表在省工人报上。但是,都没有引起企业的重视。”
周承恩牵强笑了一下:“企业根本就不敢动。理论和实践,上面的要求和基层的实际是有距离的。”
凌云说:“国营企业确实到了不改不行,非改不可的时候了。就明月峡煤矿而言,眼下还能拖,但是,越拖问题会越多,矛盾会更加尖锐。就像病入膏肓的人讳疾忌医;解决问题和矛盾,也就像医生做手术,拿着白晃晃的刀,在病人眼前晃来晃去,病人精神更加痛苦,不如出奇不意,一刀下去!”
周承恩止住步,淡淡一笑。又走到窗前眺望春光,他的思绪渐渐清理了出来,回头笑对凌云,仍不说话,心里想:你有治病的良药吗?你没有,我也没有,甚至连止痛药都没有!几千人的企业岂能当儿戏?如此狗急跳墙般地干事,无疑于饮鸩止渴。这比捅马蜂窝更可怕,更危险——简直就是自己跳进油锅里煎熬。一旦捅出乱子,企业雪上加霜,凌云也将灰头土脸,结果:两败!
周承恩站在窗前:窗外,春光格外绚丽。
凌云望着周承恩的背影说:“伯伯,我还想把行政班子调整一下,刘矿长和吴矿长都是五十岁上下的人了,他们在一线干得很吃力,让他们退下来吧。”
周承恩转身,又回到办公桌前坐下,说:“刘矿长倒是该休息了,他和很多老矿工一样,几岁就下矿给资本家拉煤,在井下干了四十多年。他的病,我怀疑很麻烦,他说是尘肺病…… 你的意思谁来接替?”
“杨建业。”凌云说。
“他?”周承恩一惊,说:“不行!你咋会想到他?”
“竹林沟的各项工作都在全矿前面啊!”凌云不解地看着周承恩。
“竹林沟这两年的工作全靠刘矿长和秦和平。你还不了解杨建业,他的毛病很深沉,胆子太大……”
凌云说:“杨建业思路敏捷,头脑相当清醒。胆子大并不是坏事嘛,有胆量的人必然有胆识,用人不能求全责备。古人讲:骏马能历险,犁田不如牛,坚车能负重,渡河不如舟…… ”
“强盗胆子大,你用吗?”周承恩说出这话,自己也忍不住笑,“按惯例,应先从矿区总支书记中考虑,冯军和朱天福都不错。不过,从年轻化、知识化考虑,赵敬国更合适。”
凌云问:“和平怎么样?”
周承恩说:“和平也不行!他才工作两、三年时间,今年刚满二十五岁,这么大的企业,没有资历和阅历,不能服众…… ”
“这是用人才,不能搞论资排辈,更不是论功请赏。你们那一辈人,二十来岁就带兵打仗了!”凌云说。
周承恩又站起来,在办公室里踱步。现在,他彻底冷静了,心思不是在班子问题上,而是在思考如何说服凌云,制止他不要对企业轻举妄动,企业改革从上至下讲了一、两年,谁也说不清该怎么搞,没必要出这个风头,惹火烧身。他想想说:“班子人选问题,你再考虑一下吧。成熟了,再研究…… 凌云,你神经绷得太紧了,五一节,和洁明、和平参加一下文体活动。年轻人,来日方长,要干很多事情。”
凌云不解地望着周承恩,他急切想听到长辈的想法和意见。他知道长辈做事忧深思远,正在思考、抉择之中。是的,自己选择的路有风险有困难。但是,不冒这个险,企业就走不出这片沼泽地,就会沉陷下去!他心里很急:“伯伯,我刚才谈的是企业的问题,您在企业所做的工作是有目共睹的…… ”
周承恩笑笑,又走到窗前凝思不语。他确实不想给凌云的一腔热血中倒进冷水,却又找不出恰当的语言来说服凌云。他担心凌云画虎不成反类犬,既害企业,又害他自己。
办公室里陷入了难捱的沉默。
沉默许久后,周承恩仍背对凌云,问:“凌云,我前次给你讲的话,你听懂了吗?”
“我想过。但我认为,我有能力解决企业的问题!”凌云态度很坚决。
“你不回万山了?”
“我没想过…… ”凌云不想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周承恩转身,走到凌云对面坐下,慈祥地看着凌云:“凌云,伯伯为你的成熟和强烈的事业心、责任心、上进心感到高兴,你的确是一个难得的人才。你想的、说的,都对。可是啊,伯伯不同意你这样做…… ”
“为什么?”凌云惊异地看着周承恩。
“伯伯可能说不过你,就不讲大道理。”周承恩语重心长地说,“我说两点,第一呢,企业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和社会工程,需要社会的联动、各方的配合才能完成。这与打仗一样,单兵深入要吃大亏,到时,想退也退不出来。工作过于激进于你个人,于企业都不是好事。所谓欲速则不达,物极必反就在这些方面。第二呢,伯伯不想让你陷入这潭烂泥。企业的路,会越走越艰难…… 不改革,是一条死路,改革,对矿长来说,是一条九死一生的险途!依你的学识和能力,大有发展空间,大有前途。现在,还有脱身的机会,就不要陷下去…… ”
“可是,”凌云急了,“伯伯…… ”
“好了,不说了!”周承恩摆摆手,“我说过,我说不过你。企业改革的账,伯伯给你完结:下几个不听招呼的干部,处理一批长期旷工缺勤的职工;今年,计划亏损二百万元,我们就亏一百五十万元,上下的面子都过得去…… ”
“伯伯,”凌云强行打断周承恩的话,着急地说:“企业怎么办?我不是想当什么‘改革者’ 要什么政绩、面子,企业再不能这样拖了!我想抓住机遇,加快企业发展,让企业活起来,强起来,不再成为国家负担;也让职工上班有一个安全的生产条件,下班有一个舒适的休息环境,起码,家属来了有一间房…… ”
周承恩说:“我理解你。可是,当涉及到个人的切身利益时,职工会理解你吗?出了差错,领导会理解你吗?凌云哪,伯伯是过来人,相信伯伯不会害你…… ”
“可是…… ”凌云涨红着脸,欲力陈己见,副矿长吴才全找党委书记说徐峰上山打猎的事,推闼直入。
周承恩果断地结束了与凌云的话题:“这件事到此为止,不再说了。老吴,有亊吗?”他想,必须尽快断了凌云的另一条路。
凌云看了看周承恩和吴才全,情绪一落千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