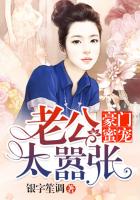神经性厌食的文化建构
神经性厌食是进食障碍的一种。患者没有食欲不振的体验,而是尽管很饿,渴望食物,但是却选择不吃东西,拒绝食用“发胖”食物,采取种种减肥措施,如自我催吐,滥用泻药或利尿药物,过度锻炼和使用可抑制食欲的烟、咖啡甚至毒品,以致体重低于标准体重15%以上。他们常常过分关心自身的体型或食物的热量,病态地害怕发胖,对体重减轻感到高兴,而且与正常的节食不同,神经性厌食患者的体重下降目标一直在变,一旦设定的体重目标完成,又定出更低的目标,对所获得的成功从不会满足。在节食过程中,还会出现许多躯体、心理和行为症状,如女性因内分泌紊乱出现停经,男性的性欲减退和阳痿,体温过低,血压下降,心率过缓,毛发脱落,焦虑,情绪不稳,餐间悄悄丢弃食物,过度饮水等等。
神经性厌食这个病名来自西方医学,曾经被认为是西方发达国家女性特有的问题。“在许多文化中,都对身材丰满的女性推崇有加---特别是在那些食物匮乏的贫穷地区。”宾夕法尼亚州马伦博格学院人类学教授科瓦茨伯纳特说。在西非,尼日利亚当地的女性以胖为美。神经性厌食在亚洲,特别是中国大陆一直以来未受重视,十年前所报道的病例还寥寥无几。但近年来,随着亚洲经济的发展,在亚洲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和中国香港、台湾等地,神经性厌食在年轻女性中正在成为一个日益突出的临床问题。在一些中低收入国家的大都市如中国大陆的北京、上海及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也逐渐增多。尽管亚洲妇女在总体上较欧美女性苗条得多,但怕胖的趋势仍然在形成,而这又显然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凸显出来,与经济全球化所引起的外来文化价值观念侵入和同化有着某种内在的必然的联系。社会的现代化增加了女性对神经性厌食的易感性,或许是因为其带来的性别化社会机会和限制。在平面和影视媒体、广告中,化妆品、减肥食品(药品)、时装模特的模式体型充斥着人们的所见所闻,无时无刻不在重塑人们的审美观,潜移默化地改造着人们对优美体态的认知。可以预料,在亚洲国家不断上升的进食障碍患病率将会构成一种对公共卫生的新挑战。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病人很少主动在各科医生处就诊,更少有接受必要的心理干预和心理治疗,相关治疗机构和从业人员也很少。
亚洲地区还没有过关于神经性厌食在社会中的患病率和发病率的流行病学调查,仅有的一些零星估计,如李诚等在香港所做的调查,显示患病人数不可低估。香港预计有3%-10%的年轻女性患某种程度的进食障碍需要治疗,而且自90年代后期以来趋势是在增长;新加坡的情况极为类似。这些地方的媒体常常向公众宣传过分控制体重行为的上升趋势、死于未经治疗的厌食症女性案例,以及从神经性厌食康复的名人。因此,一般民众如今对神经性厌食的认识提高了,知道这是一种因害怕脂肪及其他原因引起的对食物病态的拒绝。
但是,神经性厌食不仅仅是对脂肪的排斥问题。人们对进食、食物和体重的体验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厌食应有全新的解释。生物医学对于这个问题探讨得很少,且只是把这些患者回避食物和催吐单纯归结为怕胖。正如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疾病分类》第10版所描述的,神经性厌食的基本临床表现包括:1.体重指数(BMI)17.5或以下,或按照年龄和性别,其体重维持在低于预期体重或标准体重的15%或更多;如果处于青春期前,其生长发育期内体重增长达不到预期标准;2.体重减轻是自己造成的,包括拒绝食用“发胖食物”和采用其他减肥措施,如自我催吐,滥用泻药或利尿剂,过度锻炼和使用食欲抑制剂;3.体象扭曲,表现病态地害怕发胖;4.内分泌紊乱,在女性表现为停经,男性表现为性欲减退和阳痿……其中的第二条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第三条标准---产生于对发胖的恐惧---一直被认为是神经性厌食的“核心”病理症状。因此,一个不肯进食的厌食症患者合情合理的借口就是:“我不要发胖,我已经够胖的了。”有些治疗该病的权威人士建议把“肥胖恐怖”或“体重恐怖”的解除作为康复的一项先决条件。
从历史上看,拒食现象的报道可以上溯至公元5世纪,当时有所谓“神奇少女”和“斋戒女孩”之称,但对于她们的主观动机和拒食的意义不得而知。不过,像现代生物医学意义上的极端的拒食则没有。随着厌食的意义从神性和宗教转型为病态,早期的病人被赋予一系列不同的名称,如“神经性消化不良”或“内脏性神经症”等。马塞(LouisVictorMarce)写道:“这些病人达到神经错乱的信念,即自己不该或不能吃……一切的心智力量都以胃的功能为中心……这些不幸的病人只能获得部分能量以抵御营养的诱惑”;夏考(Charcot)也认为厌食症是胃神经的一种歇斯底里病症。在1958年美国发表的一篇广征博引的综述中,神经性厌食病人的心因性挨饿被依次归纳为“不想吃”、“食物恐怖”、“对食物反感”或“真正丧失胃口”,并且“几乎所有病人都发现有各种与胃肠道有关的其他症状”。
较近的研究肯定了神经性厌食病人的胃肠功能紊乱具有生物学基础并贯穿于疾病始终,如胃排空延迟产生“饱胀感”,反过来强化了厌食行为。不难想象,在缺乏普遍的文化意义上的怕胖基础时,早期的神经性厌食病人很容易把他们的症状解释为生物学上的消化障碍,但后者绝不仅仅代表生理问题,而是应该放在社会情境中看待。比如说,在维多利亚时代,这些内脏不适感使年轻妇女表达女性柔弱的理念方面十分类似于今天的怕胖。另一方面,肥胖在社会生产力不发达的时代和地区,曾经或仍是富足(对男性而言)或生育力强(女性的首要使命之一)的象征。香港研究神经性厌食的学者李诚(1989)提出,传统的中国人赞赏丰满圆润的体态,喜好美食,以此来解释中国社会里神经性厌食的罕见,也因为文化意义上的怕胖尚不普遍,因而香港的神经性厌食病人不表现出对肥胖的强烈恐惧,而后者是发达国家里本病的核心症状。
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亚洲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生活的日益富足,临床上见到的神经性厌食患者愈来愈多,但从症状表现上仍然与西方社会的病人不太一样,一个原因是西方世界的“苗条即是美”的理念尚未得到中国文化的认可,另外,与西方的年轻女性相比,中国社会里的这些病人在患病前就很苗条,根本毋须节食以减轻体重。
进入90年代后,新的研究数据表明,尽管按照西方标准,亚洲或中国妇女的平均体重依然偏低,但在西方文化的强大影响下,作为西方文化影响的后果之一,追求消瘦,害怕肥胖成为一种时尚,女性中有意识地节食和减轻体重非常流行,表现出文化的“同化”特征。
作为一种社会心理语言,神经性厌食的症状有其特定的意义。在对两名不典型厌食症病人的民族志研究中,李诚注意到她们成长于创伤性的局部世界,遭受过性虐待、父母问题和遗弃,对食物的拒绝作为苦难的象征,是以“胃胀”、“没胃口”这样的躯体诉说表现出来的。丧失吃的兴趣代表着在一个压抑的社会世界中丧失声音。这些研究显示,拿怕胖来解释神经性厌食的原因忽视了自我挨饿的隐喻的重要性,不适用于所有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反映出西方对该病的诊断标准是从西方文化出发的,过于强调肥胖恐怖,这可能会混淆临床医生对该病真正的理解。关于这一点,里腾堡(Ritenburg)也指出,神经性厌食是一种与西方文化相关的综合征。只有在经过别的文化重新建构以后,它才不属于特定的西方社会,而成为植根于“现代化”或“全球化”的跨国文化的、出现于世界上许多正在迅速城市化和日渐富裕的地方的文化现象。精神病学中文化和精神症状的辩证关系,神经性厌食顺从和抗争对于苗条的文化追求的矛盾,成为批评的焦点。
对于体型的不满,是李诚等(1996)在另一项研究中注意到的。香港男性希望更高大、上身更健硕,而女性则感到下半身太胖,希望腰、臀、大腿更瘦。显然,西方式的对完美体型的要求使传统中国文化对女性审美强调脸蛋和其他非躯干方面的观点黯然失色,中国文化正在失去对神经性厌食的保护作用。
神经性厌食所体现的性别差异,实质上体现出两性的权力差异。无论“以胖为美”,还是“以瘦为美”,所反映的只能是男性权力至上的审美观点。“女为悦己者容”,女性的发展、进入社会、参与公共事务,乃至生存的权力,仍然要获得男性的认可。在这样的情形下,女性不可能有完全自由的意志,来决定和支配自己的身体。性感、美丽成为女性的身体语言,以此作出某种程度或某种意义上的交换,才能或更容易涉足男性把持的领域。这时,社会的女性价值观必定会在一定程度上内化为女性自身的价值观。如果你不相信,可以马上打开电视,看看电视广告里有多少是瘦身减肥、美容美发、化妆品或时装等内容。这些商品的直接消费者看似女性,实则是男性。
今天的社会里,偏瘦的女性、某种程度的瘦骨嶙峋是富有魅力的象征,厌食在媒体中获得美化,模特儿用厌食、吸烟或滥用毒品保持她们的身材。无可辩驳的是,害怕肥胖、希冀更美在当前商品社会中鼓励女性约束自己的身体,养活、造就了无所不在的“美丽”产业。事实上,这个产业的历史,足以证实它代表了20世纪资本主义工业最了不起的成功之一。由于节食者必然的失败和医学上对体重控制的研究发展,这一市场自发生成并逐渐扩展;与此同时,自60年代以来,理想的女性体型趋向消瘦。因此毫不奇怪,厌食症与其他一些神经症性障碍相比,在学术界和社会上的形象都要好得多,在这一过程中,来自有影响力的机构如大众媒体的流行观点确实影响到对神经性厌食的专业观点,使得专业人士和不具备生物医学知识的民众对本症有极为相似的认识和看法。寓示着专业人员并不如他们自己所以为的那样超然和实证主义,而是会以与大众相似的方式建构和包装知识。民间理论和专业观点只是社会建构的世界的相互依存的不同侧面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