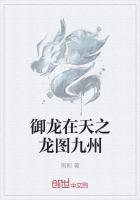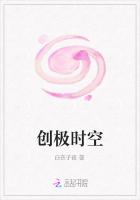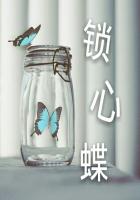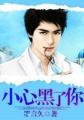牟宗三的“一心开二门”,在强调“道德的优先性”上诚然是继承了儒家的传统;其以“心”(良知)为本体,更倾向于儒家中的陆王一系。但牟宗三在梳理、诠释儒学的历史发展时,无视或忽视了儒学与佛教在宇宙论、存有论上还有“始于一气”和“本乎一心”的对立(明儒刘宗周虽有“释氏之本心,吾儒之学亦本心”之说,但其云“盈天地间一气而已矣”,“心以物为体,离物无知”,“释氏言心便言觉……亦只是虚空圆寂之觉,与吾儒体物之知不同”,见《读易图说》、《学言》上。其所谓儒之“本心”与佛教之“本心”意义有不同)。张灏在“当代新儒家与中国的现代化”座谈会上曾指出,“气化的宇宙观”(又“姑且叫它‘宇宙论式的神话’”,这后一称呼有片面性,因其还有非神话的一面),“在儒家自始至终保有一重要的地位”,而新儒家“有意无意的把这东西避开不谈,或者不像从前那么强调,有的时候甚至完全不提”,这在新儒家理论上“是一个突破”,但是“不谈这个东西,就无法正视中国儒家传统的一些基本命题,因为哲学的突破,可能是哲学很好的一个发展,但在思想史方面则很可能产生一种误解”。笔者认为,这的确点出了新儒家学说的一个重要缺陷,而正是因为有这一缺陷,其“一心开二门”的哲学“突破”在思维方式上更倾向于佛学而不是儒学,因而也就难以为道德实践确立坚实的哲学基础。
道德实践,作为社会实践的一种,从本质上说它是有“对象性”的,也就是说它是有主客体分别的。只有确信道德实践之客体的真实存在,也才会有真正的“道德心”之“诚”、“敬”,它也才不致于孤悬在精神领域而不落实在实践。大乘佛教虽主张“普渡众生”,但因其出离世间的“涅槃”目标和修为方式与社会实践毕竟隔着一层,所以程朱陆王等仍指斥其为“私”。陈来在以现象学的意象性理论诠释阳明心学的“心外无物”命题时说:“心外无物的提出……是着眼于实践意向对于‘事’的构成作用,因而心外无物本来与那种认为个体意识之外什么都不存在的思想不相干,至少对于一个儒家学者,决不可能认为父母在逻辑上后于我的意识而存在,也更不可能认为我的‘意之所在’不在父母时父母便不存在。”这一诠释的确化解了阳明心学在道德实践上可能陷入的困境。然而,牟宗三的“自由无限心”却非要开出“存在界”:“心外无事,心外亦无物。一切盖皆在吾良知明觉之感应的贯彻与涵润中。事在良知之感应的贯彻中而为合天理之事……物亦在良知之感应的涵润中而如如地成其为物……”他在此段之前谈到“事亲”的“孝行”时说:“亲之为存在物是在事亲中被带进来的。……良知是实现孝行底‘形式因’与‘动力因’,只此还不够,还需有一‘材质因’……我们注意亲之为存在物是认知地注意之,这样注意之,以为实现事亲这一孝行提供一经验的条件,即,提供一材质因,而此是附属的。在此附属层上,我们有一现象界,有一认知的活动,有一执的存有论。”“亲”之“在其自己”(物自身)是良知之涵润、创生,“亲”之成为对象是良知之“执”所“挑起或绉起”。尽管牟宗三的“良知”可理解为非个体的“绝对精神”,但在具体的道德实践中它必是“吾良知”即个体的良知。“亲”在“吾良知”中处于派生和“附属”的地位,这又怎能确立真正的孝心和孝行?
其四,“两层存有论”贬抑科学,不能促进和指导科学的发展。现代新儒家指出,在“内圣之学”的笼罩下,科学精神“毕竟为中国先哲之所缺”,而科学又为中国现代化所必需,这一观点是符合中国历史的实际并有进步意义的。但牟宗三又认为科学是“卑之无高论”,中国没有出现科学“乃是超过的不能,不是不及的不能”,这又反映了新儒家对科学的贬抑和虚骄态度。在“两层存有论”的格局中,认知主体和认知对象都属于“现象界的存有”,“外而现象,内而逻辑性,皆是识心之执之痉挛或抽搐”,科学真理是“俗谛性的真理”。在牟宗三看来,只有良知的“呈现”和“朗照”才是“真谛”,“我们的感性和知性所搅扰而扭曲的人生与宇宙不是人生与宇宙之本来面目。这是人生与宇宙之僵滞”。一方面说科学为中国现代化所必需,另一方面又如此地贬抑科学,这怎能激起中华民族向科学进军而实现现代化的热情呢?
科学需要积极地向外探索,需要不断地发现和创造新事物,并不断地改进思维范畴、认识工具。然而,这一切在“两层存有论”的格局中都有待于良知的如如呈现、创生,有待于良知的“坎陷”、“痉挛或抽搐”。如果说科学的发展是有规律、有逻辑可循的,那么良知能否有规律、有逻辑可循地不断创生新事物,并不断将其“推出去”,使其成为新的认知客体,而且相应地为主体提供新的范畴、逻辑,这是“两层存有论”没有解决的问题。
依“两层存有论”,良知的“自我坎陷”也就是良知的自觉的“自我否定”,其中“有无明之成分”,尽管是“明的无明”、“‘难得糊涂’的执”。“它一执持,即不是它自己,乃是它的明觉之光之凝滞而偏限于一边”。良知“只直接对物自身负责,不直接对现象负责”。在现代自然科学与社会人文科学日益紧密结合、自然科学亟需社会价值学说指导的今天,执持这样的“两层存有论”并不能有效地规范、指导科学技术发展的方向。现代科学技术正以其巨大的能量迅速改变着我们周围的客观世界,它决不是“权而生弊,则一念警策”就会“有而能无”的。“烦恼即菩提,菩提即烦恼”,这样的观点可能有益于佛教僧徒的修持,但无益于人们正视并改变现代科学技术已经和可能造成的弊端。牟宗三主张“德”“福”一致的“圆善论”。但由“德”而实现“福”的“自然王国”却只是“物自身层之自然,非现象层之自然”。这对于非向往彼岸世界的“俗世”大众来说是远远不够的。
三
“一心开二门”的模式引起学术界不同的思考和评价,有些学者亦着手对其进行补充。例如傅伟勋认为应把“一心开二门”扩充为“一心开多门”,即在“心真如门”和“心生灭门”之下,“至少应设纯属现实自然而价值中立的‘心性实然门’,以及暴露整个生命完全陷于昏沉埋没状态的所谓‘心性沉没门’”。“心性实然门”包括中国古代告子的“生之谓性”和西方现代的心理分析等学说,“心性沉没门”则包括基督教的“原罪”和佛教的“无明”之类。这一补充对于克服良知论者的“单元简易心态”、完善儒家心性学说的内容当然是有意义的。然而,此论一出立即遭到一方面学者的反驳:“一心开二门之二非任意的、不决定的,此乃相应于有限理性存有之直觉而设……一心开二门之超越区分乃定然不可移者。……傅先生所谓心性实然门与心性沉没门若有地位亦只能归于心生灭门下,决不能四者并列。夫一心开二门亦有其所开之之道,岂可任意开设耶!”这一反驳也确有道理,因“一心开二门”并非只限于讲儒家心性论,而是统“道德界”和“存在界”而言之,其“所开之之道”即本体界与现象界的“自然之二分”。如果承认此“二分”,那么就难免“一心开二门”的模式。
依笔者之见,中国传统哲学的主流是主张本末一源、体用胥有,是反对以本体为实、以现象为幻的“自然之二分”的。张岱年先生早在30年代初即指出此义:“中国哲人言本根与事物之别,不在实幻之谓,而在本末、源流、根枝之辨。万有众象同属实在,不惟本根为实而已。自印度哲学传入,乃渐有以实义言本根者。”儒家学说之所以没有确立知识理性的地位(新儒家所谓没有开出“学统”),没有开出近现代意义的科学,不是因其良知未能“坎陷”,而是因其误把“义理之天”、“天理”、“本心”、“良知”作为世界的本原,天地万物之“性”皆由此出;以“自然之天”(气)为本原者(如张载)亦未能免于把“太虚”作为“性之渊源”,认为“凡物莫不有是性”(《张子语录·后录下》);主张“明于天人之分”者(如荀子)却也提出“唯圣人为不求知天”,“无用之辩,不急之察,弃而不治,若夫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则日切磋而不舍也”(《荀子·天论》)。其中前两者虽有理、心与气孰为本原的对立,但在心性论上皆是泛道德论的形态;后者虽分出天人,但又把认识的对象局限在人伦之理。“道德压倒了知识”,这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也是中国传统哲学未能开出近现代科学的原因。笔者认为,实现中国传统哲学的转型,不能再以道德之“理”或“心”为世界的本原,因为这样一开始就采取了道德与知识对立从而贬抑科学的立场;如果我们有鉴于上述后两者之所以失误的历史教训,那么我们应在尊重知识、尊重科学的前提下,从中引出以物为本、分出天人的“一本多级”模式。
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即含有“一本多级”的思想因素。例如,《易传?系辞上》云:“一阴一阳之谓道”,“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也就是说此道虽鼓动、生成万物,但不具有圣人那样的道德意识:“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知”,也就是说此道本身不是善,继此而有的天地之化是善,其所成之性也是善,“仁者见之谓之仁”,“仁”并非此道初始所本有。《易传?说卦》云:“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尽管一些儒者把此“三才之道”解释为同一关系(如二程说:“至于易,只道个‘立人之道曰仁与义’……阴阳、刚柔、仁义,只是此一个道理。”见《遗书》卷一),但依文本原有的表述,它们仍有层次上的差别。尤可注意者是《易传?序卦》云:“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先有天地、万物,然后有社会及社会伦理,这是合理的自然和社会进化之序。《荀子·王制》云:“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这是更明确也更合理地把世界分成无机物、植物、动物和人类社会几个层次,“有义”即有伦理是人类社会所特有的并高出于自然界的价值所在。在宋明理学的泛道德论阻碍自然科学的发展时,明代中期的气论哲学家王廷相指出:“天地之间,一气生生,而常而变,万有不齐。故气一则理一,气万则理万。世儒专言理一而遗理万,偏矣!天有天之理,地有地之理,人有人之理,物有物之理,幽有幽之理,明有明之理,各各差别。”(《雅述》上篇)此论带有文化反省的意义,尽管当时没有得到社会的重视,但它实际上预示了中国传统哲学转型的一个正确方向(王夫之云:“人物有性,天地非有性。阴阳之相继也善,其未相继也不可谓之善。”“无其器则无其道……未有子而无父道,未有弟而无兄道,道之可有而且无者多矣。”见《周易外传?系辞上》第五、十二章,此亦有“一本多级”的因素)。
鸦片战争以后,进化论成为中国哲学的主流;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又在中国得到响应。这是中国哲学和文化实际已经经历的转型历程。进化论和唯物史观都具有强调历史发展、否定道德绝对主义的意义。中国哲学在近现代的变革始于历史观、道德观的变革,这决不是偶然的,而是被中国文化发展的主要障碍是泛道德论所决定的。30年代,张岱年先生在其“新唯物主义”的宇宙论中首次明确表述了“一本多级之论”。他说:“一本多级之论,则谓宇宙事物之演化,有若干级之不同,各级有各级之特殊规律。简言之,物为一本,而生、社会、心等为各级,生心社会不违物之规律而又自有其规律。由一本而有各级,是发展中由量转质。性质既异,故形成一新级。”他把“理”分为二:“一根本的理,或普遍的理,即在一切事物之理,此理无始无终,与宇宙同久,但亦非先于事物而有。二非根本的理,即特殊事物之理,则有此特殊事物乃有此理,无此特殊事物即无此理。如未有生物则无生物之理,未有人类则无人伦之理。”在这里,“一本多级”不仅被明确表述出来,而且基于现代的科学成果,采取了现代的哲学形式。
“物为一本”,继承和发展(扬弃)了中国传统的“始于一气”思想。这里所谓“物”是对宇宙演化的层级“析而言之”,若“统而言之”则一切“皆物”。物为实有,中国传统的“万有众象同属实在”的思想在现代哲学形式下得到了体现。
宇宙之演化“有若干级之不同”,生物和人类社会、心知在宇宙演化中相继为后起,这是被近现代科学所证明了的真理。张先生曾说:“哲学可批评科学,可考察科学之根本假设,然而在根本上哲学是不能乖乎科学的。”尽管现代的一些哲学流派避而不谈宇宙演化的层级问题,但在中国传统哲学转型的问题上,是以“一心为本”还是以物为本,却正关系到中国的新哲学是对科学采取尊重还是违背的态度问题。
以物为本,决非以物之一般的规律来解释一切,相反,因宇宙有多级,“各级有各级之特殊的规律”,所以高级事物并不能还原为初级事物。这样,科学地研究不同学科、不同领域、不同层级的问题就是完全必要的。张先生批评“旧哲学有一普遍的倾向,即认为宇宙之最基本者必即是宇宙之最精微者”,他借用戴震所谓“乃语其至,非原其本”中的“本”、“至”二词,提出“物本心至”的命题:物虽为本,但却“粗而卑”;心虽为后,但却“精而卓”。“宇宙一本一至,本与至乃是两端而非即一事。”“心出于物而可以克服物,人为境所制约而可以变化境。”“一本多级之论”充分肯定了心的精卓价值,亦充分高扬了人改变环境、追求理想的主观能动性。
张先生曾把人类界定为“自觉的有理想的生物”,又说“人即是宇宙中能有道德品值之物”。道德是人类社会所特有,亦是人类社会的高尚价值所在。“未有人类则无人伦之理”,动物在人看来虽或有互助之行为,但因其没有自觉意识,所以只是生物的本能,而非真正的道德。弗兰克纳(W..rnn)说:“道德是一种生活的社会体系,但它是能在自己的社会成员中促进理性的自我指导或自我决定的一种社会体系。”这是可以被中外学术界普遍接受的观点。把道德之“理”或“心”从世界的本原还原为人类社会的特殊之理,这是中国哲学从泛道德论的传统形态转入现代形态的一个关键。人类社会的发展是连续的和有阶段性的,因而人类的道德亦是有继承性和有发展变化的。只有如此认识,儒家道德学说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仍然适用的成分和已经落后的意识才能被合理地继承和剔除,新的道德观念与传统的道德观念也才能相衔接而融会成一个新的道德体系。
(原载《中国哲学史》1993年第3期,此次发表时作者略有修改)
“修辞立其诚”
——张岱年先生论著编年述略
衷尔钜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