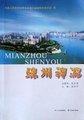—从诺奖看莫言
对话人:
朱向前:著名军旅文学批评家,中国作协军事文学委员会副主任,解放军艺术学院教授
徐艺嘉:解放军艺术学院2010级文学系研究生
时间:2012年11月20日
一、“本土化”与“西化”的平衡
徐艺嘉: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无疑是中国文学百年来获得的最高国际荣誉,也是中文文学进军世界文学的一次胜利。中国优秀的作家不计其数,但能够成功摘取世界级最高文学奖项桂冠,其创作必然要与世界成功接轨。以您对莫言作品的多年关注,再加上老同学、最早的评论者和诺奖预言者的“三重身份”①,您对此怎么看?
朱向前:我想这个问题可以从莫言2006年获福冈亚洲文化大奖谈起。这个文化奖旨在表彰“在保存与创造亚洲独特多样性文化方面”取得杰出成就的个人。授予莫言的理由是,莫言以独特的写实手法和丰富的想象力,描写了中国城市与农村的真实现状。颁奖词高度称赞莫言说,“他不仅是当代中国文学的旗手,也是亚洲和世界文学的旗手,他的作品引导亚洲文学走向未来”。借此机会,我曾组织研究生讨论了当时莫言的《生死疲劳》,在讨论会上,我有如下一段主持词,恰可阐释莫言作品如何在世界文学版图中赢得一席之地。“何谓‘旗手’?据我理解,简而言之,就是在当前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坚持本民族的、本土的、原创性的创作方向。尤其是在亚洲,在那些欠发达国家中,如何在今天美国文化铺天盖地席卷全球之际,坚持文化的个性和地域性,以保护本民族的文化生态,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并以此构成世界文化的多元共荣格局。我想莫言的‘旗手’意义正在于此。”
②徐艺嘉:也就是说,所谓“接轨”,并不意味着同一化,而恰恰是要保持自我个性?
朱向前:是的,莫言与世界文学接轨的方式恰恰是通过对抗同一化来实现的。文学和科技不一样,科技追求的是全球化,而文学想要达与世界接轨,反而要保持本土特色和作家的个性。
徐艺嘉:从那个时候起您就判定莫言作品与世界接轨了?
朱向前:还可以追溯到更早。莫言出道之初,我就认定他的小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写农村题材写得最好的小说。也因此,第一时间紧密跟踪他的作品,写下了最早的一批较为全面、系统的莫言评论文章,其中较有影响的一篇是发表于1986年12月8日《人民日报》上的《深情于他那方小小的邮票—莫言小说漫谈》,通栏标题,占了大半个版。在文章结尾我提到,我们对莫言的期待是在更大的广度和深度上超越,当然不是超越高密,不是超越华北,而是超越中国。
徐艺嘉:诚如您所说,多年来,莫言的创作带有鲜明的原创性,且各部作品之间风格差异较大。他的作品既具备浓郁的乡土特色,接中国的“地气儿”,又有国际化的特点。历数古往今来能够经得起时间淘洗、成功推向世界的伟大作品,无不是兼具民族性与世界性,所谓“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具体到莫言的作品,他是如何做到“民族性”与“世界性”的“无缝衔接”的?
朱向前: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也需要作家经验的累积。多年来,莫言在“本土”和“西化”的道路上上下求索,他在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的道路选择上,也走过了一条螺旋式的发展轨迹。在莫言创作之初,也就是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他写下了一系列堪称经典的中短篇小说,从最早的《民间音乐》、《透明的红萝卜》到《枯河》、《白狗秋千架》、《老枪》、《金发婴儿》、《球状闪电》一直到《爆炸》、《红高粱》。这段时间可说是莫言的天才和悟性发挥到极致的“爆炸”期。他表达的是最本土的故事,又融入了他自己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同时又受到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福克纳的“邮票意识”和克洛德西蒙感觉开放等外来影响,从想象方式到语言方式初步形成莫言风格。莫言在文学上是有野心和激情的,他在创作的初始阶段就立志要以故乡为依托,建立属于自己的文学王国。
徐艺嘉:我至今记得《红高粱》带给我的震撼的阅读体验。莫言营造了一个现实根本不存在的“高密东北乡”世界,奇谲空灵而又辉煌瑰丽,富于梦幻浪漫色彩,这是一般作家很难想象并难以望其项背的。这个文学场域的建构裹挟着强大气场,为这篇小说的出身与血缘奠定“豪门”基调。这部小说的语言风格粗犷豪放,想象浪漫,带有浓烈的山东高密乡土地域特色和风土人情,还多少带有一点儿野性的流氓草莽腔调。在刻画人物和场景细节时又非常细腻、鲜明、深刻,给人以生吞活剥、洞穿历史时空的激情与伟力。
朱向前:早期莫言的作品将本土意识与外来影响始终在民族传统“审美图式”的边缘进行创新与突破,若即若离,掌握分寸并拿捏到位。我对他这个阶段是高度肯定的,甚至到今天来看,我认为他写得最好的作品,仍然是《透明的红萝卜》。那种质朴、纯净和诗意,一派天籁之音,不可复制。
徐艺嘉:莫言的作品是从何时开始被推广到西方国家的呢?
朱向前:第一个重要契机应该是根据他小说改编的电影《红高粱》获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因为这部电影,西方开始关注莫言,也因此,他的作品风格出现了较大的变异,“偏西化”的特点集中体现在自《红高粱》以后到90年代中期的创作中。这期间他连续抛出了中篇小说《欢乐》、《红蝗》、《白棉花》、《父亲在民夫连里》;长篇小说《食草家族》、《十三步》、《天堂蒜薹之歌》、《酒国》(包括此后的《丰乳肥臀》)等多部作品。在我看来,莫言这个阶段的作品有点剑走偏锋,在追随西方化的道路上过犹不及。
徐艺嘉:“偏西化”的特点具体指什么?
朱向前:主要是刻意追求外在形式的西化,比如《欢乐》和《红蝗》中大段大段冗长而生硬的议论,对小说结构、意境、叙述调度和艺术感觉以及不分段落、不加标点等对西方小说修辞手法生吞活剥等各方面进行极限实验,加之感觉的泛滥和语言的膨胀,以及想象的重复,造成了作品阅读中一定的紊乱感和晦涩感,使他的创作出现了空前的偏执、躁动和疲惫。实话说我对他此间的作品阅读时从一头雾水到不忍卒读,直至丧失阅读快感。1993年,当我做《新军旅作家“三剑客”—莫言、周涛、朱苏进平行比较论纲》时,写下了一章近8000字的批评意见《莫言:“极地”上的颠覆与徘徊》。开篇即指出:“我再也不能保留我的看法了,我必须直率地说出我对近年莫言创作的批评意见:‘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成在以极端化的风格独标叛帜,败在极端化的道路上过犹不及;因此,他在创作状态巅峰的极地上和艺术风格的极限上颠覆了自己,也迷失了自己,至今陷入一种失落美学目标的躁动与徘徊之中。”①后来在莫言与我的交谈中,他委婉地对此阶段的创作作了一点解释,就是说这一批作品在国内不被看好,但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西方大国翻译不少,颇受欢迎。我理解是“求仁得仁”,他有他的预设目标,他也成功了,作为一种战略,这倒也不失为明智之举。而此阶段的创作确实对他走向西方起到了不小的作用,也对最后得诺奖功不可没。但是,即便莫言已获得诺奖,我也并不收回我当年的观点。
徐艺嘉:我感觉写小说和练武功的原理差不多,都要经历不同阶段的磨砺。初级阶段“看山是山,看水是水”,次级阶段“看山非山,看水非水”,待达到自然天成的最高境界,又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我对莫言的作品是零敲细打地读下来,涵盖面也不全。在我有限的阅读视野中,最让我惊叹的还属《红高粱》。在那以后,我记得有一次读莫言的短篇小说集《苍蝇门牙》,里面多篇小说对于大量感官体验的全方位启动以及语言中密集的审丑指向让人读久了不由产生生理上的排斥感,很有些“劈头盖脸、捣毁一切”的破坏性,包括看《酒国》,那种写法目空一切,为我们展示了小说创作的另一种可能性。他不像许多作家,有一个多年攀爬的过程,他是爆发式的,像一座火山一样,但写得有点“过”。
朱向前:好在经过漫长的徘徊与摸索过后,莫言终于找到了“本土化”和“西化”的平衡点。从《檀香刑》开始,那个传统的、亲切的、熟悉的莫言又回来了。回到了本土,回到了民族。就像莫言在《檀香刑》后记里所宣布的:“我要大踏步后退”。这是莫言在新世纪寻找中国文学发展道路所做出的一种很宝贵的调整和修正,也是他作出的中国文学要与世界文学接轨的一个极佳表率:即在最传统的形式中表达最当代的理念,以中西合璧的技巧讲述中国故事和中国经验。他晚近的《四十一炮》、《生死疲劳》、《蛙》等作品都属于这个阶段。
二、“诺奖”是如何炼成的?
徐艺嘉:谈论一个作家,归根结底要回到他的作品。文学是人学,诺奖之所以颁给莫言,是因为他的作品达到了对人性探究的深度,具有吞吐万千的气象和对人性善恶的有力剖析以及对人类生存状态的终极关怀。回到莫言作品上来,深入其作品的肌理和细部,您对他的作品有何具体看法?
朱向前:莫言的作品是恢弘的,长江大河式的,这首先表现在他作品的大体量。他的创作成果极为丰厚:11部长篇小说、100多部中短篇小说,若干部散文集、评论、演讲集和话剧、影视剧本创作,作品总量多达约800万字,文集可出到20卷。这样的丰繁而庞大显示出宏大的史诗气象。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莫言的创作涉及到多个门类,且都有佳作乃至经典,比如中篇《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球状闪电》、《爆炸》,长篇《檀香刑》、《蛙》、《生死疲劳》,短篇《枯河》、《白狗秋千架》、《冰雪美人》、《倒立》、《奇遇》,等等,都是杰作。他的散文《忘不了吃》,是我迄今见过的写饥饿写得最为传神的文章。他参与的电影《红高粱》、《太阳有耳》,分获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和银熊奖,根据小说《白狗秋千架》改编的《暖》获东京国际电影节金麒麟奖。如此大体量、高品质,并且这么全面,恐怕自有中国新文学百年以来,罕有其匹。
徐艺嘉:莫言的创作合在一起便是对20世纪中国农村风土人情、历史变迁全景式的描摹,在这一点上丝毫不逊于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等世纪级文学泰斗,这也是他独特的优势所在。莫言旺盛的文学生命力恰恰是他“天才型”作家的佐证,我曾听闻他的阅读速度极快,阅读面极广,除大量汲取中外文学的养分,他还浏览其他门类的书籍,画册中的雷电、昆虫等物都能成为他创作的灵感来源,从他的创作风格也能看出他极为强烈的倾诉欲望。
朱向前;他天然有着易于转化为文学素材的生命体验,并且他将这种体验和想象力完美融合,这就是一个优秀小说家的先决条件—有着超常的人生记忆力。莫言的书写深入扎实,而又天马行空,神幻奇谲。我阅读莫言的乡村小说,从早期的《透明的红萝卜》到中期的《丰乳肥臀》,直至晚近的《生死疲劳》等,无论是天、地、人、畜,还是乡风民俗,无论是节气更迭还是四季景观,无论是农事稼穑还是邻里纠纷,从一草一木到一花一叶,从大牲口到小青蛙,乃至一只夏日黄昏的蜻蜓停留在荷叶上眼睛转动时折射出夕阳的反光,都栩栩如生,活色生香,传神写意,纤毫毕现。浑厚多彩如油画,细致精微似工笔,直让人叹为观止。那简直就是北中国农村生活的教科书加高密东北乡的芥子园画谱。
徐艺嘉:他对一片叶子的描绘甚至都可以生动细致到几百字,这样好似用放大镜观察生活般的描写在同类写农村题材的作家中实在少见。
朱向前:有过莫言这样乡村出身和生活经历的人何止千万,成为了作家的恐怕也不下四位数,但能从笔下呈现出如此斑斓多姿的北中国农村原生态图景的却凤毛麟角。这当然关涉到一个作家才华禀赋的高下,而这才华禀赋的重要标志就是超常的人生记忆力和想象力。
徐艺嘉:您如何理解莫言作品中的普世价值和人文关怀?
朱向前:莫言的作品中塑造了上百个性格卓异的人物形象,且他始终是站在人的角度来写人,并在人物的塑造中探究人性的深度。
徐艺嘉:这点也是我阅读莫言作品比较有感触的。他不光具有大体量的作品创作,胸中还有海纳百川的大气象。莫言的文学根脉在农村,他写农村,写得惟妙惟肖,鲜活沸腾。莫言的写作是投入的,同时,他又能跳脱出来,以旁观者的姿态看农村的善恶美丑,这种客观的带有批判的、悲悯的眼光可以落在牛马猪羊身上,可以落在张三李四身上,可以落在“我爷爷”、“我奶奶”、“母亲”、“姑姑”身上,还可以落在他自己身上。他好像提前预知了人物命运的一切结局,但他就是要在他们生命蒸腾的过程中挖掘出生命的意义和人性的广度。比如《生死疲劳》,借用生前风光死后轮回托变成驴等动物之视野与行为,入木三分地刻画了人生从得意到失意,从生到死,从高高在上到做驴做马,从万恶的旧社会到剧变的新社会,生死之变迁、无奈、悲催与轮回,从狗眼看人低到驴眼观世界,大千世界人性的善良与丑恶,现实与虚幻,幸福与苦难,崇高与卑微,真实与虚伪……尽在其中。现实人生没有轮回,莫言的“轮回”不过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人生变迁的写照,在感叹造物有情亦无情的同时,真实到残忍的地步,悲悯情怀也油然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