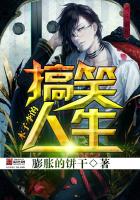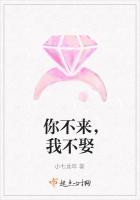班:我的确是说过“认命”。好像是在1992年台湾《儿童文学家》做我的一个“专辑人物”自述时说过的。这样的一种意思,在八十年代的中后期我也曾经有过类似的表达,大概是在1988年左右,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有一份交流通讯性质(可能就叫《通讯》)的内刊,我曾应约写过如此意思的一篇《近乎无限的幸福感》。这种意思的这两次表达,在今天我已经不会这样子来说它了。有点夸张。那是不是一个夸张的时代?自己是不是在那个时代里夸张了?但我想,当时这样子的表达,还是真实地表达出了我对找到了“儿童文学”的一种喜悦。这种人生选择我倒是至今也不会后悔。当时的大学生思潮中非常在乎一种叫做“选择”的人生哲学概念。甚至有“选择就是一切”这样的名句流传。我记不清它是不是出自萨特。因为当时大家有一种真诚的集体痛感,就是痛感错误,异常地警醒与寻找。在大学的双人床的深夜,枕头边都是书,刚刚辩论平息,黑暗中睁眼难眠,躲进小帐成一统,自认为“独醒”,认为自己寻找到了真理。这是当时的大学状态。我曾调侃写过“人人都是思想家”。我想,夸张其实是一种放大,夸张并不是虚假,只不过有点放大。我们都被放大了。
我们当时都被放大为“思想家”。我觉得我自己可能的确是有着从“思想”而特意选择了儿童文学的这种状态。不知道别人是怎样的。这带来了一个问题:我们那一代有没有“放大”了儿童文学?有没有使儿童文学“思想”了?看来应该说是有的。事实上,反过来说如果儿童文学在那时没有被我看重为那么“大”,那么可以成为“思想”利器,我大概是不会选择它的。如果我只能用一个字来回答其南兄的话,那的确就可以用一个“大”来说到我对于“小”的儿童文学所取的根本观念。可以说,我们那一代实在是中国儿童文学史上的异常加入者。按照常规,可能大多数都不会加入。
这里,我要作一个说明,就是从我个人来说其实也只不过是“重回儿童文学界”而已,因为我在读上海戏剧学院之前已经进入了《少年报》社工作。但是,的确在当时我也完全可以不选择“儿童”。我以前在年少气盛的时候显然是没有想过“假如”我没有走向儿童文学又会怎样的这个问题,但在2000年所谓跨世纪的那个时候我的确是在海边想过这个问题,结论有两个,一个自嘲的是我只能干这个,一个自信的是中国幸亏还有我和我们一批人来参与这个。后来,也想到过一些具体的“假如”,包括韦伶也曾如此假设过,那就是我假如当年毕业分配没有波折而去了上海电视台工作,那我现在可能会拍摄出了什么什么“儿童”专题片。其实还是没有脱离。我有点喜欢视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与当时毕业分配有点渊源关系。我从1995年开始使用DV摄像机,记录一些东西,也算个较早的爱好者。也有很多计划。这是说我“假如”的原因所在。但是,说得实在一点,我要走向其他别的方向已经不大可能,的确就是在于自己当时对于“中国儿童”的种种参与和设想都还根本没有完成。这件事情“不大”,谁想做?
吴:早年的戏剧学院的学习和生活对你以后的儿童文学创作和理论探讨有什么影响?
班:可能的确是有些影响。特别是以后回想起来,还觉得有那么两点对我自己的儿童专业真有一点要紧的帮助。一个是理论上的,一个是创作上的。当时对此并不很知道,后来想想才有点明白“戏剧”与“儿童”这两者之间怎么会有奇怪的联结之处,可能正是在于这两个专业都有“活动”这一个学理基础。对我的儿童美学理论上的很大影响方面,一是来自于“游戏”概念,“戏剧”竟然引发了我对于“游戏”特别地启示和关注。二是来自于“皮亚杰”的儿童发生学及其视“动作”为思维和行为之源的学说,当时泡在上海戏剧学院那个老木楼的图书馆里,不知怎么回事会使得我在那个文学时代竟然很早就开始接触和跟踪皮亚杰学说。事实上,它是非常哲学化的。其实,“游戏”和“皮亚杰”的发生论和动作学说之间,本身也是有着联系的。我说,它对我的儿童专业有点要紧的地方是在于:如果我当时只是有着“思想”,很有可能造成儿童专业之上的某种灾难——学术灾难以及儿童文学的观念灾难。我认为,对于儿童专业来说的灾难性思维就是“形而上”。我以后的“游戏精神”理论,的确同戏剧学院的知识背景有重要关联。也包括这所艺术院校的特有气质,像我们这种当时特严肃、特尔的人,浸染在那些演员朋友和导演朋友之间,时间长了也当然会感悟到生命的“生动”与“好玩”。
在上海戏剧学院的大学时代,对我创作上的影响那是肯定有的,因为事实上我们的在校课程就是不断地写作、观摩和艺术讨论。现代戏剧,其实非常地“实验性”,所以我们后来被指认为儿童文学的“探索派”,可能还是摆脱不了有这一层的精神连接。从写作的技术层面来说的话,我是非常感谢戏剧给予我的“场面”训练,这个写作训练强度很大,我认为它对于文学和艺术的表现力是很重要的基础环节(并使我有点承认某些写作能力也并非不是不可以“训练”的)。我当时的一份学业艺术总结的题目就是《场面,屹立在变迁的结构之中》。我想,另一个的确是有重要影响的地方,是来自于戏剧的“写意”这一艺术流派,实际上“写意”这种艺术形态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戏剧界就已出现并且领先于国内后来的种种超现实、魔幻现实主义以至于幻想文学等等的文学思潮,从东德的布莱希特,到前苏联的梅耶荷德和留比莫夫,到上海的黄佐临先生提出的“写意”及其中国戏曲的艺术精神,都致力于一种游走在“虚幻”与“现实”之间的切换或打破之上的迷离效果。这对我而言,在走向儿童文学所发表的第一篇小说《鱼幻》来说也就是十分顺理成章的本能反映了。
另外,有点奇怪的,也是我自己有点命运自嘲的一个表现,就是我越来越“超文本”起来,这里面是不是也跟戏剧的影响有关联,好像不承认都不行。我的确越来越看重或者着迷“现场”“身体”“活动”“行为”以及各种有关“互动”和“立体”的新媒体表现。事实上,在我近年来进入的快乐作文教学法之中就充满了这种东西。事实上,喜欢视频和DV也就是这种东西。其实,它还是来自于“游戏”的形态,可能更准确一点,但又的确是同“戏剧”的现场形态有关系。这让人觉得一个人难道事事都非得跟来源有关?那好像也太宿命了吧。
吴:能否谈谈创作与理论双栖给你带来的正面或负面的效果?
班:本来“文史哲”是不分的。可能有“文史哲”概念的人,更容易或者更为在乎地觉得需要分别用创作和理论(其实是思想和主张)来表达。我的体会,这里面的理论部分其实是一种“研究”的动力,当然也会有建树的考虑。对我来说,“儿童文学”和“儿童研究”加在一起是在做同样一件事情。有可能把它们分别去掉形式之余,而只有“儿童”这个框架之时,这个东西或者说这件活才更为“大”。坦白说,我的确很怕会有负面影响,那主要是指生怕别人(成人)怀疑你的创作,由此,我有时不得不庸俗地也要展示一下自己所获得的各种创作奖项。并且,还有一种有了就行了的想法,好像已经证明过了一样。如果要问我在这方面的观点,我认为如果你想要这么做,这就是一个绝对正面的大事,只看你如何把它做出来。这是一个更大的活。有两者参照和印证,说服力显然不一样。比如我七年多来的快乐作文实验教研活动直接同少年儿童厮混在一起,我的论说或者表达显然就会有根有据。这应该是很正面的效果。尤其是当你想做“儿童”这一块更大概念的事情之时。否则,你还不行。
吴:最近一些年为什么创作少了许多?为什么转向《六年级大逃亡》中柳老师的工作?这是你创作的延续还是一种转折?
班:我自己的走向和安排大致是这样的,一个是作为一种文学运动我们已经基本满意地完成了它,这一件活做完了,应该来做另一件活了。第二个是在中国的开放的进程中已经使得一个“中国儿童论坛”的言论践行变成一种更能影响时代进步的文化行为,而我本来就有做它的想法。再一个是我想跳过近年来的一个中国文学失魂期,不要把好东西白白丢进软弱的水中,等我们和时代一起找回中国儿童文学新的魂魄之时,我上面说到的两件活就会合起来。“儿童文学”一定要有“儿童文化”的背景,而后我想我们会向民主时代的语境和国民水准交出炉火纯青之后的新作品和新工具与新形式。其实,有不少出版社早就知道我有一系列完整成形的写作计划,而我又喜欢储存。就像你提到的《六年级大逃亡》,还有《绿人》《巫师的沉船》《幽秘之旅》这四部长篇,也都是在我做了五年的那本理论书完成之后接连出来的。做完一件活,再做一件活。
我认为,作家立世,要更为知时问世。特别是有思想的作家。作家要更能够问世。天生要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种醒世的问题。实际上这也就是人文思想主义者的“时代位置”之辩。我们当然也不想做没有思想的儿童文学作家。我的确是有一个尖锐的提问,而且,它也的确跟我近年来的做法有关系,这个问题还是提出来的好:为什么当代中国的文化精英在社会改革的五花八门的表现中却没有人前来寻求“中国儿童问题”的深度研究、批判、方案和解决之道呢?中国的思想家是不是唯独在“儿童”这个人类位置之上不能像西方的卢梭、弗洛伊德、皮亚杰等那般表现,而总归缺席?“文革”之后的思想论者和文化论者进行过多种的历史追问和文化拷问,但却始终没有主流的学者前来涉足“中国儿童文化”的领域?(就我的视野之内只知道钱理群先生对此非常的关注)还有一个具体的提问:好多年来文化界包括文学界早已对现行语文教学及其作文教学提出激烈的批评,然而,我们有没有付诸行动呢,是否应该提出认真的改造方案呢?(我也知道好像只有孙绍振先生在承担有关中学语文教改的重大项目)在两千年以来的中国文人和中国文论之中,难道找不到“儿童文化”的学术命题和认真践行吗?事实上的确是空谷回音,但却是弥足珍贵的前人足迹,以我看仅有两位人物,孤独却仍清晰地就出现在不久之前的五四时期和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周作人和陶行知。周作人可惜了,但他是中国第一位真正关注儿童文化的思想论者。陶行知的名字已说明一切,他和他那个时代曾为中国出现的各种“做”的实践运动、方案和解决之道,却恰恰是另一种“中断”的可惜。陶是中国文化史上第一个真正贴近儿童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也是第一个对“儿童问题”看得见摸得着的践行者。
这个话题我可能言多了。只为了“中国儿童问题”的中国文化语境。
然后就是我的“醒世之言”:在中国只有儿童文学作家才会最接近中国儿童心灵。
同时也是说明我近年以来在变化和寻找的儿童文学作家“时代位置”之一。
也可以说,我在2000年之前是以周作人为儿童专业榜样的。在此之后,我是以陶行知和“做”的作风以及“解决方案”的实践者为榜样的。事实上也的确有方向的明显不同,以前可算是“美学”,现在要做一点“实学”。说起来也有点好玩,那就是其南兄所提到我的那个《六年级大逃亡》长篇小说之中的柳老师,我后来倒是在现实中做起了在小说中这个柳老师想做的一系列教育改革以及小学生作文教学改革的事情,从纸上走到了现实。其实,还另有一个走出纸头的做法,就是我至今前后做了十年的快乐作文全程教学法,实际上正是在运用我的学术著作《前艺术思想》之中的“儿童操作型思维”的研究成果。这个小说是在1995年出版的,这本理论书也是在1995年完成(1996年出版)的,所以在1995年秋季我和韦伶已经创办了“快乐作文班”,而小说中的柳老师才明确提出了“操作型思维作文训练”方法。当然,作为一个作家,我也要赶紧声明:文学作品绝不全然这样。这只涉及我部分写实的小说。比如我的幻想文学作品怎么能走出纸呢?还有的“文学”是必须活在纸上那才是至高境界。
你的提问也第一次让我自己认真地想了一下这个问题:近年的变化,算是“转折”还是“延续”?我觉得可能仍然应该是一种“延续”的行为吧。
我基本上还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在生活的。我的节奏应该还是很清楚的。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期到八十年代结束,我和战友们一起投入了中国儿童文学创作和观念的探索革新运动。在九十年代初到1995年间,我们一群学术朋友差不多是赶在商业大潮全面淹没之前,做出了一批中国从来没有过的儿童文学理论及其美学理论的学术著作,我也在其中几乎是投入了五年时间而完成了《前艺术思想》的理论表达。从九十年代的中后期开始,我以论辩、理论阐述、创作和其他策划工作参与了推动“幻想文学”在中国落地的文学活动。对我的儿童文学理想来说,这件大事能够在二十世纪的“本世纪”之内得以完成,显然是一种从五四时代就被扭曲的儿童文学观念的胜利,仅以我个人就已觉得十分满意;而且,要说的全都说了,想做的也基本都做成了,可以认为“对手关系”已经消失。在2000年的12月30日到2001年的1月,我参与和策划了一个大型海滩活动,这场由二十一世纪出版社主办的“世纪之交的幻想之旅”,也被《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报》等众多媒体表达为是一场“中国儿童海滩行为实验”,它有意无意地也的确对我成为了变化的象征,大概应该是一种“超文本”的转变象征:江西的孩子和广州快乐作文班的孩子在一个大海边进行了一系列的有关文学写作、旅行、游戏、行为艺术、儿童群和心理测试的“活动”,并都是放在“中国”和“儿童”的思考框架之中。事实上,也就是从那以后开始一直到现在,我做的一些事情差不多都与此有关,其实变化的只是“舞台”。我说的“超文本”的变化意思,是说在原有文本的基础上,我们还可以从平面而走向各种立体的表达。
近几年来我主要是做了这几件事。
说明一下,我做的事情其实都是跟韦伶完全分不开的;另外,可能有一个别人不一定会意识到的家庭私人的因素,那就是我们的孩子出生在1995年,到了2000年以后便是一个标准的“儿童”,这种事情对像我们这种儿童文学作家来说就可能是一个有点重要的因素,可以说,身边的这个“儿童”也是被完全纳入和参与了工作之中的,因此这些所做的事情还的确是同整个家庭有关的。
一件事情是:完成了整套系统的快乐作文教学法和阶梯进程教案。
我认为中国儿童的“作文”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一个非常重大而有文化含量的课题。我为什么把它当作了一件大事来如此投入,是因为把它看成为一个有关中国儿童的心灵、文化背景和人文气质培养的一种“蒙学”。这件工作,非但没有脱离儿童文学,其实还应当是儿童文学工作者的历史责任和社会贡献。我们极其顶真地参与了它的改革与建构,希望能够为中国教育改革和儿童心灵问题做一点实际的“方案”建设,而不要再像我自己以前那样只会批评当代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