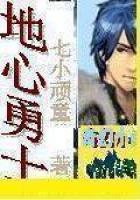覃蓁连忙道:“虽已请了大夫,但见她疼痛难忍,一时不忍便做了,奴婢不懂如何为人医病,若是做错了,请内官责罚。”心中却百折千回,淳于内官?又出现在膳房里,是方才小翠说的食医女官淳于岩么?
还未及多想,淳于内官温和道:“方才你和王真、冯临的话,我都听见了,你大约已经知道她们是掌饮食滋味温凉和分量调配的初学食医。你说你爹是大夫,你觉得她们和你爹有何分别?”
覃蓁回道:“《素问。五常政大论》说:‘病有久新,方有大小,有毒无毒,固宜常制矣。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谷肉果菜,食养尽之,无使过之,伤其正也……’所以,奴婢以为,食医和大夫相辅相成,同根同源,惟病者所需而有变。”
沉吟半晌,淳于内官缓缓道:“好了,你去忙吧。”
覃蓁“喏”一声,趋步回到了择菜的地方。小翠凑了过来,笑着道:“方才淳于岩打听你来着。淳于岩本应随驾回宫的,因为甄选宴客馆食医女官的原因才多留了一日,我看呐……许是看中了你呢……”
小红在一旁听见,接道:“你这张嘴就爱胡说。宴客馆的食医女官从来都是从初学食医中挑选,怎么会看中她?”
小翠撇嘴道:“我不就说说而已嘛……”
旁边一较年长的宫女转过头来啐道:“说说?你呀,整日就爱嚼舌根、听是非,迟早要惹火上身!”
小翠又一撇嘴,未接话,转过头对覃蓁道:“你去了这样久,方才该你倒的菜叶,我让旁人倒了,你可记着欠着我一份人情。昨晚你捏背捏得真好,晚上再帮我捏一会可好?”
覃蓁无心听她们言语,只低低道:“好的,多谢了。”心头却乱成一团,小眼睛男人的话虽让人难以置信,但他既敢说又敢做,可见所言多少有几分为真。宫女虽不是妃嫔,但未出宫前也算天子的女人,皇帝怎么可能容忍这样污浊的事情!终是忍不住低声问小翠道:“小翠,你说若是外邦宾客欺凌宫女……”
话还未说完,小翠脸色一变,打断道:“你可不许胡说!远建宫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覃蓁道:“我是说如果……”
小翠低声道:“那也不行,我自十四岁进宫,教习姑姑就着重叮嘱,宴客馆虽广延宾客,但以往从未出现过宫女被欺凌之事,以后也不会出现。你可明白是什么意思?”
覃蓁一阵静默,这言下之意显然,就是即便出现,也不许张扬。
小翠凑到覃蓁耳边,压低了声音又道:“你如果觉得不安,自己小心着就是,只是这话万万不可说出来!知道了么……”
覃蓁黯然,连向来心直口快的小翠都晦而不言,看来这事向宴客馆的管事禀报,只怕也是无用了。
过了五日,以欣赏大楚风光为名多留了几日的胡人使节终于回了大漠,宴客馆一下安静了下来。覃蓁也自然而然的回了扶梨园。甫一进屋,白芪就飞扑了过来,激动得眼眶都红了:“我听说宴客馆的一个小宫女前几日忽然染了重病,送出宫去了,偏偏又打听不着叫什么,你不知道我有多担心是你……”
她的情绪那样激动,说话都语无伦次,覃蓁不由笑了起来:“你呀,这样重的心思,小心早早白了少年头。”
白芪破涕为笑,笑嗔道:“我这心思也不过惦记你的安好罢了……你倒取笑我……这些日子在宴客馆可好吗?”
覃蓁点点头,道:“很好。”
宝春也过来了,笑道:“好就好,你不知道,自打听说宴客馆有个宫女得了重病,她就整日整日的睡不着,连带着我都不得消停。那宫女也是够倒霉的,平日里都好好的,那日傍晚去宴客馆后的松林里倒了一次泔水,回来后就大病一场,没几日就送回家乡去养病了。听说她为了进油水颇厚的宴客馆伺候,费了好一番功夫呢,没想到才领了不到半年的月例,就回了家乡……话说回来,回了家乡找个好婆家嫁了也好,总好过我们还要熬到二十五岁才能出宫……”
白芪撇嘴道:“有什么好的,病得那样重,也不知能不能医好,哪里找得到好婆家……”
覃蓁听她俩絮絮地说着,心头一惊,脱口问道:“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宝春略想了想道:“大约是五日前的傍晚吧……说是病了两日就送出宫去了……”
覃蓁大为惊恐,五日前的傍晚,那正是自己险些被小眼睛男人欺凌的傍晚!难道自己回膳房后,他们心中不快,又欺凌其他去松林的宫女了?直觉却又犹觉不可能,他们是临时起意,并非非要那么做,何况有疤男人一心不想惹是生非,有他在,也不会由着小眼睛男人胡来。
正思忖着,白芪又道:“柴纵总是找你麻烦,我还想着他让你去的地方必不是什么好地方,看来,真是我多想了……”
覃蓁闻言心头一跳,柴纵想害自己,已是再显然不过,他无缘无故的编排自己去宴客馆,必是有什么说不出的缘由,然而自己在宴客馆又确是什么也没发生……真是自己和白芪多虑了么?或是那个去松林倒泔水的小宫女其实是因着阴差阳错替己受过……柴纵安排的人将她误认作了自己……覃蓁脑中一懵,不敢再想……
是夜,覃蓁反复不能成眠,怕扰着白芪和宝春,不敢辗转,只生生地看着屋顶交错的横梁在月色的笼照下如蒙上一层朦胧的光雾,随着夜深愈加暗沉。
白芪忽然转了个身,轻声道:“睡不着么?”
覃蓁一愣,“嗯”一声,歉然道:“吵着你了?”
白芪微微一笑,道:“没有,是我自己睡不着。今日你回来,我心里高兴,怎样也睡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