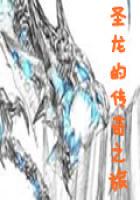看,它现在不是都来了吗?……生命的各个隐蔽的部分,都有乌云升级。狂暴的闪电不时地撕破那一堆堆蓝得发黑的东西;——它们迅速地飞驰让人睁不开眼,仿佛从四面八方包围你的心灵;然后,如醉如狂的时间到了,它们熄灭自己的亮光,从那窒息的天空突然间直扑下来。……那些达到极点的激奋的因素,平日里被自然界的那些用以维持精神平衡而使万物得以生存的规律幽禁在囚笼里,这时便突围蹦出,在你意识消灭的时候它跳出来统治你的生命,力量巨大无比,无法形容。你在痛苦之中忍受煎熬,不再渴求生命,而盼死亡给你以解脱。
而电光在突然之间闪耀了!
克利斯朵夫发出快乐的叫喊!
快乐,那如痴如狂的快乐如同一颗太阳照耀着一切现在与未来的成就。这就是创造的快乐,神圣的快乐!惟有创造才是快乐,也只有创造的生灵才可称为生灵,其它的都是一些飘浮的与生命无关的地下影子。人生的欢乐皆来自于创造:创造如一团烈火使爱情、天才、行动迸射出来。那些野心家,自私的人,一事无成的浪子在那巨大的火焰旁边没有地位,但他们也想从中借一点儿黯淡的光取暖。
创造可以消灭死亡。只要是创造,不论是肉体方面,还是精神方面都是从躯壳的樊笼中脱离,是卷入生命的旋风,应与神明共存!
不能生产创造的人是可怜的,在这个世界上流离失所是孤苦无依的,那枯萎憔悴的肉体和黑暗的内心,不能冒出一朵生命的火花!更为可怜的是这些自知不能生产的灵魂,社会尽管给他光荣和幸福,却不能如开满鲜花的大树一样满载着生命和爱情,他所拥有的不过是一具腐尸罢了。
克利斯朵夫感到一阵电流从他身上流过,他发抖了,因为光明照耀着他。那情形好像陆地突然出现在黑暗的大海上,也好像有一双深邃的眼睛从人群中瞪了他一下。这种情形,总是在他经过几个小时的发呆、意气消沉之后发生,或者发生在他想别的事或是谈话、散步的时候。如果说这时候他走在街上他会因为顾虑而不敢用高歌表现他的快乐,那么在家里他可是毫无禁忌的。他会哼着一支欢呼胜利的调子,直着嗓子伴着他的手舞足蹈。母亲听久了这种音乐,也仿佛明白了它的含义。她向克利斯朵夫宣称,他的歌声如同一只下了蛋的母鸡。
他被音乐思想渗透了,那种思想有时是单独而完整的一句,更多的时候是包裹着整部作品的一片星云:一个幕上映现出全部的曲子结构和大体轮廓;那华光四射的句子在阴暗中灿然显露,如雕像一般分明地呈现在幕上。而它们又如同一道闪电;有时是连续而至的几道闪电,每道光明都在黑暗中开辟出一块崭新的天地。往往这奇妙的力量只是捉摸不定地露一会儿面,便马上在天隅的云层里躲起来,只留下一道光明的痕迹。
克利斯朵夫一心体味灵感带给他的乐趣,于是抛弃了其余的一切。凡是有经验的艺术家都知道灵感的可贵,只有靠智力才能完成由直觉感应的作品;所以他尽量搜索自己的思维,他要献出其中所有的神圣的浆汁,——而且还常常加清水进去。——可是克利斯朵夫年纪很轻,他不自信了,他怀有那不能实现的梦想,轻视那些繁琐的手段,他只愿要那从头到尾,自然而然地流出来的作品。如果不是他此时正处于自己精神上最富有的时代,不容许任何虚无的进入,那么他也不会有心不管现实,而听凭这荒谬的计划诞生。
因为有了这源源不断的灵感,他耳中听到的,眼中看到的,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的,无论什么都会成为引子;而那一瞥一视,只言片语都成为触发梦境的因素。他那广漠无边的思维天空里缀满奇异的星星。——但仅管在此时,瞬间消失的可能也是存在的。虽然他也清楚那黑夜不会久长,思想的缄默不会拖延到他无法忍受的地步,但他还是有些担心这莫名的力量变幻不定;一会儿找他,一会儿又离开他,一会儿回来,一会儿消失……他不知道消失的时间会有多长,也不知道恢复的可能性有多大。——他天性高傲,所以他不愿去想受挫的事,他深信:我是这力量本身。一旦它消失,我自己也便不存在了,我就去自杀。——他在这种无法克制的心惊胆战中反而找到了快感。
克利斯朵夫明白单纯靠灵感永远不能成就一部完整的作品,虽然现在灵感没有枯竭的危险。思想总是以粗糙杂乱的面目出现,必须付出努力把它去粗取精,而且加上它的时断时续、时起时落;我们要使它连贯起来,没有深思熟虑的智慧和沉稳的意志是不行的,也只有通过此种锤炼,才能创造一个新的生命。既然是天生的艺术家,当然不会忽视这一步;只不过他不想承认他在表达自己心中的模型时,为明白通畅起见,早已把内心意境多少作了改动,却硬要坚持那还是灵感的本来面目。——甚至有时他把那种思想的含义理解得面目全非。因为那乐思来得迅速,他无法说出那确切的意义所在。乐思闯入心灵不知名处时,意识无力辨认它,它作为一种纯粹的力是超出了自然规律、延伸到意识领域之外的。克利斯朵夫骚动着,努力集中注意力挖掘那到底是什么,那是一种可以肯定却无法辨清而又独一无二的一种感情,是欢乐还是痛苦不得而知,因为它超出人的智力与一些不可理解的热情掺杂在一起。可是它又与人类头脑中存在的逻辑结构有所联系,所以人的智力终究要给这力起个名字,不管你了解还是不了解。
所以,克利斯朵夫相信——他强迫自己相信——在他内心深处萌动的那模糊的力确有一个明确的意义,与他的意志相符的意义。那些从深邃的潜意识中跳出的灵感是自由的,但由于受了理智的压迫,它被逼与那虽明晰清朗但实际上与它毫无瓜葛的思想联系合作。到了这种地步,作品只成为两种东西的勉强组合,一种是在克利斯朵夫心中拟定的伟大题材,另一种则是连克利斯朵夫也很感迷茫的不知意义所在的粗犷的力。
他忍受着矛盾挣扎,受着在胸中互相撞击的力的鼓动,低着头摸索前进。他一方面感到心满意足,欣喜异常,因为在支离破碎的作品中掺进了一股阴晦而强烈的生命,那不是他的意识可以表现的。
自从有了这崭新的力量,他开始敢于正视周遭的一切,包括那些别人教他崇拜的和他不假思索而盲目尊敬的一切;而且他开始毫无顾忌地批判。他撕破那层隔看幕,看透了德国人的虚伪。
其实虚伪存在于一切的民族与一切的艺术之中,人类的精神中有大半的谎言与极少数的真理。人类有不可承受之重的脆弱的精神;这种精神让那些所谓的宗教、道德、政治、诗人和作家们在纯粹的真理之外包裹一层谎言。这些谎言因民族而异,它是分别适应于各个民族的。各民族之间之所以有互相了解的困难和彼此轻视的倾向,都因谎言在捣乱,而真理对于大家来说却是一样的。每个民族把适合本民族的谎言称为理想,让她的人民从生到死在这谎言中呼吸生活;只有少数的天才伟人历经勇敢的斗争,经过一段自由的思想在那个时期被孤立的过程,才最终摆脱了那谎言。
正是这样一个极普通的机会,克利斯朵夫发现了德国艺术的谎言。原来的浑然不觉不是因为没有机会而是因为他身在庐山之中不识其真面目而已。如今他退步出山,于是山的面目呈现出来,他可以远观了。
在某次市立音乐厅的音乐会里,克利斯朵夫发现从未有过的恐惧。大约有二三百张咖啡桌成十几行摆在大厅里,舞台被设在厅的尽里头,克利斯朵夫细看周围的观众:那些穿着又紧又窄的深色长外套的军官,阔大的红脸上,胡子剃得精光,显得正经而又俗气;高谈阔论的妇人装得过分洒脱;女孩子们装作天真的样子呲牙咧嘴地笑着;那些戴着眼镜的胖男人,胡髭满面,活像眼睛滚圆的蜘蛛。他们态度虔诚而恭敬地每喝一杯酒便起身向别人祝健康,那脸色和声调是做作的:如同一边念着弥撒祭祀的经文,一边又扮着严肃发笑的神态敬酒。虽然大家把说话和饮食的声音尽量压低,但音乐还是在谈话声和杯盘声中消失了。有个驼背的高个人在指挥,胡须如同尾巴一样挂在下巴上,眼镜架在往下弯的长鼻子上,神气颇像一个语言学家。——克利斯朵夫早已熟悉了这些典型的人物。不同的是,当他用嘲弄的眼光看他们时,他们变得异常可笑。是的,有些时候在平日里无法发觉的别人的可笑会毫无缘故地进入我们的视野。
这次音乐会演奏《哀格蒙特序曲》(贝多芬作品),瓦尔德退菲尔的《圆舞曲》、《汤豪塞巡礼罗马》(瓦格纳歌剧《汤豪塞》中的一段),尼古拉的《风流妇人》、《阿塔利亚进行曲》(门德尔松所作的),《北斗星》、《幻想曲》(梅亚贝尔所作的普歌剧)。贝多芬的《序曲》奏得循规蹈矩,《圆舞曲》奏得慷慨激昂。演到《汤豪塞巡礼罗马》的时候,台下有开拔瓶塞的声音。克利斯朵夫的邻桌坐着一个胖子,他很可笑地挤眉弄眼地按着《风流妇人》的节拍做福斯塔夫(福斯塔夫为《风流妇人》中的男主角,是个蠢得可笑的角色。)的姿势。
一位又老又胖穿着天蓝衣衫的妇人,她束着一条白带子,她有着粗大的腰围,皮肤是鲜红色,鼻梁上架着金丝边眼镜,她用洪亮的嗓子唱着舒曼和勃拉姆斯的歌。她的表情没有一点儿庄重老成,简直就是咖啡店的歌女。你看她扬着眉毛,使着媚眼,眯着眼皮,左右摇晃地做着哑剧,她满月一样的脸上笑容也极肥大。这位可能已儿女满堂的妈妈,穷形尽相地要扮演痴情女子,再现青春,表现热情;同时她哼着的舒曼的歌儿也像是催眠曲。大家听得居然入了迷,但是一等南德的合唱班出台,听众马上转为庄严的神态。合唱班一会儿咿咿唔唔,一会又大吼大叫,一共唱了几支有情趣的歌。四十个人的声音似乎处理成四个人的,他们也许是故意掩盖了合唱风格,结果只剩下旋律孤零零地响着,表面看似极尽细腻,声音轻时像咽气,响的时候又像打雷;结果是既不浑厚,又不平衡,简直是萎靡不振,使人忍不住想起波顿的话:
“现在我来装狮子,我的吼叫可以与嘴里衔着东西的白鸽的声音媲美,也让你怀疑是夜莺的歌唱。”
克利斯朵夫听着,从一开始就感到很反常。这个音乐会,这个乐队,这些听众,他都是熟悉的。但是他一时之间就读出了其中的虚伪,包括他曾喜欢的《哀格蒙特序曲》在内,那种虚张声势的动作,一叹三咏的慷慨陈辞,突然显得没有了一点儿真义。毫无疑问,他听到的已不再是贝多芬和舒曼,而是那些伟大音乐家的可笑的代言人,而是嘴里嚼着东西的观众用他们的愚蠢像一团浓雾般包裹起来的作品。——不仅如此,连最美的作品中间也有克利斯朵夫从来没有感觉到的令人不安分的因子。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不敢深入寻找答案,以为那样会玷污那些心爱的大师。他不能看下去,可是因为有了开始,不由自主地要继续看下去,而那偷看的方式变成了如彼萨的含羞草一样从指缝里偷看。
他看到德国赤裸裸的艺术,万态尽现:有伟大有无聊。这些艺术家们不仅絮絮叨叨而且自以为是,暴露了他们的内心。其中蓄满丰富的感情和高尚的胸怀,那真情四处蔓延,把心也融化了;日耳曼民族那多情的浪汹涌着冲破了堤岸,即使最坚强的灵魂也变得脆弱,原来懦弱的则早被淹没在灰色水浪之下——这成了肆虐的洪水;德国人的思想在水下酣眠。如门德尔松、勃拉姆斯、舒曼等等写浮夸伤感音乐的小作家,有些什么样的思想!没有一块挺立的岩石,完全是一片湿漉漉不成形的黏土……真是荒唐幼稚至极。克利斯朵夫无法相信听众感受不到。但他向四周扫视了一遍,却发现人们似乎怡然自得地沉浸在美妙的音乐中。那么他们所听到的一定是有趣的了?克利斯朵夫不敢妄加评论,他知道这些人对台上那些如雷贯耳的名字崇拜得要命,并且他们什么东西都尊敬,不管是音乐节目,还是酒杯,亦或是他们自己,他们都一视同仁地尊敬。总之跟他有关系的一切都“妙不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