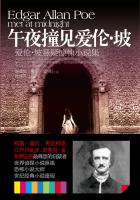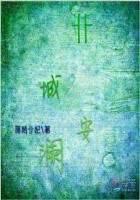天空辽阔、明净而又深邃,一队队南飞的大雁嘎啊嘎啊地叫着,用它们的身姿在蓝色的天幕上排列出了一个个大写的人字。空气、干爽而寒冷,大地上到处都是一种萧瑟、枯槁的景象,仿佛一切温暖和生机都让那些大雁往什么地方带走了。在这样的日子里,梨花湾十三队正在召开年底分红大会。
面南而座的三间屋檐参差、门窗破旧的队部房子的门口,成一字形摆着三张从未上过油漆的灰不溜秋的办公桌,桌面上堆着一摞摞账本。杜石朴坐在西边那张桌子跟前,披着一件白板儿朝外而里面又绒毛无几的山羊皮袄。他的络腮胡子长了足有一寸多长,也没舍得用手抓一抓,乱七八糟的。眼窝深深地陷了下去,两只浑浊的眼睛仿佛掉进了山崖之下,很费劲地瞅着远方那黄茫茫的原野。
会计买胜和保管郝云依次坐在杜队长东边的桌子跟前,两人正一唱一合、声嘶力竭地向大家公布着账目。他们对面的围墙不再囫囵的院子里,是来听会的社员,每个人的坐姿都是那么富有十三队色彩,有的坐在当年从老庄子地锯来的不成什么材料的梨树的枝干上,有的坐在带有根须的梨树墩子上,还有的坐在或单块而立或几块横摞起来的坷垃上,至于蹲在半截坷垃墙下面的那些社员,个个都坐在自己的脚后跟上。
几位生产队的当家人,只管堂而皇之地公布账目,社员群众似乎早就知道毫无什么指望,不得不干自己的事情。姑娘们,有的绣花,有的学针织,有的望着飞向远方的大雁想着酸滋辣味的事;婆姨们,有的用筷子绕麻绳,有的纳鞋底,有的揪着奶头给怀里的孩子喂奶;小伙子们,有的两人一组用坷垃蛋儿下方,有的合起伙来用柴棍子捉鳖,还有的在交头接耳地谈女人说粗话。
一些杂七杂八的收支账目正公布得活泼,只见四位骑自行车的人,一溜烟地来到了会场附近。当慌慌忙忙找个空闲地方把各自的车子放好之后,一起向那三张灰不溜秋的办公桌跟前走去。没错,会场里的一些社员,已经将他们辨认出来——走在前面的两位,是县农机厂的副厂长和出纳;后面的两位则,是县农业银行和公社信用社的干部。
看到他们,杜石朴惨白的脸上顿时泛起了几疙瘩羞臊的红晕,像拔丝那样艰难地离开桌子跟前的凳子,步履蹒跚地向前走了几步,然后用特别内疚的目光和粗糙得螫人的手,迎接着他们的到来。为了不影响会议,他把几位来人,统统带到了离会场不远处的一个僻静些地方。这里非但听不清会场的声音,还能遮住众人的目光。他的脚步刚刚站稳,四位来人赶忙从不同方向把他围住了。
正面的农机厂的副厂长首先开了腔:“老杜啊,今年那款你总该还了吧?”
“我本来也是那么想的。”他苦笑着,抠抠有点不对劲儿的胡子。
左面的农机厂的出纳,看着杜石朴那副好像佯装可怜的模样,忿忿地数落道:“当初给队里赊手扶拖拉机的时候,你说得天花乱坠、碗大汤宽,我们的合同上也分明写的是,前年年底还款。结果你又推到了去年,去年又推到了今年。你把我们害得好苦啊,上面每次派人下来查账,我们都要遭一通指责。”
“我也是格外过意不去啊。”他搓着脖子,红头胀脸地支吾着。
右边的公社信用社的干部,总算抢过了话头:“石朴啊,这可是前年、去年和今年,三个年头的有息贷款哪。你说好的今年决算过后可以还掉大半,要给自己说过的话做主啊。实在不想还,你掂量着办。这有息贷款,可是带屁眼儿的货,到时候垒个大头疙瘩,看你怎么办?”
“总想着集体的光阴,定然会大步朝前发展,谁知又是一场空喜欢。”他摊开两只手,做出了一个无可奈何的样子。
站在他身后的县农业银行的干部,发现这种场面纯粹成了敢于抢先者的天下,总怕误了自己的紧迫任务,连忙拉着杜石朴的皮袄大襟,致使他转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半圆,当面朝着自己的时候,他苦诉道:“杜队长,这笔贷款已经八年了,你听清了吧,已经八年了呀。买的牲口,都被你们使得老的老,乏的乏,死的死;购来的大胶轮车,也被你们使得差胳膊少腿了。根据国家有关规定,贷款的利息就不再麻烦你们还了,可这本钱今年你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放空哪。”
“唉,唉。今年的收入又是不争气。还得请,还得请各位领导,多多宽容宽容。”杜石朴的脸色变得铁一样青,脖子里和额角的血管憋得直打滚。
就在这几个人还想给杜队长说什么逼楔子之话的时候,忽听那边公布账目的买胜高声说:“大家都注意了,大家都注意了,下面开始公布我们队的分红情况!经队委会研究,并呈报大队和公社批准,今年我们十三队的每个劳动日,也就是每十个工分,分红为一毛三分钱。
“与其他生产队横向比较起来,也还低得可怜,但与本队去年的分红情况作纵向比较,又增加了三分钱,也算是又往前迈了一小步。鉴于这种情况,全队所有的家户,都还得给生产队倒找款。下面我就开始一家一户的公布,大家要注意听,如果有什么问题,就当面提出来,我们也好及时给以答复。”
会计买胜的话,给杜石朴帮了大忙、解了重围,几个要款的人,刚才还是水生生的绿高粱,此刻竟然一起变成了晒蔫的大头红萝卜。是啊,俗话说:“挨乡三分土。”他们也常和农村人打交道,每个劳动日只有可怜巴巴的那么一点收入,与其说是来要欠款的,还不如说是来要命的。
若设身处地地想一想,他们几个人,无论哪个人每月的工资虽说不算多,可也能拿到四五十、六七十元,而生产队里的每个全劳,每天平均才能挣八分工,也就是说,每天的收入只有一毛零几厘钱,一月的收入是三块钱,一年的收入是三十几块钱。
这样算下来,他们每人一个月的工资收入,就是这个生产队一个全劳的几乎是两年的收入;一年一个人的工资收入,就是这个生产队一个全劳的二十四年的收入。这可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的确,如果不是身临其境,他们绝不会相信,就在与自己共同生息的这片土地上,竟然还有收入如此可怜的民众。
难怪,人们都千方百计地想入城市户,想做有工作的人,想逃出农村这个穷坑或苦海。尽管他们几位的心情,都为这个生产队的微薄收入与生产队长的尴尬处境特别沉重,但为了回去能给上级交差,他们依然用特别沮丧而又满含期待的目光瞅着灰头土脸的杜队长,盼他能说出一句保证什么时候能还上款的话。
杜石朴一副尴尬相,两只手在两边的胯眼处不知所措地摩擦着:“说句你们都见笑的话哩,队上那头青骡子,有病好长时间了,都没钱治。昨天我身上装着刚刚借来的给我老婆抓药的五块钱,见骡子性命有危险,就连忙给了饲养员,才算看了一回。现在,还等着社员们的倒找款呢。”
他们实在听够了他的这种诉苦,个个唉声叹气一番之后,一起推着自行车离开了会场。打算合起伙来,共同去找这个生产队的上级,或更上一级的领导,看他们还有无什么补救措施。此时,杜石朴的两条裤筒里,好像统统装满了沙子,两只脚腕处,也好像被什么人铐上了沉重的脚镣,好大工夫才挪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尽管脸上的神情依然向着远方,眼睛却恍恍惚惚啥也看不分明。
买胜的高嗓门就在耳边回荡,好像啥也听不进去,惟有一种呜呜的声音在耳朵里肆无忌惮地搅扰着,像是夜里狂风吹电线时候制造出的那种悲鸣,又像有一伙什么人正蜷头缩脖子地坐在他的耳朵里大吵大闹。这种情景,让他又想到了刚才那几个来要账的人,莫非他们并没有因为自己的无可奈何而走远,却运用类似孙悟空那般的变形办法,深入到了自己的耳朵里边,正准备合起伙来,向他的脑袋发动什么新的攻势呢。
“下面公布金氏家的账目!”买胜的这句话,不知怎么一下子钻进了杜石朴的耳朵,让他顿时变得敏感起来。如果说,在方才那些讨债人面前,他是个可怜巴巴的乞丐的话,那么这阵,他好像猛然间转换成了方才那几位逼债人的角色,安闲地坐在凳子上,正等待着什么人交纳一笔欠款上来。
那次,虽说从梨园小屋撂出了海文的杂七杂八,又卡着对方放弃了贩梨的买卖,返回到大田里参加劳动,可他心里的气,远远没有发泄出去。总感到,对方是溜进自己所牧放的羊群里的一只恶狼,非但不听从他这位主人的任何口令,不服从他的驱赶,还时不时地想通过惊扰羊群的花招,达到袭击主人的目的。
就在这种时候,他又为自己曾做错的一件事情而懊悔不已。那年海文刚刚考上县城一中的时候,自己到学校里往回要他,由于话说得不太强硬,才没能撤回来,致使对方又念了许多年书,害人的本事一天天强大起来。的确,那些领导和老师再厉害,好汉还怕赖汉呢。既然说得那么轻巧,为啥没把姓海的一家人全都养活上?说穿了,是自己把一只赖狗放出去变成了恶狼。
他甚至也还格外荒唐地想,海文为啥早不出生十头八年呢?若是那样,即使有一肚子两胸膛文化,也是个绵贴货。仅以那些年下放到这个生产队里来的知青为例,哪个不是中学生,哪个笔头子不比他利索?有些甚至还有强硬的后台。刚来到农村的那阵,一个个全像疯儿马和骚骒马,根本不把他这个队长放在眼里,经过一段时间繁重体力劳动的消损,还不都变成了乏绵羊。若由着他们的性子来,生产队非改变颜色不可!
孙悟空那么能行,为啥到了唐僧手里就得乖乖顺顺绵绵贴贴,是由紧箍咒管着。人没笼头拿纸拴、拿法敉,说到底,是那些年他能轻而易举地抓他们的阶级斗争。那时候,各种各样的政治性很强的大帽子,似乎就在他的袖筒里藏着,衣裳口袋里装着,他想给谁戴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的。想批斗谁,就可以随意召开社员大会批斗,即使动手动脚地惩罚几下,也没什么不可以,就像武术老师想把他们的弟子调教得更听话、更有本事一样。
思来想去,是这世道不再抬举他了。把做人的政策愈放愈宽,致使海文像个精光光、滑溜溜的泥鳅,叫他怎么也抓握不住。这样下去,就会把那个小伙彻底毁了,也还给整个生产队留下不少坏影响。但总不能眼看着他往那条危险路上走吧,俗话说:“马烈有骑马的方子,牛大有剥牛的法子,”刚从学校回来的时候,若不把他制服,往后还要上咱的脸、猴咱的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