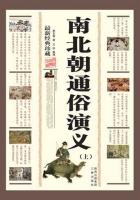马存惠刚从河西做罢买卖回来,就听到了海文被队长撵出梨园的消息,这让他比自家人受到了欺侮还心痛。他对儿子马贵说,海中山在世的时候,和我就像一娘同胞的弟兄。几乎整个梨花湾都公认的一个憨厚老实人,却让杜石朴逼走了。现在这家伙又欺侮到了海文的头上。咱爷俩去把他好好地教训一通,若是他不承认做得欠妥,就绝不能轻饶。
“教训一个杜石朴,何必兴师动众,我一个人足够。”马贵知道,杜石朴会几手杜家拳,但爹也谙熟马家拳,稍不注意就会捅出大乱子,连忙把这件事大包大揽下来。他想,别说杜石朴本就做得无理,仅凭自己灵活的脑筋和善于狡辩的嘴巴,也让对方难以应付。爹刚从监狱提前释放出来,万一闯下什么大乱子,最容易被别人旧事重提,乃至数罪并罚。
“靠你嘴头子上的功夫,剜算对方几句还凑合。想和人家来硬的,那我还要随在后边收尸呢。”马存惠被本事不大,但说话却格外强硬的儿子惹得冷笑了两声。但就心底的真实感受来讲,马贵的话又一次让他想到了被招到东山深处当女婿的马华。是啊,惟有那样的儿子,做事才会让老子特别放心。
“他胆敢动武,我就来邪门歪道。”
“暗中算计人,不是男子汉的作派。”
“对那种人,还讲这些?”
“但也要想到,你是哪家的后代。”
“反正,你是万万不能出面,刚从监狱出来,小心再吃冷亏。”
马贵最后的这句话,让他想起了往事。六十年代经济困难时期,伺候有病的父亲过世以后,为了生计,他带着全家人走南闯北,当过伐木工,开过运煤的小型拖拉机,牧过马,割过草,也跑过买卖。出远门的时候,为了筹集费用,把家里所有的东西都处理得一件不剩了,跑来颠去腰里没啥底垫,加之人多嘴稠开销大,最终还是被逼回了老家。
“兔儿满山跑,终究归老窝。”他的经历不但完全印证了这句俗话,也让他想起了临走之时,庄里一些老辈人的谆谆告诫:万一混得不好,就会外边的荒了,家里的也误了。可不,妻子吴秀梅和三个娃,非但在外边受尽了折磨,回到庄里竟然连吃住都成了问题。多亏海中山,既借给了房子,还送了半窖糖萝卜,才让他们一家人有了生活下去的可能。
他早先就天资聪颖,不论读书还是念经成绩都名列前茅,这回又闯过大世面,并且喜爱读书、看报和收听广播,世界各国的地理风貌、人情世事知道得不少,就连有名的中外经典小说和历史故事,甚至包括一些理论方面的书籍,也能说得头头是道。平常有个雪飘雨湿不能出工,人们都愿意听他诵经赞主,讲三国论五朝,说亚洲道世界。
梨花湾的清真寺被当作“四旧”拆除之后,几个阿訇也被整得不敢随意走动了。每当开斋节、古尔邦节或圣纪节,一些穆斯林只有到他家里来做礼拜。平时,谁家悼念亡人或举办婚丧大事,也要请他到家里主事诵经。他的所作所为,早就被一些人记在心里,只盼有个什么机会就开始下手。
没过多久,说是为了什么破旧立新易风易俗,韩维民伙同上面有些人,决定让生产队长杜石朴带头,把十三队作为本民族人养哼哼的试点。为了能顺利开展这项工作,提出让马存惠这个宗教界人士的后裔,动员当地所有的穆斯林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一起投身到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去。
“侮辱比杀戮更恶劣!”在杜石朴召集并主持的社员大会上,马存惠义正辞严地呼吁大家,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这种侮辱人格、祖先和本民族尊严的无理要求。结果人家既无视他和众人的反对,还让杜石朴代表上级宣布了具体的奖惩措施,继而又让几个陌生人哄赶着一群哼哼,准备强行按户摊养。
看到人家纯粹不顾大家的反对,马存惠便率领庄上的男女老少,手持木棒打跑了所有的恶人与脏物。杜石朴万万没料到,这些人如此胆大包天目无领导,一口气跑到公社,赶忙向主管此事的革委会副主任龙仁和汇报和请示,对方向他耳语过一阵之后,他便像是得到了皇上的密旨,大步流星地来到公社门口的体育场,以生产队当家人的身份,声称自己队里出现了阶级斗争新情况,经龙仁和副主任同意,要将正在搞军事训练的这个群团组织里的成员,火速带往十三队。
实话说,他没有胆量完全按照龙仁和副主任的意思办,只是想借助这些人的气势,吓唬一下那些不听话的社员,为了怕出事,还特意让他们下掉了子弹与刺刀,并一再强调只能当作演习。他想,哪个社员再厉害,还能不怯枪、不怕死?而十三队的群众却以为,自己已被对方当成了敌人,愈发不肯示弱,操起猎枪、铁叉、斧头和菜刀搞起了自卫。
发现局面已经失控,杜石朴着急得真不知怎样办才好,连忙指派海文的父亲海中山,想办法托劝和制止两边情绪过激的人员。没想到,处在风口浪尖上的海中山,不一会儿便倒在了这场混战之中,最终也没搞清是谁将他置于了死地。而受伤被俘的马存惠,被当作反动头领关押了起来。由于和之前的一些所谓严重政治错误的事情联系起来,最终被判刑入狱。那时,他总以为,今生今世自己定会无常在南湖劳改农场,可没想到,去年国家落实政策,竟能减刑出狱。
这个生产队本就是全县有名的老大难,一个劳动日只有一两毛钱的收入。他坐大狱的事情,不只给家里人加重了精神负担,也愈发捆住了挣巴光阴的手脚,只有灰不溜秋在队里死受穷。小儿子马华已过了而立之年还没成家,只好给山里人做了倒插门的女婿。大儿子马贵,至今还是光棍一条。他当然明白儿子话里的意思,却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刚放出来,爹也不怕,总不能眼看着那个没靠山的娃,让别人随意欺负吧?”
“要我看,先把海文找来问清楚情况之后,再做考虑。如果他想让咱们给他出这口气,再去也不迟,不要费力不讨好。再说,万一把矛盾激化了,两家人都将不得安宁。”其实,马贵根本不愿为海文去冒那种风险,却把话说得特别在理与中听。再说,他也知道,海文那个高中生,也绝不会同意他们硬拼蛮干。
发现马贵是这样一种态度,马存惠吩咐他赶快去找海文,而自己却思索着下一步的路到底该怎么走。其实,自从海文接管梨园以来,他总是放心不下。是啊,谁都知道,这些年来,那梨园是一本糊涂帐,而海文又生性过于耿直。他已预感到,那样的安排,随时都有产生矛盾的可能。于是,之前就曾给儿子悄悄吩咐,一定要给海文当后盾。若有为难,他也可以亲自出面。
事情果然不出所料,听到海文受气的消息之后,他后悔自己对那小伙关照得太少。对方是有梨园缠着,不好出来走动,而自己呢,虽说腿脚也还灵便,可总怕到那种地方,别人会说闲话。正在这么自我谴责的时候,发现海文已走进了自己家的院子,他连忙上前揭起门帘,把海文让进了屋。
好久没到大伯家来了,觉得一切都是那么新鲜和亲切,他不由自主地打量着屋里的一切,虽说是土墙、土地和土炕,却显得一点儿也不土气。对门的北墙根,摆着一尊绿底黄方块图案的老式三仓儿大木柜。柜中间立着一面长方镜,两侧是一对锃亮的紫铜香炉,再往外是一对几尺高的古式花瓶,瓶后边还摞着几本厚厚的经书。
西墙上挂着经文中堂,肃穆而有气势。南墙边靠炕的窗台上,放着几本古典小说和一台又小又旧的半导体收音机。东墙挨里屋门的地方,挂着两张不太大的地图,一张是中国的,一张是世界的。一切,似乎都在介绍着这个家庭主人的追求与爱好。
海文见马存惠大伯盘腿坐在炕上,也将自己的腿收起来坐在炕边。炕中间是一张洁净的炕桌,就在打量这张炕桌木质的时候,海文眼睛的余光却发现,马贵的身影在窗玻璃的外边晃动了一下,接着就不见了踪影。那种肩扛铁锹的架势,似乎在向他爹打着招呼,自己已经上工去了。也就在这时,随着门帘落下时候的一声脆响,只见麦尔燕双手端着一个盛着茶盅与茶壶的大磁盘,细步纤纤地走进了屋。
她的眉毛就像两小缕躺着的嫩嫩的夜色,脸蛋原本生得白净,又淡淡地涂上了一层粉,给人一种青涩而含蓄的感觉。上身穿一件蓝底碎白花的大襟纽疙瘩紧身衣,腰束得格外纤细和攒劲,胸脯鼓出两个明显的小包包来,下着一条浅绿色的颤颤抖抖的裤子,叫人总以为她是飘着进来的。
“阿丹哥,你最近可好啊?”
“还好,你们一家人都好吧。”
“都好,你怎么不接着念书了?”
“成绩不太理想,再说高考录取比例太低。”
“像你这样的人,不去念书实在有些可惜。”
恭敬而又小心翼翼地问候与回话之后,麦尔燕在父亲和海文面前的桌上各放了一个茶盅,继而又一一揭起盅盖,举起铜壶斟满了茶水。在做这一系列动作的时候,总是娇憨地抿鼓着小巧的嘴唇,让人觉得她很羞涩、很矜持,一对湿漉漉而又毛茸茸的眼睛,却不时地和海文淘着气。
旋即,盅子里的茶叶、红枣、果干、沙枣、核桃仁、桂圆全都漂浮起来。马存惠一番礼让后,二人一起端起了茶盅,继而都拿着盅盖,划拉着茶水上漂浮的五彩缤纷而又飘溢着质朴香味的各类干果。此时,麦尔燕才彬彬有礼地退出了屋。
麦尔燕已经走了,可海文总觉得她还在眼前,尤其是那股淡淡的粉香味儿,总会在他的鼻翼附近缭绕。他能感觉出来,与以往相比,她似乎从未这样生动,也从未如此富有魅力,就像是另一个人似的。他想不明白其中的缘故,一切就像递来的这盅盖碗茶,这般多色彩、多悬念、多主题。
“阿丹,我已听说了你被撵出梨园的事,要想开些。”
“多谢大伯的挂念,实话说,我看得还比较开。”
“这样就好,本来我还想替你出这口气呢。”
“没那种必要,完全可以自己承担。”
为了不让大伯为自己操心,谈话之中海文又详细谈了他的想法。虽说,自己的行李是被杜石朴从梨园小屋扔了出来,可是由于没让集体财产受到一丁点儿损失,他的情绪,并没有局外人想象的那样低落。现在,他考虑最多的,倒是那次没能进行到底的梨园聚会。
对于庄户人来说,时间和精力就是他们的光阴和性命。稍不注意,便是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再说,农活的种类很复杂,劳动的地点和收工的时间又变化多端,根本没一致可言,大家能集中在一起很不容易。那次聚会,大家非但没能尽兴谈吐,仅有的一个良好开端,也让突如其来的杜石朴搅乱了套,接踵而至的,则是无休无止的报复。
自己这个聚会的主持者,每天在完成本职任务的同时,还要砌半截园墙,杜英英也遭到了她老子的一番臭骂。情况最严重的要数张丽丽,竟然挨了她老子劈头盖脸的一通毒打,险些没把她的鼻梁骨打断。其他与会者也没能幸免,几乎每天都要遭到杜石朴的左量右算。
并且,还受到了上级领导的严厉谴责。韩维民在整个梨花湾大队的社员会议上,夸大其词地向他们敲起了警钟——有的“知识青年”回到生产队,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反而和一些出身不好的人秘密串联,打算搞反动组织,妄想纂夺生产队的领导权。如果不改邪归正,当心上大当、吃大亏、倒大霉!
海文当然能感觉出来,韩维民是想通过混淆时代背景,来给那次聚会增加社会压力。但他没有怯懦,杜石朴的报复,他早就领教过,不过多出几身臭汗而已。“力气是横财,出尽了再来”,靠着这个朴素而又颇能抚慰心灵创伤的真理,农民这个群体,该经历了多少磨难,越过了多少坎坷,一直繁衍生息到今日,何况这些点点滴滴。
从梨园被赶出来的当天下午,放下铺盖卷之后,他立即去找上次开过会的年轻人,商量今后该怎么做。在他的想象之中,他们应当是爱因斯坦曾说过的那种情景:“在我们所有的努力中,在每一次新旧观念之间的戏剧性斗争中,我们坚定了永恒的求知欲望,和对于我们的世界和谐性的始终不渝的信念,当在求知上所遭遇到的困难愈多,这种欲望与信念也愈强。”
仅对这段话的酷爱,也能说明,他正是这样一位有鲜明个性的人:每当客观外界的压力愈大,他的奋斗精神也愈加旺盛和强大。无论以往杜石朴的报复、求学时遇到的各种困难,还是此次考试落第,都概莫能外。他总觉得,人,尤其是年轻人,更应该如此,否则对年轻这个词及其概念,都是一种糟蹋和亵渎。
但实践却惩罚了他,辛勤奔波了一番,只有李心秀、高步清、海兰对他的态度还算不错,其他一些人,特别是他们的家长,大都对他的想法无法理解。总觉得,将来的事情再吸引人,可眼前的冷亏太难吃。这样的态度,几乎是群体性的看法,让他又一次领教了生活的冷漠和无情,同时也让他感觉到了成功的遥远和朦胧。
“是你把农村的事情看得过于简单了。”
“没想到会有这么复杂和严重。”
“要我看,对于你受气的事,绝不能轻易放过。”
“我倒认为,不必当回事。”
“如果现在不去找杜石朴算账,往后他会得寸进尺。”
“即使算,也是一笔糊涂账。”
“不管你怎样认为,我依然觉得这第一步很重要。”
听大伯说得那么实在和诚心,海文顿时增添了不少信心和力量。竟然觉得,自己正站在一座大山跟前,山上万物富有,需用什么只要一举手就可以得到。继而又感觉,自己正躲在一棵大树之后,前方什么样的东西袭来,都会应声倒下,接着便化为乌有。蓦地,后边的大山和前面的大树都已隐去,一股云烟过后,父亲的尊容竟然出现在自己的面前。老人家先在山上双手叉腰地看着他,接着又飘下山来站在大树生长过的地方,似乎想对他说些什么。直到自己的感觉完全稳定下来,海文才赶快回答:
“那营生,我正不想干了。”
“为啥?”
“今天杜石朴才骂出了实情,让我看管梨园,是为了让我跟着他的屁股转。我宁可干重活苦活,哪怕褪皮掉肉,也不愿做那种人。”
“俗话说得好:‘不怕四书五经读明,单怕世路闯明’。那半麻袋梨,在你这个干净娃的眼里是不少,可与这个生产队里一年四季明走的、暗去的相比,算个啥?‘众人的老子死了没人哭’啊!再说,那半麻袋梨,也不是白白被人拿走的。对于这一点,看来你根本没有想到。说到底,‘肉烂了在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