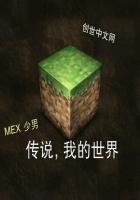其时南北两朝划江而治,北朝拓跋氏为鲜卑后裔,能征善战,对中原的锦绣河山素来虎视眈眈。及至这一朝,天弘帝拓跋烈励精图治,版图扩张了三分之一,膝下又有九子,自然不甘于北方苦寒之地,两朝之间的暗龃龉一时间暗流涌动。
这异族男子见司马明禹知道她的来历,似乎也并没有惊讶,只是略略一颔首,算是默认,开口道:“你倒认得我?”
司马明禹虽然重伤之下面色惨白,却毫无惧意,平静道:“北朝九王当中,只有四王拓跋彦礼贤下士,身边能人异士颇多,传说昔日西域天殊散人也被收罗在你幕僚之中。”
拓跋彦闻言笑道:“正是。你的生辰八字已知只要你没有离开凉州城,天殊散人布下玄天阵法就能逐渐缩小范围,郑小将军在此范围内将客栈民居一一搜遍,当然能找到。”
郑鸿飞见司马明禹神色肃穆,颇有敬重之意,更是傲然道:“玄天阵法精妙无比,只怕连‘凤潜’都不会。你司马氏无能,北朝天子心系百姓,岂能坐视不管,现下四王与我郑家交好,岂非你司马氏气数已尽?我郑家迟早取而代之,到时候南北虽划江而治,却天下互惠,百姓有福。”
司马明禹并不被他激怒,仍是平静笑道:“如今我才得明白,为何自小你便同我过不去,原来郑将军是存了这等鸿鹄之志。”
这就是在暗讽他本是燕雀,惹得郑鸿飞大怒,宝剑噌地一声拔出,寒光在屋中一闪。拓跋彦制止道:“不可,要使司马氏人心涣散,赵王谋逆的罪名就要坐实,他必定要在认罪伏法之后在菜市口腰斩。”
郑鸿飞闻言生生收回离司马明禹只有三寸不到的剑,只觉得一身的戾气无法纾解,忽的看到方才中了两掌横卧在地的蔡二立,当下一剑贯胸而出,嘴上吩咐带刀侍卫道:“一会把他的尸体悬到城门上去,看还有哪些狗奴才敢帮赵王谋逆。”
他下剑极快,一道血箭直冲出来,尽数洒在他身上,屋中人竟没有一个脸色有虞。
司马明禹仿佛没有看见蔡二立惨死当场一般,目光在天殊散人身上很停留了一刻,这才稍稍运了口气道:“抓我回京后,只怕皇上的也该晏驾了吧?到时候只要说皇长子赵王妄图弑君篡位,已被郑友耀和郑鸿飞父子拿下,腰斩于菜市口,先叫一众司马氏忠臣寒心,再扶持三弟登基,郑妃垂帘听政,大权在握。”
“几年后三弟必将死于二弟之手,如此二弟弑君之罪也是死路一条,我们兄弟三人皆无子嗣,大夏终于要改朝换代了,我说的是不是?”
郑鸿飞见他说的轻描淡写,好像不关自己的身家性命和司马氏气数一般,奇道:“是,难道你还有法子翻过来不成?”
“那么,”司马明禹却不再理会他,将目光重又回到拓跋彦身上道:“依郑氏父子之略,四王爷有什么好处呢,况且我观四王爷其人,是不会做无利的买卖的,不知四王有何求?”他语气闲闲,仿佛此刻并非性命攸关,而是跟一个久未谋面的朋友聊天。
拓跋彦微笑着颔首道:“司马明禹啊,你真是有趣,让我想到了我五年前,大约像你这么大的时候。”说着更指着他对郑鸿飞道:“我早说过他绝非草包,让你们留意。他不过是为自保而蛰伏,是条毒蛇,有机会了必定咬死对手”
司马明禹立刻接口道:“四王既引我为知己,何不与我合作,大夏分兵二十万,助王爷夺嫡。”
拓跋彦听了嘴角勾起一抹笑道:“这个买卖可做不成,我可没有夺嫡之心。况且郑将军和贵妃已经答应我,郑氏掌权后,北方十三城尽数割让给大魏,这等厚礼,我大魏怎会不收?”
说着语意中拖了一丝慵懒道:“明禹何以认为我有夺嫡之心?你不信么?”
司马明禹再不曾想到,郑氏为篡位,竟已勾结北魏,要割让北方的大半江山,深吸了一口气冷冷地看着郑鸿飞。
却说慕容青樱手里拎着元胡,马宝,防己,细辛和佩兰几包草药,轻手轻脚地避开人上来,见施谨瑜已经到了,却不进去,仿佛在全神贯注地听着什么。连忙上前奇道:“你怎么不进去?”
施谨瑜“嘘”了一声,指了指房中,压低声音道:“屋里不对劲。”话音刚落,青樱手中的几包草药已然到了他手中,人影却奔了出去。
施谨瑜一个伸手没能拉住,只得将草药随手搁在地上,追了过去。
青樱凑在门前屏住呼吸,从门缝中看去的时候,正是一个面目英越身材高大的异族男子略略转头对郑鸿飞说:“你们这就带他回京吧,连同兰陵侯叛子一道。”郑鸿飞闻言立即挥手示意带刀侍卫上前架起司马明禹。
就算旁人不认得这个人,青樱却认得他。昔年在山上的时候,此人每年端午便会上山来求见先生,态度十分恭谨,有一回先生在午睡,他便在月落庄庄门前等候。青樱在庄门口玩耍见到他还问过要不要帮他去叫醒先生,横竖先生脾气好,即使被叫醒也不会生气。这人却说不必,甘愿等先生醒来。
先生也不是每年都见他,青樱印象中好像只见过一次,回来后双眉紧蹙似是不太欢喜,自己当时问起来先生仿佛还说过,这是北朝的四王,每年都会来请他出山,即使自己不应允,他也定会留下非常厚重的礼品再行告辞。
先生不高兴是因为不喜欢欠人情。
是以她此刻一望便知,心中暗暗叫苦,却更思忖着要如何救司马明禹。
青樱全然没有听见他说话一般,心中自在盘算。忽然猛地一踢房门人就跃了进去。
施谨瑜大惊,也来不及想,跟着冲进去了房间。
两个人先后冲了进来,声响巨大。屋中人无不一惊,继而侧目。
施谨瑜在这当口还不忘教导青樱道:“你真是太鲁莽了,以后万万不可如此。”
青樱旁若无人地反诘道:“那你干嘛还跟进来?”
“我说过,劝不了你的时候只能帮你。”
说着两人相视一笑,还像从前在凤鸣山一般。
青樱上前对拓跋彦笑道:“与王爷一别数年,王爷的风采更胜往昔,倘若王爷不是男子,我还想向王爷讨教驻颜的方子呢。”
拓跋彦乍一见她,眼睛一亮,道:“你是青樱?如今已经长这么大了?”
郑鸿飞素来厌恶司马明禹,在凤鸣山中,旁人皆不与司马明禹来往,一半是他的身份不同,既是金枝玉叶,却又是落魄王孙,赔上一些虚礼却没有好处,另一半则是忌惮郑鸿飞,他才是十三人中真正身份最尊贵,最不能得罪之人。
偏有个慕容青樱与司马明禹交好,郑鸿飞对她也没有半分好感,及至后来她嫁给赵王为妃,更是敌友分明,此刻便恶言冷笑道:“真没想到,赵王妃今日也驾临,也好,一样是逆贼,一起拿下!”
施谨上前一步,与青樱站在一起。虽然一言不发,但是气氛却无形地紧张起来。
玉成公主左右逢源,与郑妃一向交好,驸马又是朝中大员,没有姑母的示下,总不能将他们的长子也一并拿下吧。
拓跋彦显然记得青樱,全然没有顾忌现下的气氛,反而冲青樱笑道:“你几时下的山,方才郑小将军叫你赵王妃?你已嫁人了?”眉目中行云流水,似是同老友在交谈一般舒展。
青樱本已想好言语,不想他突然问起这个,脸上不由得一红,已被郑鸿飞抢道:“自然是早嫁了人,他们俩在凤鸣山上时就不清不楚勾勾搭搭,只怕是做出了什么苟且不文之事,不得不尽早成婚。”
青樱的余光瞥向郑鸿飞见他如此污蔑自己和明禹,要是以她素日在凤鸣山的性子,必定要寻出些由头来刺他一番。然而一见明禹斜卧在床,心中一凛,深知不是任性的时候。
心念电转之下,一面似是自然地走上前去,一面笑道:“我都快十七岁了,还不嫁人,难道王爷会娶我么?”
她如此说,本意是为了放松屋里众人的警惕,方才她已经注意到了,房间西面窗户到明禹所在的床中间,并没有人挡住去路。原也是,司马明禹重伤,况且他会武功之事只怕没几个人知晓,郑鸿飞必定想不到防备他跳窗而逃,一行七个人只堵住了门。
本来明打明地带明禹跳窗,她并无半分把握,毕竟他伤势未愈跑不快,而屋中皆是高手,转瞬之间就能擒住他们。
但是此时却是夜间,今夜又是无星无月,如果没有屋中燃着的三根蜡烛,这个时辰该是伸手不见五指。
蜡烛在北边的台案上,她是要往床的方向跑,自然不可能去吹蜡烛。
但她心中已有一计,虽冒险,但只能一试。
拓跋彦见她如此有趣,忽然笑道:“既是嫁人了,为何还是闺阁的打扮,莫非?”
他虽然故意没有说白,但不光是青樱,就连施谨瑜心中都暗叫不好……赵王妃一事本来只为掩饰身份,她同司马明禹两人大约都从来没有在心中承认过,是以倘若不见人,她就还是旧日里姑娘家的打扮。这些时日在外,自然更是随意,长发并未束起,只是随意用一双珑水滴玉环在略略装饰,不是已婚妇人的发髻。
两人在宫中事事小心,何尝想到此刻因为发式被揭穿。
司马明禹阖上双目,也不知是在听还是气力不支晕了过去。
好在青樱反应极快,立时转移话题道:“王爷对青樱真是关心,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有求娶之意呢。”
她说出这话,在场的除了拓跋彦出身北朝,男女民风素来热辣直白,只含笑看着她。其余的人,连同郑鸿飞在内,都闹了个大红脸,施谨瑜更是眼睛都闭上了,嘴里还不忘呵斥她道:“青樱,快别胡说!你是姑娘家,怎可说这话!”
青樱似闲庭信步一般,不知不觉走到了拓跋彦面前,只听他笑道:“如果真有此意呢?”
青樱嘻嘻笑道:“有此意可不是光嘴上说说,可有什么信物没有?”
郑鸿飞施谨瑜并着屋里的一干人皆瞠目结舌,不期他们二人竟你一言我一语地认真谈起来一般。
青樱见拓跋彦只是眉眼含笑,却并无意真的交换什么东西,右手如电一闪,满头青丝如瀑洒落在肩头,她随意往后一挽。手中多出了束发用的双珑玉环,对拓跋彦道:“不如这枚束发玉环就送给王爷做个念想?即使王爷回了北朝,也能时时想起我来,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