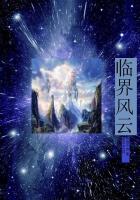见她没有动静,皇帝低头伸手一把将她捞了起来。臂弯中的少女不情不愿地看着她,眼角似乎还有盈盈的水雾。
“你刚才不是还在埋怨朕不来照应?现在你该承认,还是需要朕保护你吧。”他在她耳畔轻轻地说,却不料她忽然转过脸来,姣好的面容一下子放得极大,声音也不算小:“陛下也看见了,奴婢现在还不是活得好好的?”
他一时语塞,感受着臂弯中的温度,只觉得她虽然很近,却又似乎很远,也不知道她是不敢反抗还是不愿反抗。从前他不懂这些,以为只要把人强留在身边就行,经历了这许多才明白,旁人不会无缘无故地迎合自己,只有有求于己的时候才会故作顺从。对于她的心思,他本来不屑于知道,现在想去懂她,却又发现自己一无所知。她就像一株狂风凌虐下顽强生长的小草,时而依附大树替自己遮风挡雨,却不觉得它对自己有多重要。当它有足够力量保护自己的时候,自己就无足轻重了。
他有向上生长的繁茂的枝叶,需要时时仰望天空,而非俯视一棵小草。小草也不需要他永远的恩赐,一时的利用并不需要立誓永久依附,他从前把自己看得太重要,或许令旁人暗暗嘲笑也说不定。
可是他终究不肯相信她对自己的荫庇毫无感怀,闷声道:“朕已经替你出了这口气,你还有什么不乐意的?”
“奴婢也没有生什么气,她又不是故意的,我哪里是那么计较的人呢?奴婢难道看不出陛下是为了朝政才这么做的么,我又不是小孩子,可以随便哄骗的。”这一句反问教他愈发羞恼。自己好心好意替她出了恶气,却一点感谢之语也听不见,在她口中反而成了一个斤斤计较之人。女人怎么都这么不知好歹?
“既然你在这里住得挺习惯,朕也不管你了。你记住,若是再出什么事,永远别再指望朕替你出头。”他头也不回大步离开,心情十分郁闷。
“喂,宁贵妃被打入冷宫,你今天应该高兴才对,怎么还跟陛下怄气呢?”傅棠心知道她与皇帝之间的事情,眼见两人明明能够重归于好,却又偏偏再次擦肩而过。也不知她自己心里急不急,反正作为一个旁观者,她是挺急的。
皇帝和侍卫们都离开了尚寝局,众人忙着收拾一地狼藉,清簌一面听着傅棠心的话,从水里捞出抹布狠狠一拧,神色很是不悦。傅棠心见她只顾狠狠地拧绞手中的抹布不理睬自己,劈手夺了那块皱巴巴的抹布:“拧那么干做什么,你不高兴别拿东西出气。”
“我不拿抹布出气,还能拿什么?不要惹我,我今天药还没吃呢。”她气恼不过,面上的红云自与皇帝说话时就起了,直到现在还没有散,看来心里一直郁结着。
傅棠心见她终于开了金口,扑哧一声笑了:“你的病早好了,还吃什么药。哦我知道了,你不会在气他说你‘乱吃药’吧!”
清簌不说话,娇颜越发通红。傅棠心知道自己猜中了,心中暗暗好笑,却不得不装作一副感同身受的样子来:“这样的话的确挺让人生气的,但你也知道,他国事繁忙,很多事情也只知道一个大概,那个人强迫你喝药的实情他也不了解。这只是因为没人跟他说过,所以他才误会了。如果有人跟他说了实情,皇上英明睿智,又怎么会这样说你呢。如果换做是你,前面一直被人蒙在鼓里,故事只看到一个结局,也难免不误会什么嘛。”
“可是他还说什么‘最讨厌乱吃药的人’。没人强迫,谁会莫名其妙地吃药!说得轻巧,他在那种情况下,肯定二话不说就喝了!”想起之前自己中毒的那次经历,明明他已经知道酒水有问题,还是不管不顾地一口饮尽,好像知道中毒的不会是他而是自己似的。傅棠心说的虽然有些道理,心底到底还是有些气不过。傅棠心听她辩驳之声细弱蚊蝇,知道她已经气消了大半。将抹布丢在水桶中,二人重新盥洗了一番,继续擦拭着庭院中的血迹。
“什么忠臣的血是红的,佞臣的血是黑的,我看都一样,有什么区别?你看这地上,刚开始都是红的,一会儿都变黑了。他的血和安侍卫的血混在地上都一样,哪里还分得清,真是瞎说一气。”
“你还看呢?洒了一地的血,看得我都要晕了,不不,闻味道我都要吐了。”
二人细细清理着带血的地面,听旁边几个小宫女在抱怨,忍不住相视莞尔。傅棠心刚升了从八品,在无品级的宫女们面前算是姑姑了,所以适时也要拿一下威风出来。她尽力绷着脸,做出一副颐指气使的样子:“不好好干活,胡乱编排什么呢?想不想看看你的血是什么颜色的?”
“我错了姑姑,我们不说话了,立刻好好干活。”小宫女吐了吐舌头,立马住了口。程姑姑走了过来,嗔怪地看了她一眼:“自个儿还在说闲话呢,不许旁人说。擦不干净就先歇着吧,听说宫正司有清理血迹的好办法,我待会儿问问去。你们今日也累了,早些休息去。”
“姑姑。”半嗔半讨好地喊了一声,傅棠心的面上露出怨恨的神色,“姑姑的脸可好些了,现在还疼不疼?安氏真是罪有应得!若不是她被打入冷宫,我还真得找她理论去。”
“你还找她理论?”程姑姑知道她是开玩笑,也笑着摇了摇头,“你这孩子,就会说些好听的话。”
“姑姑今日也累了,还是奴婢替您去一趟宫正司吧。那条路奴婢倒还熟悉。”清簌看着程姑姑脸上的红印,心里有些不忍。
程姑姑停止夸赞傅棠心的话头,朝她满意地点了点头:“也好,你们年轻,就替老身跑一趟吧。”
南书房里,案下奏陈的官员口若悬河,御案上的天子却神色郁郁。
“……加上贴补河工的钱,一共的支出是去年的两倍。因此这次我们给礼部的拨款少了两千两,致他们在京畿开设三家书馆的规划难以实现。礼部尚书因为这个,已经找了臣很多次,臣也实在没有办法。臣等……陛下,陛下,您有没有在听?”桌案后的红衣官员抬起头,见皇帝托着腮,满目愁容神色淡淡,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小心翼翼地问。
“林梓瑞。”皇帝唤着他的名字,指尖轻轻地敲打着桌面,十分客气地询问,“林尚书,听说你家中妻妾和睦,前日才刚纳了第三房小妾,可是这样?”
“啊?”户部尚书一下子没反应过来,颇有些目瞪口呆。不过这也坐实了皇帝刚才确实没有将他的奏报听进去一个字。他有些郁闷,却也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应答:“回陛下,臣年下四十有三,膝下只有一个儿子,因为小时候发烧,现在口耳还有些毛病。家母一定要臣再纳一房妾室,微臣只好尊重她的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