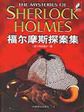被霍去病用言语一损,容笑一张老脸更烫,别的不好说,一左一右烤熟两个鸡翅膀基本没什么难度,额头上撩起头发,还可以顺便煎个蛋,省柴又环保。
霍去病环保意识比较弱,没想到这一层,却好奇另外一件事,是故低头背手,眯着眼睛盯住她红艳艳的面颊,不紧不慢地逼近这只人形煎锅。
容笑坐在地上,如感芒刺在背,却故作镇定,抱住双膝,放长呼吸。
少年轻柔的气息突然拂上左耳耳廓,容笑浑身一颤,惊觉全身血脉里都仿佛有蚂蚁在爬,忍不住退缩惊慌:“你、你凑过来干什么?”本该是指责的声音,偏偏变得绵软无力,似夜半月色溶溶,更如池边柳絮淡淡。
霍去病不理会对方的色厉内荏,伸出右臂,用食指和中指瞄准她散落鬓边的乱发,夹起、掠开,再将拇指指肚准确无误地摁上她左边的颧骨,认真地蹭了又蹭。
容笑忍无可忍,将脸转了过来,鼻尖恰巧顶上少年的鼻尖。
猝不及防的,两双幽深似潭的黑眸对住彼此,眼睁睁瞧着有倒影旋在深潭中,一寸寸,一分分,越陷越深。
木案上,烛泪汹涌,一滴接一滴滑落,一道道凝在烛身,仿佛愈合多年的伤口。
伤处已复,疤痕难消。
帐内,空气被烛火灼烫得摇摆不定,两个人的侧面剪影镌刻在篷壁,一高一矮,一站一坐,一俯视一仰头,长长的眼睫一抖不抖,四目相投。
他和她的呼吸早已凝住。
原来,投在对方眼眸中的两个小小倒影,是自己。
目光下行,掠过对方的嘴唇,昨夜的一幕倏然撞上心头,那时他们脸对着脸,唇贴着唇……
“啪!”
一朵烛花意外爆开,惊散不合时宜的联想,两个人“唰”地扭脸转身,不约而同用手指捂住自己的嘴唇,心底多了几分难言的慌乱。
尴尬沉默中,一个抬头盯着帐篷顶上的纹路学习针法,一个低头用手指扣着木案研究油漆。
过了良久,抬头的那个挠挠后脑勺,解释道:“我就是想看看,你脸上的伤如何好得这样快,不是想,唔,不是想……。”措辞许久,无以为继。
低头的那个继续摸油漆,瓮声接话:“嗯,明白。”
抬头的那个松了一口气:“明白就好,明白就好。昨夜的那个……唔,昨夜那事,忘了吧。”
低头的那个动作变得有些凶悍,木案差点被手指插穿,声音好像是被挤出来的:“本、来、已、经、忘、了!”
抬头的那个整整衣衫,顾左右而言他:“是去练武场集合的时辰了,我先行一步,你、你也快些吧。”说毕,翻出铠甲,快速披挂,大走到帐边,一撩帘,身形便融入了外面的春光里。
等他脚步声远,容笑坐在地上蹬腿乱踹,恨不得踹出个无形的洞来,一把将霍去病给塞进去活埋。
抓抓早已凌乱不堪的头发,跳起身,披上铠甲,容笑吹灭烛火,撩帘退步出帐。
懊丧感仍然浓郁积压在心头,忍不住狠狠跺了下脚,不想一脚跺到个无辜路人。
心底一惊,她忙低头,连声道歉:“对不住,对不住!”
对方痛得哇哇大叫,听见道歉却仍不依不饶、破口大骂:“走路不看路,瞎了眼的……咦?你,你不就是那个臭小子!”
这声音着实耳熟,好奇抬头看清来人,容笑惊讶地张大眼睛,“啊”的一声向空地连退两步。
铠甲十分沉重,平衡没控制好,她一个踉跄:“你是……。”
名字明明就在嘴边。
对了,眼睛一亮,他是那个……胖胖的卫生巾。
“你是淮南国的苏非!”
胖子苏非身形庞大,往那一站,就是一座小山,结结实实挡住了所有阳光、所有视线。他扭扭脚腕,越扭越痛,忍不住厉声发牢骚:“不是我是谁!每次见你这臭小子,苏某人都倒霉透顶!”
被笼在他制造的阴影中,容笑在心里捂嘴偷乐——这就叫报应,谁让你当初刚见面就踩了我一脚来的!
“你怎么来了这里?”容笑竭力克制住笑意,正色发问:“你家太子呢?”
“想不到你倒是对本太子一直念念不忘!”
不等答话,胖子苏非只感身后有大力袭来,将自己一把推到一边,踉跄两步,勉力站住,忍不住回头,委屈瘪嘴告状:“太子,他踩……。”
“容笑,想不到你也在这期门营内,本太子与你二人当真是巧遇啊巧遇!哈哈!”
明媚的阳光里,一个胖子哀伤地捂着脚,看着他家风流倜傥的主人左手展开绯色袍袖,右手轻抚腰间灿灿金剑,故作潇洒地对着个臭小子朗笑。
那笑,呸呸,真假!报仇便一剑咔嚓,何必入营卖笑?
胖子撇嘴腹诽,瘦子李尚看他形貌过于猥琐,生怕他任性闹事,连忙一把将他扯到身后,适时提醒,声音尖细:“太子,时辰不早,该去练武场了。”
太子刘迁威严点头,挥挥手,故作礼贤下士之态:“容笑,难得重逢,我便赐你与本太子并肩同行!”说罢,目光灼灼地盯着容笑,一脸期待。
容笑眨眨眼,这是神马意思?
“大胆!还不快些跪下谢恩!”胖子挣脱瘦子的束缚,磨牙教导,一副恨不得生啖了她的模样。
容笑被他吼得一哆嗦,情不自禁又退两步,不想一脚踩到自己略显肥大的下裳后摆,立时向后跌倒!
刘迁忙伸手拉她,不想她倒势凶猛,两人的手指在空中交错而过……
风声起,身后奔来一人,眼明手快,一把将她接住。
坚定的双手握紧她肩头,让人觉得安心无比,站稳回头,果然是李敢。
李敢对她笑笑,声音柔和爽朗:“怕你不知时辰,过来提醒你去练武场集合。这甲胄沉重,初穿不习惯,待你适应两日,便好了。”
仿佛才看见刘迁等三人,他松开容笑肩膀,侧步抱拳躬身道:“听仆射大人说,陛下知淮南太子骑术出众,昨夜特请太子入期门,赐教众郎员。敢才得知消息,迎接来迟,还望太子恕罪!”
苏非本就忌恨李敢那日射箭偷袭雷被,扫了淮南的面子,此时见他大模大样居然不施跪拜之礼,心下更是来气,不由冷笑几声:“要说迎接太子,恐怕你李敢区区一个郎员还不够资格!”
刘迁一摆手止住苏非,语气和缓,颇显身为太子的气度:“现下大家都在期门军共事,那便不必分什么尊卑高低了,只按军礼相见即可!本太子听说,你李敢刚被擢升为期门宿卫,负责教习新员箭术,也是喜事一桩。今夜若无事,便来本太子帐中小酌一杯如何?”
不等李敢答话,他扭脸看向容笑:“容笑,你也来吧!”
容笑和李敢对视一眼,面色都有几分惊疑不定,刚躬下身,要婉拒,太子“唰”一甩绯红袍袖,步履招摇地走了。
一胖一瘦两个手下,快步跟了上去。胖子临走前,还留下一声响而又响的“哼”,仿佛不如此便不足以表达他内心对容李二人深深的鄙视。
容李二人面面相觑,都搞不清这位太子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却也不好再追上去拒绝。
遥遥的,那三人背影越变越淡,容笑“啊”的一声醒悟过来。
李敢被她吓一跳:“容兄弟,你怎么了?”
容笑指着瘦子李尚的背影,哆嗦着唇,半天说不出话,李敢笑着拍拍她的头:“别着急,慢慢说!”
被他这一拍,容笑缓过气来:“昨天我随你入营,曾瞧见有人躲在树后偷窥,跟你说句话的工夫,那人就不见了,当时还以为是我眼花,方才看见李尚的背影,我才认出来,那人便是……。”
“便是李尚?”
容笑用力点头。
李敢背着手沉吟了一会儿:“这么说来,淮南太子一行大有可能是为你而入营。”
两人意见不谋而合,容笑心里“咯噔”一声,被压上块石头。她没想到奇葩那么记仇,不过踩他一脚,居然不顾太子身份,一路追踪到军营来打击报复。想必汉武帝看中他骑术是假,他自己请求入营才是真的。
瞧出她的心事,李敢又用右手握紧她肩头,目光坚定:“容兄弟,你且别慌,凡事有我!而且……。”他眨眨右眼,“太学里的五经博士举荐弟子司马迁前来期门驻营教习兵法四行。”
容笑大喜:“你是说司马兄现下也到了营中?那他上次在李府为何不告诉我?”
李敢松开手,转身前行:“御命昨日才下,他自己都未料到,如何能提前告知?”
跟上他的脚步,容笑面色由阴转晴:“如此一来,我便不再是孤掌难鸣了!那太子若是气量狭小,想报复于我,我也有朋友相助!”
“话虽如此,你我今后行事还是要分外小心,别被有心人抓住把柄!那霍去病的话,回去后,我又思量一番,发觉他讲得甚有道理。”一扭脸,李敢认真嘱咐:“容兄弟,你与他同帐,今后万万不可再与他口角。事先未对你解释详细,是我思虑不周。因你不知他家世,才敢对他拳脚相加。其实,我早该告诉你,那霍去病身份矜贵异常,他乃是……。”
“李宿卫,仆射大人到处在找你,你快随我来!”
张仆射的贴身侍从奔过来,截断了李敢未说完的话,李敢见他一脸焦急,不敢怠慢,只好对容笑无奈一笑,跟随而去。
容笑听话听了一半,只觉丈二摸不到头脑,霍去病身份矜贵?当今天子姓刘,皇后姓卫,一路行来,也没听说哪个大臣姓霍,就算他家富贵,又能富贵到哪里去?
看看天光大亮,众郎员都入了练武场,振振甲胄,容笑大踏步向人群奔去。